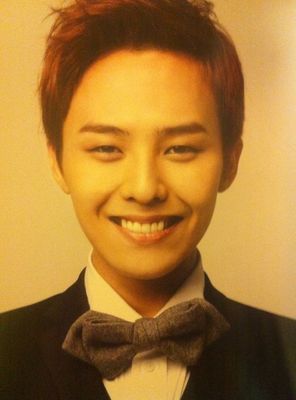永远的马缨花
——缅怀作家张贤亮
多少年以后,他在《辞海》上看到:马缨花又名绿化树,喜光,耐干旱瘠薄。这条目上解释的文字没有一点不和马缨花相似。这一夜章永璘失眠了。“绿化树!绿化树!……”章永璘时时闪现一株株绿化树——《绿化树》
昨晚看完电影《亲爱的》回到家。为那些个悲情寻子的父亲、母亲们感到难过,本想写篇影评。打开电脑,各大网站都在报道同一个消息,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离世……
读张贤亮的作品是在我二十几岁的年纪。那时候从山西辗转到了福建平潭海岛工作。单位处于一个叫娘宫的渔村旁边,宿舍面对着空旷的大海,下往后回到宿舍没有电视,更别说电脑了。唯一的消遣就是听收音机,阅读各类作家的书籍。而张贤亮就是这个时期走入我的生活。
记得读他的《绿化树》时,我正雄心壮志捧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书在猛啃,那段时间里年轻人兴起自考热,类似于成人高考的自学考试。我期盼能通过考试拿到一张大专文凭,把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填补上。
某天晚上,我正在为哲学中提到的一元论和二元论苦恼,翻到张贤亮妙趣横生的句子,就放不下了,翻开《绿化树》开启了一场与作家隔着书页交谈的感动。冬日的娘宫港,静得可怕,黑夜如潮水涌动。宿舍正对着海面,波涛起伏的海上,碎银般的白月光洒满了海面。坐在台灯下,灯光迷离中,收音机里台湾歌手齐豫低低地唱着梦中的橄榄树,那是一个流浪者的梦魇。如同张贤亮因为一首《大风歌》的诗歌,被发配到大西北,一去就是22载。但是他没有被命运打倒,1979年平反,重新执笔,而后作品如同井喷。写出了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壹亿陆》等一系列让中国文坛震惊的作品。
话题扯远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才二十几岁,为了追寻一段海岛的爱情“南漂”至平潭,而他把我扔在岛上,去山区开挖隧道工程去了,海岛男人的生活目标简单,赚钱,买房,结婚,生娃。
不管那个年代,只要揭开生活面上的面纱,本来面目都是狰狞的。
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借“章永璘”右派的口吻,其实是还原了他成为右派后的种种人生际遇。他除了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对物质,说穿就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在读《绿化树》时,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来描绘一个右派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个“少爷”沦为阶下囚的种种滑稽的生存哲学。
他利用视觉差,在食堂里多打100CC的稀饭;他利用老农民的逻辑局限,骗了人家几斤黄萝卜,兴奋得像是全宇宙的君主:“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倒霉的是那些萝卜全翻进了沟里;他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只为能刮一下蒸馒头的屉布,他得逞了,那屉布上刮下来的馒头渣渣足足有一斤;他奉命用糨子糊窗子时,也能用克扣下来的糨子,摊上几张煎饼,可怕的饥饿感暂时被压下,心头窜出的,却是扎心扎肺的酸楚……
如此这般之后,他终于写到了他的救赎者,那个名叫马缨花的女子。她请他来到自己温暖的小屋,坐在炕头,给他吃的,给他那做梦都不敢想的死面馒头。他在馒头上看到那女子指肚的印记:“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看到这里,除了对主人翁的同情,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自艾自怜起来。曾经以为海岛是桃花源,生活在其间,发现除了要适应那凛冽的风,还有腥味极重的鱼干,以及稀得可照人影的地瓜粥,更别说听不懂海岛人声线极高的地瓜方言,未来显得如此渺茫,看不到未来的等待,就如张贤亮在西北改造的漫长时日……
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借用右派“章永璘”在家继续读《资本论》情节,试图把一个右派灵魂的得到净化,他在文中自省“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竟然用这种手段去骗一个老农”。这时候,他遇到了那个叫马缨花的女子,那个冒着风险给他白面吃的女子,还有蒸土豆吃的女子……
这个女子用一种极其朴素且认死理的方式,供着她眼中的知识分子吃喝,为了他甚至不惜利用瘸腿保管对她的好感获得食物,供章永璘读书。这个女子的爱,带着凛冽的暖意和寒意并存。她把章永璘急于要结婚的原因领会错了,误以为他不相信她,她对章永璘发誓:“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呢!”
在还相信爱情的年纪,读到这样的细节,真是泪眼婆娑。后来又买了张贤亮文集,还读了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后来,知道张贤亮为香港的不老女神宫雪花写自传,渐渐地觉得他似乎不是当年书写《绿化树》的张贤亮了,也慢慢淡出了关注他的视线。
许多年过去了,再翻起书柜里扉页有些发黄的《绿化树》,那书页里还夹着一两行读书的感怀,“当苦难的人生中,遇到一个自己倾心爱的人,那是一种幸福。”
读“绿化树”,可以说是影响我的爱情观。曾经以为爱情是一个男子百般的疼爱你 ,将就你,甚至把你当公主看待……而张贤亮的“马缨花”为了一段爱情,除了低到尘埃里,还以身心相许,为她爱的人所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在海岛结婚生子,接触了许多海坛女子,她们的生活观就是如此,为了撑起一个家,春夏秋冬除了忙锅台,还要忙出海养殖收采……
在港口工作的十年间,年年冬日里看到海滩前有包着头巾的妇女,推着巨大的橡胶轮胎,在冰冷的海水中行进,轮胎上面放着用网兜装着带壳的海蛎。平潭冬天的东北季风肆虐,那灰蒙蒙的天空中还常常伴着细雨,在海水中艰难的行进,那冰冷的海水漫上女人的腰际,甚至齐达胸口。空旷的海滩前,唯有海岛女子头上鲜红或大绿的头巾,格外醒目的风中飞舞,如同生命的火焰在燃烧……
每每这个时刻,我就会想起“马缨花”,想起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勇敢决绝的女子,在西北的火炕中烤着地瓜,烤着土豆,只为她珍爱的右派男人能填饱肚子,能够有力气读书,能够走出这黄土高坡……
时光过去了近二十载,张贤亮笔下的“马缨花”还是如此生动地活着,他却走了。作家闫红说张贤亮:“从苦难里趟过来,有人陷入深沉的反思,有人去做不相干的学问,有人更加唯唯诺诺,只有他,是抡圆了活。而他还说,自己这样都算落魄的,他原本的理想是做总统。”
其实,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就是自己的总统,一个书写江山,指点世界的总统。他的文字就是他的兵马,在时间的长河里托着这个“总统”行走,不管他走多远,不管他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在中国文学界的领域里,他都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就是那个被“马缨花”永远爱着的“总统”。

甲午年初秋写这段文字怀念曾经喜欢的作家张贤亮先生
2014年9月28日于平潭时报社办公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