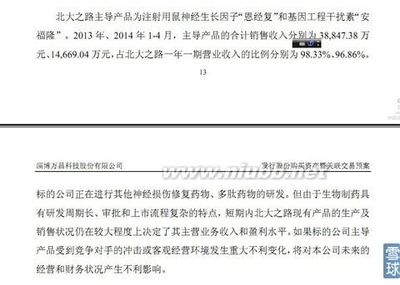毛继鸿先生,是“例外Exception”品牌1/2的创始人,亦是这个品牌的领袖。16年前,他与前妻马可一同创办“例外”,成就了中国最早,亦是最成功的设计师品牌。他不仅见证了时代的进程,还持续影响着中国设计师品牌的发展。
毛继鸿不是个谦虚的人,他把2005年后,中国设计师品牌服装大发展的行情,归功于“例外”的突围而出;也暗示自己肯定不是最有钱的人,但应该是有钱人里最有文化的⋯⋯他和马可当年游览黄埔军校,意气风发地在北伐纪念碑前对马可说:“我们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我们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所以,他注定不会是个谦虚的人。谦虚便意味着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要建功立业,哪怕这个时代不再金戈铁马。
于是,从“例外”的诞生,到品牌形象和产品的全面升级,之后“方所”又横空出世,紧接着将在上海带来一连串的“大动作”,这一路澎湃走来,毛继鸿又哪里甘做池中物?
设计师品牌的春天
“例外”并非是一帆风顺的。2005年,毛继鸿过得不太平。2004年11月,“例外”在北京第一次作秀,产品全面升级。当时的市场,设计师品牌的附加值还未显现出来,所有人都在相对较低的价位上,与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商业品牌搏杀。价格翻了一倍的“例外”,门店数量大跳水,犹如给“例外”做了一次大换血;之后,马可的淡出,也逼迫着毛继鸿要肩负起设计的重任⋯⋯
毛继鸿:我们这一路过来,面临着几次的重新定位,在不同的时期里面的重新定位。在WTO之前,我们做了一次提升。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可能跟那个逸飞、3E这些品牌一样,都全部low掉了。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快有100家店了。那个时候,我们去北京的展会,看到的全是“徒子徒孙”在学“例外”。我们俩转完后,很骄傲,但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就500元到800元。不行,这个问题我们得改。所以就促成了2004年11月在北京的那一场秀,马可把整个品牌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了,那盘货也翻了一倍的价格。突然间,生意跌得一塌糊涂。后来就开始收店,收了50家店,就只剩50家店。但我那一年50家店的收入,超过原来100家店的5%。
林剑:于是,便迎来了设计师品牌的大爆发。
毛继鸿:2005年提升后,诞生了我们第一家过千万的店。那个时候过千万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的设计师品牌没有一个可以单店过千万的。我们就45平米就过了千万。那一年,我们把那个店给扩充了,在扩充店的前面,我就做了1000万的冰。我跟我们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再加上SOGO的老板,三个人拿锤子把那个冰给敲了,等于是新店开业。把冰敲完后,一个星期里,全国50多家店铺里面都有一张大的宣传片,就是我们敲冰的。所有商场都意识到设计师品牌可以赚钱,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去。所以才有了后来那么多牌子。首当其冲的就是DECOSTER。
林剑:春天的感觉很爽吧?
毛继鸿:我觉得最幸福的还是马可,她完全在做自己的东西。我问她,赚了钱干什么?我说资本不是罪恶,使用资本的方式才有善恶的分别。我说其实我们通过资本可以买自由。她当时要做“无用”,从05年开始就开始采风、准备。我全力支持她,因为等于整个公司我一个人顶着。我当时就说,要让你一个人先出来,至少我们是放了你一个人的自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和那些福建的运动品牌,与温州的休闲品牌相比,“例外”仍旧是小众的。它在渠道商那里是个神话,在文化界是个传奇,而在时装界似乎姿态孤傲。但去年春天,随着彭丽媛频频亮相于媒体,“例外”的名字被传遍了网络,一时间,天下谁人不识君。很幸运,毛继鸿从此不再需要对大众言说“我是谁”,
林剑:在互联网的时代,品牌的沟通需要很符号化的东西。
毛继鸿:对。其实从去年的三月份之后,那件事件之后,我觉得互联网是帮我们不少忙的⋯⋯就到了后面的问题了,你怎么跟消费者,跟这个市场,跟整个世界,用更准确的语言去传递出我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林剑:你们身上东方的印记还是很明显的。
毛继鸿:我们当时在做“无用”的时候,其实一直想破一个问题——日本人已经把东方的视觉符号领域已经挤满了,留给后人的空间不大了。我跟马可和团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真正把东方设计师和中国的设计师之间的这种东西戳破。可能在这么多做服装企业的设计师中,我是花的时间最多的。过去在做商业的那些符号——“例外”的符号——可以借用日本人的手法,也可以借用欧洲人的手法。因为衣服始终走不掉两只袖子,两个裤筒,一个领子,这是基本结构,变也变不到哪里去。但要真正建立一种语言体系的话,我们选择从一个创作者/人的角度上去考虑的。我们从发音、品牌名称、LOGO、品牌寓意,再到衣服的型、表演形式⋯⋯都做了很多的区分。这个其实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去借鉴回来的,作为一个创作人生命本身的角度去传述这个事情。这套思路是非常重要。
林剑:外界都在说,现在的“例外”在“去马可化”。
毛继鸿:后面我们存在一个问题,马可不直接操刀去做“例外”的时候,其实她再回来做“例外”也不行 了。这是老实话。因为她的观念完全是“无用”的观念,很不适合商业操作。我得重新去换一套语言回来。这套语言其实把我又逼到了带设计的那个领域里面去。其实过去家里有一个设计师,天天做就好了,你就在外面做市场、做传播。现在再找回来的语言,我觉得开始有一定的当代性的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会重新去思考,你越往外走,你会越发现其实家里面的东西才是宝贝,老祖宗的那个玩意其实是宝贝。其实你的识别性就在那里了。其实我们现在力求换回来一套系统,不是特别的完整,也是在过程当中。通过去年的情况来讲,我不再需要讲“我是谁”的时候,我可以开始重新做我的一个国土,我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市场在那里,我的认知度在那里,我拿到全世界去都是我自己。但是我自己要做得特别清楚,我们就往回走,就再看回一些民间的东西,关于我们传统的东西。后来我们做方所也会带来更多的人群,去思考到底人文关怀、文化、艺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林剑:你这样做,累不累呢?
毛继鸿: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马可比我还要累。习惯已经拧成这样子了,当你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找不到力量。很简单地去做事情,我是找不到力量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不然我的心是没法安的,没法稳定的。
他们这一代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作品大奖赛来到中国。首届铜奖获得者王一扬,后来创办了“Zuczug/素然”;第二届铜奖获得者陈翔,后来创办了“Decoster德诗”;而与陈翔同届的马可,却摘得金奖,与名落孙山的毛继鸿一起,创办了“例外”。这真是一间时装界的“黄埔军校”,成为了开创中国设计师品牌的“三驾马车”。虽然,这几个人的名次都优于毛继鸿,但他讲起当年自己参赛的设计,仍自豪地认为是属于未来的。
林剑:例外的开始,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设计呢?
毛继鸿: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过程有相似之处,但是肯定我们理解的也有不一样。我跟马可当时在南方相对比较独立的圈子。我们对待衣服的角度,最早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受日本的那几个设计师影响挺大,就那三杰嘛,Commedes Garcons,山本耀司,包括三宅一生。
林剑:三宅的理论是西方设计表现人的曲线,就是量体裁衣;他最核心的理论,虽然表现形式没有那么传统,但是他的观念是传统的——衣服就是衣服,是人去适应衣服,和服什么的都的这样做的。
毛继鸿:是这样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我们当时觉得最好的几个设计师,像JeanPaul Gaultier、Claude Montana、Thierry Mugler,意大利的主要是RomeoGigli还有Armani等等,尤以VivienneWestwood更为甚,是在扒皮。但只是他们每个人的形式不同,但基本都是贴着人的身体去做衣服的。
三宅一生当时构建了第二个空间出来,是脱离了身体,在身体跟衣服之间构建一个新的空间出来,像和服的后背这个空间,包括穿着的方式。后来,兄弟杯后,我没有做衣服,跟马可在香港公司待过两三年。因为香港公司基本是做美国单和欧洲单,这个影响很大的。1995年,我们到了那家公司,在汕头待了四五个月,就要一个能卖的系列,要改成Armani的样子,那个时候根本不喜欢Armani,但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是牛逼的。
林剑:所以马可、王一扬、陈翔这一代从早期“兄弟杯”出来的设计师,都带有了那个启蒙年代的烙印。
毛继鸿:当下这个时代造就的设计师,和这个产业本身都存在硬伤。我认为这个产业本身核心的东西是技术和衣服。当你真的跟由Yohji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包括现在最好的这些好的设计师,真觉得没有这几把剪子是没法做的。而且就说我这个,我告诉你我在缝纫机是什么概念?因为我话里面有话的,一踩就飞了。不管你现在是做中国的衣服,还是做外国的衣服,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会越来越近,会越来越融合,你分不清楚哪个东西是谁的,但是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现在“例外”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林剑:那时候你在广州,广州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一些东西的话是容易一些。
毛继鸿:其实那个东西已经真的不重要了,你说要做一个最牛逼的发动机,把全世界的东西全部组合在一起,中国的大飞机就是这样做,全球采购。苹果也是这样子的,你要做一个最牛逼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眼睛,有没有这个落实的体系,这个很重要,你的工作的态度,你的工作逻辑和你的工作团队的协同,其实环境就是这样子。像Yohji讲过,我的版师比我的设计师重要。但是你去理解一下,为什么版师比设计师重要呢?我们所有的企业想不通这一件事情。他的理论依据是版师是可以控制风格的,但设计师不能控制风格,你画得出来,但做不出来。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我们所有的设计师都要会做衣服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设计师做提案的时候,都必须做出衣服来,这个提案才是完整的。
林剑:但不能分工吗?设计师设计,版师就做版师?
毛继鸿:这是我们教育体系当中不好的一块,把它分开了。其实我觉得服装最核心的部分是两手、材料、身体和人本身的关系,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可以跟手有关系的行业。如果说这个行业丢失了这个东西,后面也是会被所有的电子的东西给替代掉。所以我们在做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保留它。这就像是做模的过程,设计师永远会用手跟泥,其他95%都可以用统一化的东西,但是唯一的就是线条,这个线条是用粘土去抚摸出来的,捏出来的,热爱我品牌的人,是因为喜欢我的线条,因为都是摸出来的。
林剑:这个观点和当下流行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年轻设计师,是英国系统,圣马丁系统出来的,完全忽略做。
毛继鸿:其实中国现在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年轻的设计师深度不够,这是现在最难的。我们中国的设计师,说老实话都只是画小人,根本不是跟材料,跟人体,根本不是跟立体裁减这方面的对话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拨的知识培养,才真正可以去做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例外一直在做的过程。要改变年轻人对于文化,对于设计,对于衣服这件事情的理解是最难的。
购物空间的营造
如今周末造访广州太古汇地下一层的方所,连插根针进去都难。这个融合了“例外”全线产品,外加百货、图书、咖啡的综合性商业空间,用毛继鸿的话来说,是他另一种讲话的渠道。单一的服装,已不再能承载毛继鸿不断拓展边界的乌托邦理想。于是,他从尺度上,把服装——紧贴人类皮肤,人外部空间的建构——往外延伸至购物空间。
林剑:我觉得方所这个东西做的时间点拿捏非常好,再早可能也不行。晚了这个形态大家都做,也不好。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大家原来的社交场所是线下多渠道的,包括有文化的,和消费的。未来会越来越集中,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商业空间。库哈斯以前写过一个《哈佛购物指南》,认为,购物可能是人类未来终极的社交空间。在一定体量的商业空间里面,除了零售外,含有一定的社交功能。把整个的零售品牌的形象,全部整合到第三空间,会是改变未来线下零售的关键。
毛继鸿:因为有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这些渠道的冲击之后,其实实体店购物变得越来越无聊。我5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有一次我在深圳万象城,在电梯上面走,看到下面的餐饮有很多人,然后在上面走到每家店去的人非常少。我当时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单品牌销售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本来是一个公共空间,又变成了一个独有空间。这是一个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觉得那个空间被私有化之后,不仅人员在里面的效率不高,人员的支付方式上面也会存在着浪费。后来我就一直都在思考这个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好玩。当你找了一个载体,公共空间的适用性、效率等各个方面都会提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打破了等级,是那些用信用金钱形成的等级。
林剑:其实购物空间的规划,从本质上来说和一个城市的规划是一样的。按功能划分住宅区、CBD,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毛继鸿:对,这几天我们看街道就清楚了,好的城市街道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适合的。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充分地放大,你把一条马路变成200米、300米宽的话,人在那里面就是一只蚂蚁,人没有尊严了。其实这就是尺度上面的把握。我们说一个好的城市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山、通道,跟建筑物本身对话的关系。10年前,我回长沙的时候,发现“沃尔玛”在黄兴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只是一种大公司、大品牌,非常低质的产品。我们拿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