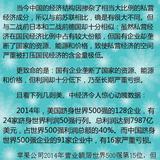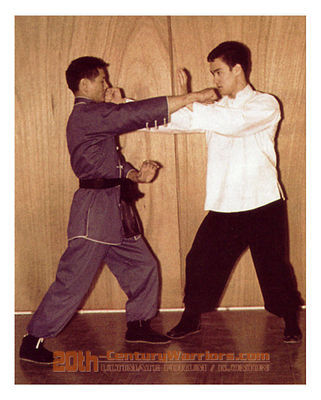[转载]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
![[转载][转载]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 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变化](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104622t01ad05eb0888b3f78e.jpg)
标签:转载 |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国涌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我把"被"字抄错,成了"披"字,现在一一改正,并向各位读者朋友致以深深的歉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31页)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1999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2003年4月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五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2月27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10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五四”以后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21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2001年5月8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五百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和平演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2002年10月30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21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500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1998年3月4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Scientist,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十二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11月11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1941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1944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
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1998年3月11日)
这些观点本身诚然还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导真理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狭隘的现实算计。他认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口号时,绝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学,“他们好象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希望许良英能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许陈寅恪,乃是因为陈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对“利禄之徒”弥漫,伪学术、伪思想盛行的学界现状忧心忡忡,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2001年4月21日,读了许良英转给他的99岁的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99岁的大老……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先生。季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谈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晖时,他说本来以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但是迄今还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这篇批判文章,固然论点很不错,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对此他深感忧虑。
二
晚年李慎之的内心深处之所以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凉”,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对现实政治制度的绝望、清醒,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他们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后世的人往往难以想象的。二是他对文化传统即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三是他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无忏悔。
2002年5月18日,在读了我们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后,他曾写信给许良英:“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不配。第二个感觉是有些悲凉,偌大一个中国,能数得上的就这么些人,而且还有像我这样对民主、自由主义了解甚少之人。”这里面固然有他自谦的成分,但这种悲凉是一贯的,他多次说及全国上下懂民主的也不过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会说:“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已不敢说什么‘启全国人民之蒙’的话,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识分子’,于愿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后写信给许良英:
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
应法广采访,对我虽非第一次,但确极稀少,我现在是想争取多一些发言机会,但是我总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这样叫一叫,当然不是考虑为当局鸣锣喝道,而是希望能给国人一个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和平演变”。不过由于当局一动不动,我觉得如果能先实行私有化,也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点社会基础。至于政治上当局正在不断收紧,我的文章大概已无在大陆发表的可能,我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已经老了,物质地讲,我们是最少可怕的人,现在老人都越来越衰退,我胆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已。
我越来越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完全靠谎言维持呢?
在这封信后面他又加了几句话,表示“1、启蒙之必要,2、启蒙之艰难,3、启蒙还是有希望的”,并惭愧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展现了远古神话中的那种悲壮的情怀,悲观没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没有使他放弃,“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然而“写罢低眉无处发”……不过一息尚存,我总是要想,也总是要写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为不学无术,……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2001年11月12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呼声,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是在极权高压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论空间。看到这点,还是令人高兴。”(2002年10月14日)这是对知己的直言,也是内心的独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夸父逐日般的现象。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反复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是真诚的,对他参与建构的这个体制、他深爱的这个民族、对历史和现实,他都有着冷静、客观的认识:
“但是中国的传统,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传统,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实在是夜长梦多。这就是我所以慨叹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觉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1976—77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全民对民主的常识几乎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问题,民主实际上要[依]有相互对立与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团,有敢于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又能够达成妥协的个人,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么时候能够破壳而出,我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都像胡适所说‘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当然也有些乐观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具体化的、现实的根据。
我自以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极少数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万恶统治下”多少还受到过一些启蒙思想,历经劫难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这极少数之内。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对民主的理论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来,到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可以说靠自学,靠自己反思成为启蒙思想家的人,现在中国就是靠他们在学术界撑起一片天。然而这片天实在太小,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我现在确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我‘为’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过写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7月4日)
我同意中国今天的社会条件比起国民党时代、五四时代以及晚清时代大概是大大地进步了,所谓进步指的是可以实行民主的社会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总觉得有觉悟的人太少了。撇开我心目中的“官学”和“极左派”不说,九十年代也出来了一批‘民族主义分子’和‘新左派’,他们的嗓门很大,听众甚多,……而民族主义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与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极容易赢得群众。事实上从各种民意调查中看,这批人在青年学生中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就主要从爱国主义出发,才走向亲共、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上了一个大当的。其实世界在20世纪已发生了大变化。自由主义已肯定地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而中国却仍然置身于这一主流价值之外(就政府行为讲还很显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说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铁的规律的话,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进民族由于种种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经验,成为大家的榜样之后,大家必须要学习,而形成一条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走人类必由之路”)的话,我还是相信的,然而夜长梦多,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从美国归来后写给许良英的第一封信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内儒外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
9月6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20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HAVEL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21世纪末,或者22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1840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20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2000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10页纸的长信给许先生,表示自己早几年就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并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见写下来:“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他认为1949年以后的30年,“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看作是他对整个百年中国的最后认识。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他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正如他2001年4月21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57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同年6月29日,他回顾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认为主要来自少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而朦胧 的平等思想。他入党虽晚,却历来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从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产党人、陆定一的丈人严朴。与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实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虽然搞学生运动时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别人起劲,“我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参加党的”。当然,他毕竟是手上没有沾过血的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踏上这条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不能简单论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讲到自己的“彻底觉悟”:
从“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来是一个“红干部”,但是还是划了右派。头两年,我在思想深处竭力要说服自己,只有党对,不容我对,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彻底觉悟了。我用了《封神榜》里哪咤的一句话对自己说:“削骨还父,削肉还娘”。我看到有许多人当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论罪),就思想而论,我是真右派,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说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讲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后即明白自己确是右派分子,与毛主席的思想是针锋相对,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干校时我没有把马恩列斯全集都带走,而是尽量搜罗单行本带走,供“天天读”之用,但精神上是为了“脱魅”。
“我对毛的崇拜前后也有二十年。后来自以为觉悟算早的,但是,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幼稚。毛其实本质上与他晚年(批林时)自许的‘哥儿们’——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并无二致,不过是靠了所谓马列主义骗过了我们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们又是根本没有经历过个性解放的体验的人,也不可能识破他那一套(从本质上说毛和我们都还是传统中人),结果个人和国家都吃了极大的苦头,走了极大的弯路,因此,下一篇我想从毛的草头天子的本质来写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借尸还魂,变本加厉的,只是,那样写出来,更无处发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说,正因为自己在1960年就已“彻底觉悟”,所以整个80年代他几乎不着一字,原因就是当时他熟悉的知识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讨论“社会主义民主”,讨论改良计划经济,“而我则自从60年代觉悟后,实在不愿写违心的文章(当然,我深知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的,不是违心的),90年代以后越来越宽松,才开始打些擦边球,我去年估计今年还会宽松些,不料大错特错,反而出了义和团来,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过,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80年代不着一字的另有一个主要原因乃是“胆小”。1999年他写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写的《李慎之自述》中说得很坦诚:“我还是一个胆小鬼。80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90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页)
这一点他在2002年1月写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自剖,80年代,当王若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遭到整肃时,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辩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最后发表时删去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这一句。(同上,575页)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变化应该是1999年,这是他的整个人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与他自述心迹时所说的1960年的“彻底觉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肯定传统文化的“半个新儒家”转而作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的重要论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噤若寒蝉”的“胆小鬼”变成了登高一呼的斗士,最终超越了恐惧和自我恐惧,写出了感动千万读者、也赢得了极大声誉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这一年起,他从80年代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之争转向普遍关注国内外的思想动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认为那不仅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575页)许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给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整个80年代影响较大的还有民主与专制思想(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预等等。也正是这一年开始,这个不断自称“极度孤独”、“无边孤独”的老人实际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认为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岁的知识分子党员启蒙—起信—革命的历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页)顾准无疑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过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转型的人,所以他才会如此推崇顾准:
我对顾准估计是很高的……顾准是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几乎走完全过程的,因此他的觉悟特别可贵,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也特别大。你也知道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结论居然是“痛苦地”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这二十多年来我也接触过党内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没有一个达到顾准的标准的,从胡耀邦到孙冶方到王若水。(也许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说。)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者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我是相信传统的力量的。就是所谓“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国不足百年,根子还没有扎下就被灭绝五十年,现在也还说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后一定会出现以民主为目标的思想家,也必须要高扬顾准承前启后,存亡续绝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说,我的第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识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青年时就没有做过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几年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些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楡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月30日)
他的这番话是悲怆而真诚的,其中同样弥漫着悲凉的气氛。相比之下许良英“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顾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华洋溢的李慎之对他同时代的许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与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里说:“我自认为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倘能经常向你请教,(在这方面,事实上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识,而常识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对许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满敬意,一而再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见到他,他也曾当面跟我说起)。2002年1月21日他给许的信中说:“我十分钦佩你研究民主的学术著作,十年二十年后必然成为‘国民必读’。”5月18日:“应该说我现在觉得你真是可钦可佩,年近八十还下决心研究民主的历史,以你现在的身体精神看,这个任务是绝对可以完成的。我在几年前说过要编一套中学公民教科书的话,说实在的,我并无自己着手来干的计划,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别人。总觉得年纪老了,此生无望。现在看看后生也没有人认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样,在几年前就干起来,也许有生之年还能干出些成绩来。但是话虽如此说,我到现在还是下不了决心,心中总觉得还有几篇文章可写,写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岁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在杭州见到李先生,他曾当面主动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说,“在我朋友中,我认为只有你一个人虽然似乎觉悟稍晚而见机甚早,并且全身心投入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研究,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后一定可以完成。这点是我对你极其钦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过)而迄今没有志气与信心向你学习的。”
五
李慎之晚年对这个时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他对邓小平、周恩来、胡乔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难以泯灭,这是他的局限,也许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毕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身上带有许多这个特定时代给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动海内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虽然指出邓调动部队的“无可饶恕的罪过”,但他同时也说:“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页),他的笔端对邓还是含有温情,其中无疑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当中乃至标题(如《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泽东时,基本上都是称“毛主席”,经许良英指出,他的解释是他之称毛为“毛主席”是一种习惯,“我的意思是人们称嬴政为秦始皇一样”(1998年11月11日)
对周恩来,他更是敬重有加,笔下总是称“总理”或“周总理”。对于批评周恩来的声音,他是很不满意的,在他谢世前不久,我曾听他说过,如果有时间他要写万言长文反驳,并问过我人家是怎么批评周恩来的。
称呼有时候确是颇能反映心迹的,特别是在回忆文章中。1997年他写过一篇《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提到胡乔木时至少有17处称“乔木同志”、4处称“乔木”、4处称“乔公”,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乔木好的一面。这一点在几年之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中有所改变,几次提及胡乔木后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页)可见他的认识还在变化中。
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国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1979年他曾是邓小平访美时的顾问,80年代正是胡乔木提拔他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乃至副院长。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忆,他谈起80年代邓小平要他定期去讲国际形势,言语之间显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随同李慎之出国访问的一位科学家清楚地记得,那时他说话的口气都是代表官方的,给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虽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彻底觉悟”,但在整个80年代邓小平、胡乔木等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都是旁观者,始终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么关心。其中原因固然与他自称是“噤若寒蝉“的“胆小鬼”有关,是不是与他对当时地位、处境的得意有关呢?
他晚年之所以对邓、对胡都有着“同情之理解”,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对他的重用、提拔,对这种知遇之恩他难于忘怀,正是这样的心理使他难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羁绊。其中就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知恩图报这些观念在起作用,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毕竟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最后否定了文化传统,但作为“半个新儒家”要从根本上超越这些观念又谈何容易。对此,我想我们也只能对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筹,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负,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许表示“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后说:“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他曾多次慨叹爱国志士稀少,他在世纪末的呼喊回音空荡。无边的孤独感笼罩着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对比他年长三岁的许良英说:“我有时很为我们的年老与孤独感到有些沮丧,因此找你说说。”
从1999年以来,他不断地在给许良英的信中表达这种“极度的孤独”感,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华、经历所导致的自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仅此还不足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实际上自从《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阳纸贵之后,举世仰慕、以结识他为荣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他还有着着的孤独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说,“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无力感,觉得“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我写过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两个人响应,其中一位是与我同年的76岁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难受,然而也还是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干下去。”
不过据苏绍智回忆,李慎之在1999年回国前,特地去看望了他,两人畅谈了一整天,他们有着二十年的友谊,苏显然不是李所说的“利禄之徒”,否则他也不会专程去找他,并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后,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就写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与他有深交的。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感到孤独?
1999年9月6日,在谈到自己美国之行的感受时,他在信中说:“我年轻时最推重鲁迅,而有点看不上胡适,这点我现在承认是错了。然而,十年来,我几次去美国,住的时间将近十[月],跑了几十个城市,十几所大学,竟没有看到一个可与胡适相比的留学生,虽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说自己孤独,其实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或许是他本人没有察觉,他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国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欢夸张的表达方式等都对他的内心所产生的细微影响。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但在世纪之交他们持续五年多的通信中,我们处处都能体会到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诚挚、坦荡、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找到了共识,他们都肯定了启蒙的重要性,启蒙首先是启知识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将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着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不过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传教育的空间,可以努力‘改造国民性’了。”毫无疑问,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并不是自大,而是一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负,这一切使他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一种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怆感,也使他晚年笼罩在一层只有远古神话中才有的那种无比豪迈又无比朴实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氛围之中。他做一个“公民教员”的志愿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长存于这个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
[转载]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
独裁者排行榜(转)
图解: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转载]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左宗…
[转载]惊人遗嘱藏保险箱81年 …
[转载]国民奴性的临床表现
[转载]学习研究:试析1972年毛…
[转载]档案解密:毛泽东与尼克松会…
[转载]日本“无条件投降”幕后真相
太押韵了,写的真是绝了!(转)
中国百年历史人物照片 (转)
成语归类(值得收藏)
[转载]孙立平:下半年中国政局将有…
[转载]将才与帅才的十二个差异
[转载]历史研究:瞿秋白与《多余的…
[转载]历史资料:瞿秋白:《多余的…
[转载]文革揭秘:“二月兵变”真相
[转载]大 事 记: …
曾国藩处世36字决
[转载]金敬迈文革中(68年)被抓原…
[转载]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三封遗…
[转载](原创)开国前后最全任职资料
新“好了歌”
[转载]中国历史上被毒死的二十位皇…
做个打不倒的人(转)
[转载]改革意识形态的重大步骤
[转载]中国近代十大最令人爱戴人物
[转载]54张扑克展示古代名人
[转载]毛泽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
[转载]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
[转载]你没见过的50个世界历史瞬间…
7月9日沪指创近七年最大单日涨幅
公安部25年来首次高调“救市” …
[转载]影响中国的100位现代高层智…
蒋中正指挥的22次抗日大会战
[转载]揭秘:中国高层领导的子女现…
[转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转载]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
[转载]老大哥的靴子
[转载]大裤衩里消失的名人
[转载]改变中国历史的十次宫廷政变
高中口诀 初中口诀(珍藏版)
[转载]中国的1300余万黑户该何去何…
[转载]中國和加拿大貪官,一比嚇一…
朱普乐:毛时代的衣食住行
[转载]1923年蒋介石访苏为何败兴而…
[转载]是谁整倒四大野战军的军事指…
[转载]日本海军致丁汝昌的劝降书|…
[转载]转: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民族…
[转载]习近平讲话引用的古语名言50…
[转载]“推翻三座大山”正传
[转载]《读者》杂志十年精彩卷首语…
[转载]《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
[转载]李承鹏:看的见的台湾
红朝前七子与后七子(推荐转发)
人生有度,误在失度,坏在过度,好…
[转载]不太被注意的四个社会主义国…
[转载]备查资料-中国共产党及我国…
[转载]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明细表
[转载]分享电子图书:一部完整的《…
[转载]解密:1975年毛泽东为何违心…
一张图帮你读懂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
[转载]严锋:五十年代那些“很黄很…
毛泽东27位秘书的结局(转载)
[转载]文革时中共高层的一组照片
[转载]WTO贸易保护到期:变化已轰…
[转载]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
[转载]傅国涌:告别屈原人格
[转载]“四人帮”垮台后 为何没…
[转载]中国的十大奇特工程
[转载]50年前毛刘冲突,他们都说了…
[转载]汉族DNA研究得出惊人秘密
[转载]中华民国历任国家元首和政府…
[转载]被历史雪藏百年的三大中共元…
李克强: 收回2500多亿元用于…
[转载]蒋介石对近代中国的功绩
[转载][转发]人的“三、六、九等”是…
[转载]抗日战争国共双方各杀敌多少…
[转载]杨连宁:薄熙来背后是谁在受…
中国最美的100句诗
[转载]历史沉浮:反“江西罗明路线”…
中国千年遗训100句
[转载]凡是为苦难作赞歌的人都是伪…
[转载]階級鬥爭又來了!這回要專誰…
[转载]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
[转载]精选古代诗词名句900句简析
[转载]中纪委下半年要干哪些大事?
[转载]口头语泄露哪些心理秘密
[转载]从春秋到明清中华民族是如何…
[转载]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
[转载]曾国藩:社会大乱之前 …
[转载]昔日的新华日报
[转载]美到极致的文字
[转载]因为写得太经典·所以转了
[转载]中国式谎言(太有才了)
[转载]退休者必读,未退休者参考
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饱…
[转载]“老机关”谈“机关八忌”
[转载]习大大说了有事就给他打电话…
朱柏庐治家格言
千古奇文《寒窑赋》
[转载]中国最大的特色
[转载]世界十大恶书榜
习主席的七句话,已传遍全国
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片段
[转载]杨成武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讲…
[转载]世界上有多少社会主义国家?
[转载]所谓亡党亡国,最典型的例子…
[转载]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
[转载]抗战中,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
[转载]● 历史的真相:…
[转载]白瑜:亲历台湾土改
[转载]拿什么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精…
[转载]马英九七七讲话:尘封多年的…
[转载]精辟啊!看了,你就喜欢!
[转载]盘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十…
[转载]改革之星——新中国60年60位改…
中国十大禁片
[转载]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
[转载]戊戌变法代表人物
[转载]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转载]影响中国的100位现代高层智…
[转载]影响世界进程的100人
[转载]100年变了什么?
[转载]中国近代以来的九首国歌
人生法则108条(转)
[转载]处世大全, 看完真的服了
[转载]中国十大秘抄本
[转载]毛泽东为何决心将华国锋作为…
[转载]朝鲜砸毛岸英墓内情:文革红…
65个生活细节决定人生成败(转)
[转载]人生顺利的四大法宝
1921年中共党员名录(126人)
[转载]张鸣:教科书的梦魇
[转载]中美俄朝韩五国教科书上如何…
回望血与火的十大战场
有多少“抗战遗址”还被遗忘
永不忘却“醒狮”的呐喊
“七七事变”78周年重读抗战家书
新华网将推出3D动新闻《七七事变》
[转载]十大谎言
[转载]【不是历史 历史从不宽…
[转载]延续晚清灭亡命运的四大汉臣…
[转载]中国历史上一百个传奇女人
[转载]郎遥远:中国权力场人鬼难分
[转载]郭沫若给斯大林的祝寿词全文
[转载]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希望!
[转载]习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转载]ISIS的前辈们所创下的红色恐…
[转载]蒋介石的工资与民国时代的工…
[转载]中国当前面临的八大危机
[转载]1945年蒋介石抗战胜利讲话-…
[转载]【转载】被丑化的历史人物
[转载]中国古代八大名赋
[转载]人类文明的特征
[转载]台湾历史教科书如何讲述中国…
[转载]李作鹏晚年怒揭周恩来:当年…
[转载]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转载]倒霉的老朋友...
人生二百“最“(转)
[转载][转载] 历 史
[转载]古诗词中蕴含的哲理
[转载]触目惊心!挡内有鬼!已成立…
[转载]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希望!
[转载]毛泽东思想的两大逻辑基础
盘点中国本土禁片知多少
[转载]中国人民发声了!十问人民日…
[转载]俄罗斯终于承认:列宁到底是…
[转载][转载]认清毛左分子
[转载]毛泽东“雷语”大集结,试试看…
[转载]爱自己的十一种方法
[转载]老一代革命家反思毛氏专制体…
[转载]盘点奴性思想和行为
[转载]看看真实的鲁迅:淞沪抗战&n…
[转载]宪法宣誓下一站,宪法监督
[转载]一堂深刻的民主政治课:少数…
[转载]太惊人了?世界各国社会福利…
[转载]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国民党…
[转载][转载]师哲回忆录
[转载]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七位老师
《南风窗》:解读边疆
[转载]马云说:远离这四种连狗都不…
[转载]林彪事件中的神秘汪东兴
中国土司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nbs…
[转载]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
[转载]“左”派“右”派的共识与分歧…
[转载]李智海编发:权势宣传的鲁迅…
[转载]看你的工资和国际接轨了没有…
[转载]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希望!
[转载]李克强怒拍桌子质问副部长父…
[转载]鉴别国家优劣的方法
“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
[转载]“文化大革命”内幕
[转载]【中华传统节日资料大全】
[转载][转发]这些人民币,您都认识…
[转载]1971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转载]外蒙古独立真相震撼曝光&nbs…
[转载]100种人生
[转载]记住这十句话,你就记住了中…
影响你一生的30个做人智慧
[转载]中国王朝灭亡的方式统计
[转载]中国近代各省军阀名单
独裁者排行榜(转)
世界各国独裁者名单
20世纪的几大独裁者排行榜
常用文学典故解释
[转载]【转载】极其珍贵的60张历史…
[转载]毛泽东逝世我没拍到人们悲恸…
[转载]曾经的马克思主义信徒默克尔…
[转载]社会主义的历史
[转载]宋亡之后文明的十二大逆转
[转载]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将领 …
[转载]好消息!7月出版的《炎黄春…
[转载]刚刚流出来的民国的照片,原…
[转载]亚洲周刊专访郝伯村
[转载]王文华:传国务院下午召集救…
[转载]郝柏村:中国应在22个抗日大…
[转载]一寸山河一寸血 之开篇… 2
[转载]一寸山河一寸血 之开篇… 1
[转载]一寸山河一寸血之 难忘硝烟
[转载]中考历史专题复习资料(9个…
[转载]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