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人来说,功利主义是一种著名的常识性哲学。当面对道德困境,最自然的问题莫过于:“我做什么将会为绝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倘若你将之作为你行动的标准,那么你就在践行功利主义。
不过,功利性标准的实际运用非常困难,有时造成戏剧性效果。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
他看到一艘救生艇在三百码开外漂泊着。那是一艘小船,上面有五六个水手。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大船。
“救命!”哈德森叫道,“救我,在这里。”
一束光闪烁着。那道光打到了安德里亚·多利亚号的船尾。在哈德森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的导引下,光束集中到靠着网的沮丧的水手身上。
“救我!”哈德森再一次叫道,“快点!快!”
哈德森等待着人们能挥动他们的桨。他奋力地摆脱着变动的潮流,用尽全力让来救他们的人看见。
但是救生艇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救命!”哈德森又叫起来。“请快一点!”
救生艇依然静静地躺在水面上。光束再一次照花了他的双眼。他们看见他了,他们听到他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来?我的天啦!哈德森意识到,船现在正在下沉……!在他进行海上商业航行的培训中,哈德森学到救生艇必须保持与大船三百码的距离,避免被拖入到沉船的漩涡当中。那就是为什么救生艇与大船保持三百码的距离的原因……
他沉默了一会,骑在凸起部位上,等待着最终结局。一轮橘红色的太阳从他身后升起,新的一天嘲弄这悲剧的发生。安德里亚·多利亚号不再是水平地而是垂直地立在水面上。桌椅,沙发,衣物的碎片,断裂的木头在海面上随波飘荡。当船一点一点地沉入海底时,哈德森在一张网上往上爬。
他又卯足了劲。“救命!”他声嘶力竭地叫道:“请过来带我走。你们不能看着我死去。”
他几乎可以看到那些水手在救生艇上看着他。但他们没有划过来。
那个绝望的人只能再一次大声咒骂。之后他开始祈祷,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向救生艇上的人祈求。他叫喊着,祈求着。[1]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有可能救一个人而甘冒几个人生命的风险吗?这真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我们通过三步来了解功利主义的真正本质。第一步,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功用原则。“功用”的意思就是“有用性”,功利主义用这个词的意义在于扬善抑恶的达到最大平衡。功利主义即:
1.我们应该如此行动,扬善抑恶的达到最大平衡。
但这还不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善为何物。事实上,第二步在于,功利主义通常与享乐主义携手与共,享乐主义将善的本质特殊化了。享乐主义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善,而快乐的生产就是正确的行为标准。这样,功利主义即:
2.我们应该如此行动,宣扬快乐,抑制痛苦,达到最大平衡。
但这还是不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要将谁的快乐最大化。事实上,第三步,功利主义(就像这个词的通俗意义)尤其是与社会享乐主义同气连枝,这个理论指出,我们应该增进社会的善,或者说,所有人的快乐。这样,功利主义的动机并非自利,而是一种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其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满足。功利主义依赖于仁慈原则:幸福尽可能在所有人那里广泛而平等地分配。这样,最终功利主义即:
3. 我们应该如此行动,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
很明显,功利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也是一种哲学立场。作为一种民主的观念,多年以来,他成为立法和司法进步,社会改革,福利运动,以及平等理念的基础。毋庸置疑,最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通常也会深入地参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站在自由的立场上,显然如此。
在历史上,最著名的社会功利主义者是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我们发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对象都是一些著名的天才人物,边沁8岁学习拉丁语,而密尔3岁就开始学习古希腊语!)。不过,这两位思想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功利主义形式,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一个人强调的是幸福的量,而另一个人强调的是幸福的质。
现代功利主义的奠基者是杰里米·边沁(1748-1832)。对于边沁而言,做出道德决定的过程相当简单。你所需做的不过如此:首先,考察一下你所面对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其次,考察一下所有人的感受,最后,选择那个可以让宣扬,抑制痛苦,达到最大平衡的行为。
我们已经指出,变迁强调的是宣扬快乐,抑制痛苦,达到最大的平衡。那么他的快乐观就是一个纯粹的量。最大数量的最大快乐,对边沁而言,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事实上,边沁的量化的快乐观来源于其著名的论述:
摒弃偏见,图钉游戏会与音乐和诗歌的艺术和科学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图钉游戏能够带来快乐,它就会比其他东西更有价值。[2]
怎么判定最大的快乐?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观念,最清晰地体现在边沁的享乐计算(hedoniccalculus)中。按照边沁的说法,为了计算快乐,我们必须用七种方式来考察快乐:
1.强度,即其有多强烈。
2.持久时间,即其持续多长时间。
3.确定性,即其发生的几率有多高。
4.邻近性,即其多么接近它。
5.丰度,其是否有可能带来更多快乐。
6.纯度,其摆脱痛苦的自由能力。
7.广度,有多少人会受到其影响。
边沁指出,下面的口诀可以看成是“整个道德和立法大厦的基石”:
强烈经久确定,迅速丰裕纯粹,
无论大苦大乐,总有此番特征。
倘若图谋私利,便应追求此乐。
倘若旨在公益,泽广即是美德。
凡被视为苦者,避之竭尽全力,
要是苦必降临,须防殃及众人。[3]
在采用了这七个标准之后——一些人将其等同于道德的晴雨表——我们应该可以像一台机器一样得出,什么样的行为可以传递出最大的快乐。边沁自己谈到了“综合所有快乐的所有价值”。并非是要我们总是能够、必须投入到这样的快乐算术中。另一方面,难道我们所有人不是总会采用某中方法,无论其多么粗糙,每一次我们都会去考量一个决策的行为快乐和痛苦的成分?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边沁提出了我们知道什么与我们应当做什么之间的区别。当他人的幸福意味着你的自我牺牲和痛苦的时候(用一个之前用过的词,心理学自我主义者),尤为如此。在这里,边沁提出了四种约束力的学说:自然、法律、意见和上帝。借助这些约束力,边沁的意思是存在某种具有强制力和威胁的东西,要将这四种约束力看成伦理行为的动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自然规律、市民社会的法律、公共和人们的意见、以及上帝本社你都会让我们不快——要么在我们的一生中,要么在我们的下一代中,或者两者兼具!自然、法律、意见、上帝“劝诫”我们克服我们天生的爱好,并按照社会功利的价值行动。边沁也将四个约束力称为自然约束力、政治约束力、道德约束力和宗教约束力。但无论如何,他提出的例子足以说明他的意思:
假设一个人的财产或身体被火吞噬。如果他遭此厄运是由于所谓的事故,那就是灾祸;如果是由于他自己的不慎(例如忘了熄灭蜡烛),便可称为自然约束力的惩罚;如果是政治官员的判决使他如此,那就是属于政治约束力的惩罚,即通常所谓的惩罚;如果是由于他的邻人对他的道德品格有所不悦而不给任何帮助,那么蒙受火难便是道德约束力的惩罚;如果是由于他犯下某种罪孽,或因惧怕天谴而心烦意乱,以致招来由直接责罚表现的神怒,那便是宗教约束力的惩罚。
至于宗教约束力范围内那些关于来世的快乐和痛苦,我们无法知道可能是什么样的。这些并非人所能见。[5]
尽管边沁是现代功利主义的奠基者,但是他的后辈才是所有功利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
密尔的小书《功利主义》是哲学的经典文本。此外,难以想象的,这本书清晰地表达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哲学观念。我们看一下他关于功利主义的享乐性本质的论述:
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做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行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要清楚地揭示这个理论所建立的道德标准,还有很多东西要说,特别是要说明,痛苦和快乐的观念究竟包含了哪些偶那个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不过,这些补充说明并不影响到这种道德理论所根据的人生理论——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追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它们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与在其他任何理论中一样为数众多)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6]
再看一下他对于功利主义的社会性本质的论述:
我必须重申,构成功利主义的行为对错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而这一点是攻击功利主义的人很少公平地予以承认的。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在他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应当像一个公正无私的仁慈的旁观者那样,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全部精神,可见之于拿撒勒的耶稣所说的为人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邻若爱己”,构成了功利主义的完美理想。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理想,功利主义要求,首先,法律和社会的安排,应当使每一个人在内心把他自己的幸福,与社会整体的福利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尤其要把他自己的幸福,与践行公众幸福所要求的各种积极的消极的行为方式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结果不仅要使得任何人斗无法设想,自己的幸福竟然会与危害公众福利的行为相一致,而且要让促进公众福利的直接冲动,存在于所有的习惯性行为动机之中,并让与之相关的情感,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活动中都占有一个大而突出的位置。[7]
边沁和密尔都将功利原则作为仁慈原则的论证:当且仅当行为产生了快乐和幸福或者需要的满足,且这些快乐、幸福或满足尽可能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时,行为才是正确的。和边沁一样,密尔也赞同社会性功利主义的基础不能被证明,至少在我们通常的意义上无法被证明:
……终极目的的问题是无法在证明一词的日常意义上得到证明的。一切第一原理,我们知识的第一前提以及我们行为的第一前提,都是无法得到推理性的证明的。[8]
另一方面,还是有些证据的:
能够证明一个对象可以看到的唯一证据,是人们实际上看见了它,能够证明一种声音可以听见的唯一证据,是人们听到了它,关于其他经验来源的证明,也是如此。与此类似,我以为,要证明任何东西值得欲求,唯一可能的证据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9]
在引述的这些文字的基础上,一些读者或许认为,密尔陷入了伦理主观主义:如果一些人并不欲求幸福,那么对他而言,是否并不意味着幸福不值得追求?需要弄清楚的是,密尔用另一个问题对此做出了回答:如果有人看不到 一个东西,那是否意味着那东西就看不见?善可以作为幸福,但这很难得出,善在脱离了感受它的经验之外,就没有客观的真实性了。强调一遍,密尔和边沁等其他享乐主义者一样,都是伦理学中的客观主义者。我们会看到,上面的引文中的真正的问题并非如此。
密尔同边沁分道扬镳的地方是他不同意边沁的快乐的纯粹量的观点。但密尔并不否认量在快乐计算中的作用,他更相信的毋宁是量的作用要低于质的作用。
可是这样的人生理论引起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反感,其中有些人还怀有最值得尊敬的感情和意图。他们认为,如果一味生活(如他们所说)的最高目的便是快乐,除快乐之外没有更好更高尚的追求对象了,那是全然卑鄙无耻的想法,是一种仅仅配得上猪的学说。很早以前,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就被轻蔑地比作猪,而在现代,主张功利主义学说的人也时常成为德国,法国和英国抨击者们同样不可的讽喻对象。
伊壁鸠鲁学派的人受到这样的攻击时,总是回答说,把人性说的堕落不堪的人不是他们自己,而正是那些指责他们的人,因为这种指责假定,除了猪所能享有的那些快乐之外,人类再无其他的快乐能够享受了。如果这种假定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指责虽然无法反驳,却也因此不再是一种非难了,因为,假如快乐的源泉对于人和猪来说完全是相同的,那么对于猪来说是足够好的生活规则,对于人来说也将是足够好的。人们之所以感到,将伊壁鸠鲁派的生活比作禽兽的生活是一种贬抑,正是因为禽兽的快乐是说明不了人类的幸福概念的。人类具有的官能要高于动物的欲望,当这些官能一旦被人意识到之后,那么只要这些官能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不会感到幸福。
当然,我并不认为伊壁鸠鲁学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所得出的理论体系是毫无差错的。任何比较充分的理论,都还需要包括许多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的成分。但就我们所知,伊壁鸠鲁的人生理论中没有一点不认为,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作家一般都将心灵的快乐置于肉体的快乐至上,主要是因为心灵的快乐更加持有,更加有保障,成本更小——也就是说,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外在优点而不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内在本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功利主义者都已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们本可以完全自洽地采纳其他的也许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论据。承认某些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追求,更有价值,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荒谬的倒是,我们在评估其他各种事物时,质量和数量都是考虑的因素,然而在评估各种快乐的时候,有人却认为只需考虑数量这一个因素。[10]
对于密尔而言,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手,很难说,尽管图钉游戏比诗歌更快乐,但绝不意味着其从属于低级的幸福。性快感能够与理智的快感相提并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或者用密尔的话说,难道你宁可做个满足的猪,而不愿做个不满的人,或者说,宁可做个满足的傻子,而不愿做不满的苏格拉底?对于密尔而言(边沁亦是如此),值得追求的行为就是为了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然而,对于边沁来说,“最大多数”的意思是数量上的多,而对于密尔,则是质量上的最好。
[1] William Hoffer, Saved! The Story of the “ AndreaDoria”—The Greatest SeaRescue in Histor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79,pp. 180-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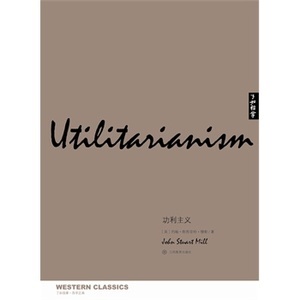
[2] Jeremy Benthem, The Rationale of Reward, inThe Works of JeremyBentham. Edinburgh: Tait, 1838-1843, II, I,253.
[3]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6页。
[4]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9页。
[5]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3-84页。
[6] 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第7页。
[7] 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第17-18页。
[8] 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第35页。
[9] 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第35页。
[10] 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年版,第7-9页。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