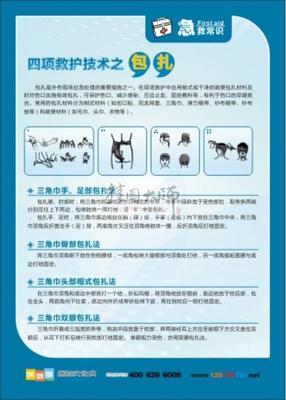从佛教的立场来讨论楞严,很久以前就有二个预言流传着。预言楞严经在所有佛经中是最后流传到中国的。而当佛法衰微时,它又是最先失传的。这是寓言,或是神话,姑且不去管它。但在西风东渐以后,学术界的一股疑古风气,恰与外国人处心积虑来破坏中国文化的意向相呼应。楞严与其他几部著名的佛经,如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便最先受到怀疑。民国初年,有人指出楞严是一部伪经。不过还只是说它是伪托佛说,对于真理内容,却没有轻议。可是近年有些新时代的佛学研究者,竟干脆认为楞严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和印度的一种外道的学理相同。讲学论道,一定会有争端,固然人能修养到圆融无碍,无学无争,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但是为了本经的伟大价值,使人有不能己于言者。
说楞严是伪经的,近代由梁启超提出,他认为第一:本经译文体裁的美妙,和说理的透辟,都不同于其他佛经,可能是后世禅师们所伪造。而且执笔的房融,是武则天当政时遭贬的宰相。武氏好佛,曾有伪造大云经的事例。房融可能为了阿附其好,所以才奉上翻译的楞严经,为的是重邀宠信。此经呈上武氏以后,一直被收藏于内廷,当时民间并未流通,所以说其为伪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楞严经中谈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种仙,梁氏认为根本就是有意驳斥道教的神仙,因为该经所说的仙道内容,与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梁氏是当时的权威学者,素为世人所崇敬。他一举此说,随声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对此说者也很多,不过都是一鳞半爪的片段意见。民国四十二年学术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载有罗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粤笔受首楞严经翻译考一文。列举考证资料很多,态度与论证,.也都很平实,足可为这一重学案的辨证资料。
我认为梁氏的说法,事实上过于臆测与武断。因为梁氏对佛法的研究,为时较晚,并无深刻的工夫和造诣。试读谭嗣同全集里所载的任公对谭公诗词关于佛学的注释便知。本经译者房融,是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族系,房氏族对于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师回国后的译经事业,唐太宗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房融对于佛法的造诣和文学的修养,家学渊源,其所译经文自较他经为优美,乃是很自然的事,倘因此就指斥他为阿谀武氏而伪造楞严,未免轻率人人于罪,那是万万不可的。与其说楞严辞句太美,有伪造的嫌疑,毋宁说译者太过重于文学修辞,不免有些地方过于古奥。依照梁氏第一点来说:我们都知道藏文的佛经,在初唐时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并非取材于内地的中文佛经。藏文佛经里,却有楞严经的译本。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也就是楞严咒的一部分。这对于梁氏的第一点怀疑,可以说是很有力的解答。至于说楞严经中所说的十种仙,相同于道教的神仙,那是因为梁氏没有研究过印度婆罗门和瑜伽术的修炼方法,中国的神仙方士之术,一部分与这两种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是否是殊途同归,这又是学术上的大问题,不必在此讨论。但是仙人的名称及事实,和罗汉这个名词一样,并不是释迦佛所创立。在佛教之先,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和瑜伽士们,己经早有阿罗汉或仙人的名称存在,译者就我们传统文化,即以仙人名之,犹如唐人译称佛为大觉金仙一样,绝不可以将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实者,都拉为我们文化的特产。这对于梁氏所提出的第二点,也是很有力的驳斥。而且就治学方法来说,疑古自必须考据,但是偏重或迷信于考据,则有时会发生很大的错误和过失。考据是一种死的方法,它依赖于或然性的陈年往迹,而又根据变动无常的人心思想去推断。人们自己日常的言行和亲历的事物,因时间空间世事的变迁,还会随时随地走了样,何况要远追昔人的陈迹,以现代观念去判断环境不同的古人呢?人们可以从考据方法中求得某一种智识,但是智慧并不必从考据中得来,它是要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的。如果拼命去钻考据的牛角尖,很可能流于矫枉过正之弊。说楞严经是真常唯心论的外道理论,这是晚近二三十年中新佛学研究源的论调。特此论者只是在研究佛学,而并非实验修持佛法。他们把佛学当作学术思想来研究,却忽略了有如科学实验的修证精神。而且这些理论,大多是根据日本式的佛学思想路线而来,在日本,真正佛法的精神早已变质。学佛的人为了避重就轻,曲学取巧,竟自舍本逐末,实在是不智之甚。其中有些甚至说禅宗也是根据真常唯心论,同样属于种我外道的见解。实际上,禅宗重在证悟自住,并不是证得神我。这些不值一辩,明眼人自知审择。楞严的确说出一个常住真心,但是它也明白解说了那是为的有别于妄心而勉强假设的,随着假设,立刻又提醒点破,只要仔细研究,就可以明白它的真义;举一个扼要的例来说:如本经佛说的偈语:"言妄显诸真,真妄同二妄。岂不是很所显的证明楞严并不是真常唯心论吗?总之,痴慢与疑,也正是佛说为大智慧解脱积重难返的障碍,如果纯粹站在哲学研究立场,自有他的辩证、怀疑、批判的看法。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就有些不同了。学佛的人若不首先虚心辨别,又不肯力行证验,只是人云亦云,实在是很危险的偏差。佛说在我法中出家,却来毁我正法,那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南怀瑾自叙于金粟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