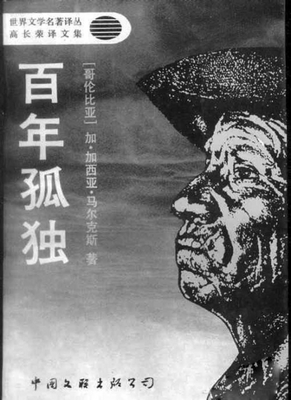我在《北京文学》打工的日子
白连春
1
我到《北京文学》第一天,没上班,只是参观,认识领导和同事。
章德宁社长和孟亚辉副主编对我很热情,前者要我第二天记得带饭碗,后者和我握手。杨晓升老师对我很冷淡,轻轻看我一眼。他在电脑前忙。杨老师是副主编,管原创版,当时《北京文学》只有原创版,叫编辑室。
章社长告诉我我归杨老师管,然而,杨老师对我很冷淡。我的心有些凉。
第一天,是否见过张颐雯和萧夏林,我忘了。反正,上班后,就见到了。我和张颐雯一见如故,成了朋友。萧夏林是编辑室主任,开始,对我很好。
那是2000年底,究竟11月还是12月,我忘了。
我只记得:我和贵州人代兴伟同一天到《北京文学》打工。代兴伟热爱音乐,揣着一颗要成为音乐人的梦想来到北京。
代兴伟分到发行部,当时,发行部只有代兴伟一个人,归副社长吴双明管。
很快,总编室主任朱吉余老师给我介绍了女朋友,一个新疆来北京的画家,三十岁,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小巧,漂亮。女画家和朱老师的新妻子是朋友。朱老师的新妻子最少年轻朱老师二十岁,黑龙江的。两个女孩曾一起租房。女画家很合我心意。我喜欢我未来的妻子是画家。
朱老师给我介绍女画家第二天,我和已经在《青年文学》做编辑最少两年的河南作家赵兰振见了面。无意中,赵兰振和我谈到艾滋病。他是医生,家在周口市,对艾滋病很了解。他说他的家乡发现了艾滋病,还说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牢牢记得他的话。他说艾滋病治不好,在全世界有泛滥的可能。我吓得不轻,哪敢告诉他我去过周口市,也卖过血。那晚,因为聊得太晚,赵兰振留我住下。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早早就离开了。
那时,艾滋病村是否发现,我不记得,这,要查实。但是,艾滋病在河南省肯定已经被发现了。我内心恐惧,给朱老师说,女画家很懒。我找了这样的理由,朱老师气得够戗。现在,朱老师,你知道我内心的苦楚了,你原谅我了吧?
赵兰振给我说了艾滋病,我不再和他接触,人多地方,尽量不去,公交车,更不坐。无论什么活动,能推就推,实在不能推,我才去。我手机也很少开,一般人找不到我。
2
编辑室三个人,萧夏林是主任,编辑只有张颐雯和我。萧夏林难相处,脾气大,曾经,他在我送审的一篇小说后面签的退稿理由是:小说很有特点,但是一般化。
看到他签了这样的理由,我不服,我找他,希望他能通过那篇小说。他把我骂一顿。我找杨老师,把小说和萧夏林签的理由都给杨老师看。杨老师看了,说,小说还可以,不是特别好。最后,为缓解我和萧夏林之间的矛盾,那篇小说最终没通过。
从此,萧夏林对我的意见大了,他怪我不该找杨老师。
萧夏林对张颐雯的意见更大,因为,在萧夏林来《北京文学》前,他和张颐雯的哥哥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张颐武,已经成了公开的敌人。讲起这事,萧夏林很激动,他说他要打张颐武。他还说他曾经打过张守仁。具体,萧夏林因为什么要打张颐武,又因为什么他打了张守仁,他对我说过,现在,我忘了。
萧夏林对我的意见大了后,再不和我说话。萧夏林对张颐雯的意见本来就更大。就这样,《北京文学》编辑室主任萧夏林,他手下两个编辑:张颐雯和我,我们都反对他。更为重要的是,萧夏林和杨老师处处对着干。在小小的编辑室,包括萧夏林本人,共四个人,萧夏林和三个人都处不好关系。萧夏林不得不离开编辑室。正赶上章德宁社长想成立一本选刊,萧夏林就到了章老师的选刊。原来的编辑室改叫原创版,新成立的选刊叫选刊版。
萧夏林到选刊版的同时,王童从《北京娱乐信报》来到《北京文学》。他当了社长助理,进了原创版。
以前,我处处受萧夏林欺负,王童来了,我处处受王童欺负了。在欺负我这件事上,王童比萧夏林更加有过而无不及。
比如,夏天热,王童开空调。我身体差,空调吹久了头痛,就到窗前,打开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为这事,王童找到杨老师,要杨老师开除我。王童说我是农民,不让他吹空调。王童指着杨老师,大声责问杨老师:为什么留着我这样的农民,还不让我滚回四川?
比如,河南省作者尉然,是张颐雯的作者,他经张颐雯编辑发表一篇小说后,不知道为什么投了一篇给我。尉然看得起我,把小说投给我。我当然得看了,小说写得不错,就送审了。杨老师通过了。这篇小说发表了,在我校对时,王童说,我抢了张颐雯的作者。我把尉然的小说校对完,为缓和这场纠纷,最终,发表出来,署的编辑是张颐雯。
现在,写出这件事,我对张颐雯没任何意见。我只是写出编辑部规则:任何编辑都很宝贝自己的作者,因为作者是编辑的饭碗。然而,王童本人则可以任意抢别人的作者。比如,获了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蒋韵本是张颐雯的作者,结果,被王童抢走了。蒋韵老师那篇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心爱的树》,本应归张颐雯编辑的,被王童抢走,归了王童。蒋韵老师觉得对不起张颐雯,后来的小说都主动给张颐雯,王童再抢也不给王童了。有一次,刘庆邦老师给我一篇小说,王童找到刘老师,责备刘老师的小说不该给我这个打工者,应该给他,他是社长助理。
在此,必须写出:王童不看自然来稿。他只看名家稿子。自然来稿都是我和张颐雯看。杨老师照顾我,为多给我发钱,让我比张颐雯多看一倍自然来稿。就是说,每个月,如果张颐雯看500封,我就看1000封。
看自然来稿的结果是:100封里还挑不出一篇可以送审的稿子。
3
我和贵州人代兴伟在《北京文学》打了不知道多久工后,《北京文学》为方便我们更好地打工,把一间原本是仓库的地下二层的地下室清出来,让我和代兴伟住。必须说明:这时《北京文学》全体员工,包括领导都在地下一层办公。
代兴伟身体比我结实很多,他比我矮比我胖比我白,搬进地下二层时,我选了靠窗的位置,自从听了赵兰振的话,我对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很怀疑,总觉得地下二层,空气更不够。而且,我占了仓库里仅有一张床。那是张小铁床。我一看见就爱上了。从此,我一直睡这张小铁床。在北京,我搬了无数次家,都睡这张小铁床。
这样,代兴伟只得选靠门的位置,而且,不得不买床。我怕代兴伟对我有意见,搬家当天晚上,请了代兴伟的客,我们两个人吃了四十多块钱,买一张小床足够了。但是,代兴伟仍然对我有意见,从此,他总是向杨老师反映我的不是,就跟我的身边有个间谍似的,弄得我的心情总好不起来。
这一段时间,我和代兴伟,我们的工资都是每个月800块钱。
除了睡觉,我不喜欢呆在地下二层,代兴伟也不喜欢,所以,下班后,我们都在地下一层。代兴伟想当音乐人,他弹吉它唱歌。有时,我听。有时,我听厌了,就看书,或者看电视。每当我看电视,代兴伟都要指责我声音放大了,影响他。我只能开很小声,挨电视很近地看。没小板凳,我就坐在一叠旧杂志上。有时,我不看电视,就趴在旧杂志堆上写诗或小说。在北京,我有不少文字,就是下班后,在地下一层,趴在旧杂志堆上写出来的。
没多久,我的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获了《中国作家》杂志当年的奖。在领奖时,我认识了贺龙元帅的女儿。贺龙元帅的女儿已经是将军,贺将军,她知道我的困难,愿意帮助我。她在香山脚下部队院里,有一处闲置的房子,希望我搬去住,一来可以给她看着房子,二来我也可以不住地下二层了。我很高兴,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很快,我就搬出了地下二层。
住在香山脚下,上班到和平门,骑自行车单程三个小时。
这时,正值秋末冬初。路上,有时下雨,有时刮风,还有时,下雪,我才知道:这一条路,我骑自行车有多艰辛。上下班,我几乎穿越半个北京城,加起来,就是穿越完整的北京城。贺将军知道我的工资每个月800块钱,决定给我换单位,新单位是一家大报社,抬头有中国两个字。我见了老总,老总说,我们的报纸每天都要进中南海。我吓了一跳。老总说你是贺将军介绍的,我肯定要。我没吱声。老总继续说,贺将军说你的文才好,所以,我决定让你做一件很重大的工作。说到这里,老总停下来,看着我,希望在我的脸上看到喜欢的表情。我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是一个很木的人。
你坐过飞机吗?老总问我。
没。
你想坐飞机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想,还是不想。我不知道。于是,我没回答老总这个问题。
我决定让你经常坐飞机,至少,每个月坐一次。
噢。
我要你坐飞机跑遍全中国甚至全世界。
噢。
又一次,老总停了下来,看着我。他真的希望我惊喜。但是,我的确没。我一动不动坐在老总对面。我的内心非常慌张。我不知道老总究竟要我做什么。我等着老总告诉我。
我要你去全中国全世界采访,把你培养成全中国全世界都著名的记者和作家。
噢。
我一动不动坐在老总对面。我继续等着老总的下文。我想知道老总究竟要对我说什么。
我每个月最少给你开工资五千,最多开五万。
噢。
你不高兴吗?说到这里,老总终于忍不住了,他艰难地挪了挪坐在很高级的沙发上的肥屁股,问我。
不。
你真的不高兴?
真的。
为什么?最少五千,最多五万,不比你一个月八百块钱多很多吗?八百块钱,在现在这个时代还叫钱吗?
是多很多,但是,说了半天,我仍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工作啊。
我要你去采访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家,然后,写报道。
歌颂企业家?
就算吧。
我做不到。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做不到。
这么说,你要拒绝这个工作了?别忘了,这个工作可是贺将军给你介绍的,别人想抢这个工作都抢不到。
我轻轻站了起来,我给老总弯了弯腰,说,对不起,这个工作我不接受,打挠您的时间了,我走了。说完,我转身,很快走出老总的房间。在我的身后,老总差点气死,他立刻给贺将军打电话。贺将军听了电话也差点气死,她不要我继续住在她的房子里了。于是,我又搬回《北京文学》的地下二层。
我搬回《北京文学》地下二层住了没多久,《北京文学》不让我和代兴伟再住免费的地下室。搬离地下二层时,我花二十块钱,买下那张我爱上的小铁床。《北京文学》收回地下二层,还当仓库。我和代兴伟必须在外面租房子住,我们的工资仍旧是每个月800块钱。我和代兴伟分开后,渐渐感觉出对方的好,最终,成了朋友。
这时,发行部新招聘了发行部主任,这人是浙江的,叫应显明。
应显明一到《北京文学》,就是发行部主任。他简直是在压迫代兴伟。他对我也很不客气,比如,我给某作者回信,退稿,信封用大了,他都要打电话,把我叫到发行部,把信封改过来,给我上半天节俭的课,如果,我寄了挂号信,他更要检查很久,像我寄的是炸弹,像我浪费了《北京文学》多少钱。
终于,代兴伟无法忍受应显明,决定离开《北京文学》了。代兴伟离开时,我们在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他要我继续坚持,他说我已经是很不错的作家了。
说着,代兴伟差点哭了,他舍不得离开《北京文学》。
4
我在离办公室不远处租了间很小的平房,每个月房租500块钱。这样,我每个月800块钱工资,就实在太少。少得简直不能生活。那段日子,我在《北京文学》打工,过的不叫生活,叫活命。
《北京文学》所在地和平门,离天安门很近,不上班,不分白天黑夜,我都喜欢走路到天安门打发时间。有时,夜里睡不着,我会慢慢走到天安门。有时,白天呆得很晚了,即使饿着,我也不想回到出租屋。我紧紧抱住天安门广场旁边一棵瘦瘦的松树,像抱住我一生一世,不,三生三世,不,永生永生的情人。我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仰望天空。北京的天空真的很蓝。北京的夜空更加蓝。绝对是一座宁静的大海。看着如此蓝的夜空,我总是忍不住产生飞的感觉。
我好想飞上北京的夜空。
我好想从此化作北京夜空的一颗星星,或者,什么也不化作,就这样,无影无踪地,随风,飞在北京的夜空。
我好想死在北京,就这样埋葬在夜空。
我好想死在北京,等着第二天早上你路过时,发现我在街边冰凉的尸体。
一次又一次,我站在金水桥上,望着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我站在毛主席画像下,默默地给毛主席说话。
真的,无数次,我用心给毛主席说话,希望毛主席在天之灵保佑我。真的,无数次,我天不亮起床,甚至,半夜起床,甚至,整夜不睡,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着看升旗仪式。
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毛主席画像下,我白连春不知道流下多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诗人和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泪水。
亲爱的祖国如此博大,白连春如此渺小。
亲爱的祖国如此漫长,白连春如此短暂。
亲爱的祖国如此辉煌,白连春如此暗淡。
亲爱的祖国如此幸福,白连春如此苦难。
没多久,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太阳活着》,在《四川文学》发了头条,于是,我想到《四川文学》去。我给《四川文学》主编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都得不到回音。后来,就是最近,王童写博文攻击我,我才知道:原来是王童给《四川文学》说了我的坏话,王童给《四川文学》的主编说我不会编稿子。
我无法回四川,必须继续留在《北京文学》打工。我搬了家,搬到了北京的南郊。北京的南郊是北京最穷的地方。房租变成了每个月200块钱。上下班,骑自行车单程要一个半小时,还不能骑慢了。只要在北京,我就不想换其它工作,我热爱《北京文学》,全心全意热爱。这时,我在《十月》发表了中篇小说《母亲万岁》。著名作家老村,介绍我和我的编辑邹海岗老师坐在一起吃饭。邹老师是著名诗人邹狄帆的儿子。饭店就在老村家附近,同时也在邹老师家附近。
吃饭过程中,邹老师问我:《北京文学》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800块。我说。
邹老师说太少了,随即,问我:你知不知道寇挥?
不知道。我说。
寇挥比你先到《北京文学》打工,因为工资太低,实在无法承受,回老家了。说了寇挥后,邹老师又问我:你知不知道赵兰振?
知道。
赵兰振在《青年文学》打工,每个月工资都开到2000多了,而且,赵兰振都在昌平买房子了。
噢。
我听到邹老师的话吃惊不小。我不想像寇挥回老家,想像赵兰振在北京的郊区买房。从这天起,只要有人问我《北京文学》给你开多少工资,我都理直气壮回答:800块。
很快,我说《北京文学》每个月只给我开800块钱工资的话,传到杨老师耳朵里。杨老师批评了我。我非常难受。我想:我是离开呢,还是留下?我实在不知道。
批评我后大概半年吧,杨老师见我没离开,就给我涨工资。随着时间推移,杨老师一点一点给我涨工资,1000块钱,1500块钱,2000块钱,最后,到2008年,我生病离开北京时,早已经是每个月3000块钱了。
杨老师给我涨工资到每个月1500块钱时,一天,我骑自行车在街上,突然看到一条广告:北京南郊某处卖房,首付只须两万块钱。
我下定决心买房。不上班时,我骑自行车,转了一处又一处工地。我看好了一个我可以承受的地方,在北京南郊丰台区和大兴区的交界处。我到处借钱。有些朋友愿意借。有些朋友先是答应了借,真到借时又不借了。我开始找老家亲戚,看是否能用最快速度,帮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房奴。
5
杨老师开始给我涨工资,我决定死心塌地留在《北京文学》。我要在《北京文学》打工到死。挣钱是一回事,能够给更多基层无名作者编发作品,我感到很幸福。每当我发现一个新的写得好的作者,就像发现我自己。真的,一点不夸张。无论农村作者,还是城镇作者,都让我觉得是亲人。一切真心热爱汉字的人,我都当成亲人。读一篇稿子,这个作者是否真心热爱汉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天生是农民。我天生是诗人。我天生是编辑。
在此,我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编了,通过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发表出来,每当想起这事,我就揪心地痛。
在此,我再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编了,通过了,眼看着就要发表了,我已经把校对的工作都做完了,竟然,没发表出来,我的心痛得流血。
在此,我还多说一句:有几个作者的稿子,我打了电话,告诉对方,作品某期发表,我正在校对,结果,最后,仍没发表出来,我甚至偷偷哭过。
没办法,领导的考虑更全面,更深入,更长远。
而我,只是普通的打工编辑。
萧夏林离开原创版后,孟亚辉副主编来到原创版,看二审稿子。孟老师是领导,工作很多,很杂,不仅看二审稿子一样,他整天忙得团团转,要应付上头,要应付下头。有一次,他把厚厚一叠稿子给我,都是我送审给他看的稿子。他说时间太长,退了吧。
我双手哆嗦着接过来,说,孟老师,你都没看呢?
看不过来,这些都半年了。
这些稿子都很好啊,你怎么着也得挑几篇吧。
给我新的吧。
那,这些旧的呢?
退了吧。
不。
那是你的事。
孟老师走出办公室后,关上门,抱着这些稿子,我就哭了。我忍不住啊。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没办法,只得一个作者一个作者地退稿。有几篇,我实在舍不得退,又重填了新的送稿单,再一次送审。
还有几次,比如,吉林作者冯印伟,河北作者赵新,以及浙江作者钱二小楼,他们的稿子,开始,在孟老师那里都没通过。我觉得好,不愿放弃,又找杨老师,把稿子给杨老师,最后,这些作者的作品,总算发表了。
6
杂志编出来了,印出来了,最后,是要卖出去给读者读的。卖不出去,读者想读也读不到。《北京文学》在发行上下了很大功夫,结果总是不理想。每次开会,章德宁社长和杨晓升主编都很着急。萧夏林看起来比两位领导更着急,他对发行部主任应显明非常不满。应显明整天坐飞机全国各地飞,住高级宾馆,请人吃饭,到头来,杂志仍然发行不出去。有一次开会,萧夏林骂应显明,说应显明只知道花《北京文学》钱,不知道下基层,找真正的发行商。话音未落,立刻,就遭到应显明一顿凶恶的拳打脚踢,萧夏林的下巴当即肿了,流血了。众人费很大劲,才把应显明拉开。拉开后,应显明还跳起来,要打萧夏林。
这起打架事件的结果是发行部主任应显明,被开除了。他是招聘的,开除起来简单。
然而,最终,萧夏林也不能再在《北京文学》上班了。这,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萧夏林是《北京文学》正式员工,虽然脾气大,骂了人,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最根本一点,萧夏林是被打的人。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还不确定:萧夏林是否真的被开除。因为我离开北京前,还多次看见他来找领导。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萧夏林已经不在《北京文学》上班,他,基本上,疯了。
7
成了房奴后,我穿的衣服更像农民。我几乎天天都吃白菜。无数次,我到市场捡菜。我住的地方离北京市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不远,有很多人捡。别人能捡,为什么我不能?批发市场一天到晚都很忙碌,人来人往,只要肯捡,任何时候,都能捡到菜和水果。老天真是有眼,让我住在北京市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附近。
我买的房子在远郊,离办公室很远,单程,骑自行车很快,都要两个小时左右。我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有时,骑自行车到半路,屁股痛了,腰酸了,就下来推着走。这一天,我推着自行车,突然,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喊住了。男人喊住我,立刻,紧紧捉住我的左手,把我带到就近的派出所。我刚进屋,屋里坐着的两个警察,都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
哪里的?其中一个问我。
我找一张椅子,坐下来。我累了。四川的。坐下后,我回答。
来北京做什么?
打工。
身份证拿出来。
家里搁着。
暂住证拿出来。
也在家里搁着。我说。我坐直了,看着问我话的警察。我在脸上堆起浅浅的笑容。我的笑容看起来懒洋洋的。我真的累了。我的心很虚,其实,我没办暂住证。我舍不得花那五十块钱,照相三十,办证二十。还必须一年一换。我曾经问过。
你还笑?铐起来!另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警察。
好啊,我说,我把双手伸了过去。
你以为我们不敢铐你?刚才问我话的警察接着说。这个警察要大很多,六十岁左右吧,头发都花白了。
欢迎铐,我来北京十年了,不是第一次被铐。
听我这样说,六十岁左右的警察问,你在哪里打工呢?
《北京文学》。
什么?你再说一遍。
《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就你,扫地吧?
我想扫地,可是《北京文学》不让。
那,你在《北京文学》做什么呢?
你看呢,你不是警察吗?
我看你最多就是扫地。年轻的警察说。
不是。
那你做什么?
编辑。
编辑?就你?
年老的警察走到我跟前,双手叉腰站住。他的脸上,很复杂的表情,变化很快。
有工作证吗?
没。
没工作证,怎么证明?
用你们的电脑查吧。
电脑查?你?
我叫白连春,查吧,我累了,正好休息会儿,等你们查。
很快,年轻的警察就查到了。
怎么证明你就是白连春呢?
不需要证明。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白连春。
凭什么我们相信你就是白连春?
你们可以不信,我刚说过,欢迎铐,可是,你们要想清楚,要找到合理的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怎么样?
你们可以试一试铐我。
可以给你的领导打电话吗?那个把我捉来的四十多岁的穿便衣的男人,问。
可以,不过,领导今天不上班,你知道,领导不需要天天上班,领导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其实,《北京文学》领导,比如,杨老师,一个星期最少上三天班。我是故意说少的。
领导家里的电话呢?
我不需要知道领导家里的电话。
那么办公室呢?捉我来的便衣警察继续问。
我在这里。
什么意思?
今天我值班,你把我捉来了,没人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打破了也无人接。
这时,年老的警察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问,没其它办法可以证明你了吗?
有。
什么办法?
把我铐起来。
先不说铐的事,先……
把我捉来不就是要铐我吗?
不是要铐你……
你们北京警察不是看所有外地人都是坏蛋吗?你们北京警察不是看所有外地穷人更是大坏蛋吗?我这个大坏蛋,你们为什么不铐呢?
你走吧。把我捉来的四十多岁的穿便衣的男人,突然说。
不把我这个穷人当坏蛋了?
走吧。
我是坏蛋,警察铐坏蛋理所当然啊。
现在你像编辑了。年老的警察站起身,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走吧小伙子,快去值班吧,我们和你一样,也是在努力工作。
真的不铐我了?
走吧。
那我可走了警察叔叔。
骑慢点。
8

转眼,我在《北京文学》打工七年了。这天,我突然接到《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老师电话。梁老师约我在北京某宾馆见面。我知道梁老师除了是《星星诗刊》主编,还是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内心激动,不知道领导见我做什么。这之前,我和梁老师从未见过。我终于见到了梁老师,同时,还见到了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宋书记。我很惶恐,猜不出如此大的领导见我,究竟为什么。经过简短的谈话后,我知道了,原来,梁老师想让我到《星星诗刊》去。他离开重庆,刚到《星星诗刊》没多久,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编辑。在这次谈话中,宋书记表示,只要我去《星星诗刊》,我的关系,包括户口,可以立刻转到成都,而且,单位还可以给我一间免费的小房子住。
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我曾想去《四川文学》,可是《四川文学》不要我。
宋书记说,《四川文学》是《四川文学》,《星星诗刊》是《星星诗刊》,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单位。
见这条理由不成立,我又说,我在北京刚买了房子,我是农民,舍不得。
宋书记说,房子可以卖掉,到成都后再买。
房子贷了很多款不好卖。我说。
慢慢卖。宋书记说。
那,我考虑考虑吧。
好吧,我们四川可是真心欢迎你回来的。
谢谢领导如此关心我。
那天中午,我和梁老师,宋书记一起吃了饭。结果,我还是决定不去《星星诗刊》。我不去《星星诗刊》,一因为我真心热爱北京,真心热爱《北京文学》,二我觉得杨老师对我越来越好了。我这个人就这样,别人对我好,我就对那对我好的人死心塌地。这,也是后来我生病回到四川,发生了借三十万块钱,给我的堂兄法官白联洲介绍的据说也是我的堂兄的亲戚,连借条都是三个多月后补写的,无法讨回借款,最后不得不自爆得了艾滋病的原因。
9
人生中,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我迷恋的北方》,是1985年秋,我在黑龙江省当兵时,发表在《诗林》上的。当时《诗林》主编是巴彦布老师。我在《北京文学》打工,巴彦布老师已经退休搬到北京通县,他知道我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给我投来一篇散文,我给他发表了,于是,巴彦布老师多次请我到通县他的家玩。他七十岁,蒙古族人,热心肠,知道我在《北京文学》已经打整整八年工,又知道我拒绝回四川去《星星诗刊》,真心爱《北京文学》,决定悄悄帮我做件大事,让我在《北京文学》转正。他和北京市文联书记吕浩才认识,就给吕书记写了一封长信,专谈我转正的事。结果,巴彦布老师这封信,在北京市文联引起一场八级地震。吕书记非常不买他的账,不但不给我转正,反而执意要把我开除了。这时,杨晓升老师已经是《北京文学》社长,杨老师力保我,才把我留下。事后,巴彦布老师很后悔,觉得自己太看重和官员的友谊,问我离不离开《北京文学》,我说不离开,我又没错,离开,不是正明我错吗?
我继续在《北京文学》上班。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安徽女孩,问刘庆邦老师住在哪里?我说不知道。女孩说,你是《北京文学》编辑,怎么会不知道刘老师住在哪里?我说知道也不告诉。女孩赖在编辑部不走。于是我问她写什么?她说小说。我要她给我看看。她很高兴,说,她要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听着,轻轻皱皱眉。我看了她写的小说,小学生作文一样。我给杨老师打电话。杨老师说千万不能告诉她刘老师住在哪里。下班了,女孩仍不走,我把她从办公室赶出来,锁上门。我推着自行车到街上,她紧紧抓住我的自行车不松。
天已黑尽,我不能和女孩这样耗。我用很大力,把她的手掰开,骑上自行车。骑了一会儿,我回头,看见女孩很无助的样子,走了。
第二天,女孩又来了。办公室人多,杨老师在,我赶紧把女孩介绍给杨老师。女孩缠住杨老师。杨老师被女孩缠得没办法,不得不,把女孩介绍给作家荆永鸣,因为荆永鸣和刘老师是朋友,又开着几家饭馆,也许可以收留女孩。
最终,女孩是否见到刘老师,我不知道。
10
我在北京南郊买的房,挨着北京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那一带外地人相当多,哪里人都有,河南人山东人最多。这些河南人山东人,年轻的在市场倒蔬菜水果卖,年老的捡垃圾收废品。有个山东大爷收废品,我给过他旧书报。我在《北京文学》做编辑,全国各地给我寄来的书报,攒着,不知不觉多了。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个山东大爷。他除了收废品,还到市场捡菜和水果。我也时常去捡。我们成了朋友。有时,他捡到好水果就送给我。次数多了,我不好意思,请他到我家吃过一次饭。
闲谈中,他自然清楚我的身世。我对他也有一些了解。据他说,老伴死得早,儿子也死了,女儿嫁了,他就离开家乡,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一天,我在《北京文学》上班,临时到邮局办点事。这期间,张颐雯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称是我父亲,来到了北京。张颐雯信以为真。我回来,她告诉我:你家出事了,你爸到北京来了,在你家的物业等着呢。我一听,有点傻。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没说话。我知道我父亲绝对不会来北京找我。谁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晚上下班,我回家,看见门口坐着山东大爷。连春,回来了。山东大爷笑着,赶紧给我招呼。怎能冒充我爹呢你?我不高兴,但是,也不能对一个给我笑的老人发脾气吧?
我开了门,把他让进屋。他站着,不好意思坐。我请他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想回山东老家。我噢一声,等着他的下文。他对我笑了很久,接着说,他想给我借点钱。
借钱?我的心有些惊。我想,我和你,只是这样的朋友,你怎么能开口给我借钱呢?再说,我买了房,一直忙着还银行贷款,哪里存有钱?
见我犹豫,山东大爷哭起来。他说他老了,一个人在北京,没朋友没亲戚,很孤独,一天一天觉得不舒服,想回家,想死在故乡。他说他会开三轮车,回家后,卖一辆三轮车开,拉点货和人,凑合着,也能过日子了。
听他说了这些话,我的心早软了。我想到我自己。山东大爷不就是我的老年吗?
于是我问他想借多少钱?
六千。他说。
我一听,不少。我的心很痛。但是,我还是对他说,两天后来拿吧。
他听到这话,立刻对我表示感谢。
送走山东大爷,我当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叫孙殿英,也是山东人,在北京离我家不远的村庄做生意,开一家小商场。我想:从一个山东人那里借钱,来给另一个山东人。我以为我想得很妙。
我开口给孙殿英借五千块钱。孙殿英一点没犹豫就同意了,答应第二天,给我把钱送来。
两天后,山东大爷来我家,我给了他六千块钱,要他路上保重。
山东大爷回到山东后,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山东玩。我哪有时间去?我以为他回山东后会过得很好。一天深夜,我的门被敲响了。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山东大爷。我非常吃惊。在我的吃惊还没结束时,他已经进了我的屋。怎么啦?出啥事了?我问他。他说的话把我吓得要晕倒。他说,他撞人了。他说,他把一个老头儿的腿撞断了。他说,他这是逃到我家来躲的。
我浑身颤抖,不知说什么好。我让他睡沙发。我自己也睡下了。我哪里睡得着?凭感觉,我知道他也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对他说,要他回山东去,找到交警,把他现有的东西,包括新买的三轮车和其它一切,都赔给那个他撞了腿的老头儿。他听着,哎哎地应着。我给他拿了回山东的路费,送他上公交车后,我骑自行车上班,几次都差点摔下来。这天,我上班迟到很久。我到办公室时,杨老师冷冷看着我,问,怎么才来?
我立刻说,在路上,我被车撞了。
伤着没?杨老师紧张起来。
没,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以为这事结束了。不,大约半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黑龙江打来的。一个妇女问,你是白连春吗?我说是。妇女说,你爸在我的旅馆里,没钱了,希望你能给他汇点钱来。我差点跳起来。那天是星期二,张颐雯和王童都在,杨老师就在隔壁。我想跳,不敢。很快,山东大爷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来。
连春,是我。
我知道是你,又怎么啦你?
我到黑龙江了,住在一家小旅馆,一分钱都没有。
你那里是什么地方?
牡丹江市。
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我……
放下电话,我想,我在黑龙江认识谁呢?我想呀想,很快就起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刘长军,正好是牡丹江市文化局的。
我立刻翻到刘长军的电话,打过去,居然接了。我说刘长军吗?我是白连春啊。刘长军很高兴。我们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我就说了我爸在黑龙江,被困在一家小旅馆没钱的事。刘长军一听,很着急,问,那,我给送点钱过去?我就是这个意思。送多少呢?两百吧。两百少不少啊?要不,送一千吧。刘长军说。最后,刘长军说,我立刻就送去。
就这样,我又借了黑龙江的刘长军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至今没还。我生病,回到四川后,给刘长军打过电话。刘长军问了我的病情,连忙表示钱不用还了。我想,等我的生活稳定下来,再还吧。欠着别人的钱,我心里总不舒畅。
刘长军送钱去后没几天,山东大爷来到北京,住进我家。于是,我上班,他到市场捡菜和水果。就这样,我们过着日子。因为从此不用买菜和水果,对于山东大爷和我生活在一起,渐渐地,我接受了。一天早上,山东大爷洗衣服。他洗自己的衣服,也洗我的衣服。本是让我高兴的事。然而,他放洗衣粉太多,他把很多洗衣粉放到一大盆水里。我说,洗衣服,把一点洗衣粉放在一小盆水里,把衣服泡一会儿,再洗。他就不高兴了。等天黑,我下班回来,山东大爷不见了。
他把我攒着还银行贷款的两千块钱,偷跑了。
这事没多久,我病了。一病就很严重。我怕我一直担心的艾滋病来了。我到就近的医院检查,没查出问题。医生说重感冒,输点液就会好。我输了三天液。不见好。我请假回到了四川,在故乡的医院,医生查出我是艾滋病发病了。
多年来,我悬挂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来了。
我奇怪:北京医院什么也没查出来,隔不到一个星期,四川医院倒查出来了。我在北京输液的那家医院不小,比四川这家医院大很多。
11
在故乡的医院住了两个半月院,我出院了,暂住同学家。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某救济站打来的。一个女同志问我是不是白连春?我说是。这女同志问我认不认一个人。我一听是山东大爷的名字,立刻说不认识。电话没放下,我听见电话里,女同志对山东大爷说,人家说了不认识你。
挂了电话,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我又把电话打到了救济站,问清楚了,原来,山东大爷被救济站收留了。
救济站不能一直收留他。救济站要想办法把他送走。
山东大爷没亲人朋友,于是,他告诉了救济站我的电话。救济站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总算找到了我。
我打电话给孙殿英,叫孙殿英给山东大爷买了北京到成都的火车票,把山东大爷送上火车。就这样,山东大爷来到四川,又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在工厂生活区租的房子,邻居大部分是东北人。山东大爷生活很习惯。他和几个东北老太太处得很好。我发现我的钱用得很快。原来,山东大爷用我的钱,给一个东北老太太买油买肉买菜,买衣服,还给老太太儿子买烟。老头儿老太太们都有退休工资,他给人家吹牛,说他每个月有退休工资两千八,其中一个老太太老伴死得早,动心了,要嫁给他。一天,山东大爷给我提出来他要结婚。
我说好啊。
山东大爷说,我结婚了就不和你住在一起了。
当然。
你给我拿点钱吧。
不能。
为什么,我照顾你这么久?
你照顾我这么久,你怎么说得出口?好吧,你想要多少钱?
五千。
三千。我说了三千后,停住,过一会儿,我问,你结婚了,没退休钱怎么办?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不是管,是担心,怕你今后还会来找我。
我不会再找你的。
今后,你没钱怎么办?
我回老家,把房子卖了。
没几天,山东大爷就回了老家。回老家约一个月,山东大爷又来到四川泸州,在那个东北老太太家住了两天。东北老太太见他没拿来钱,不和他结婚。山东大爷走了。我不知他去了哪里。
今天,此时此刻,山东大爷都没和我联系。过十多天,我也将离开四川泸州我的家乡,到广东东莞去了。我还会继续给《北京文学》打工。朋友们,有好作品,想在《北京文学》发表,请发到我的邮箱里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