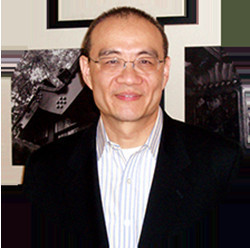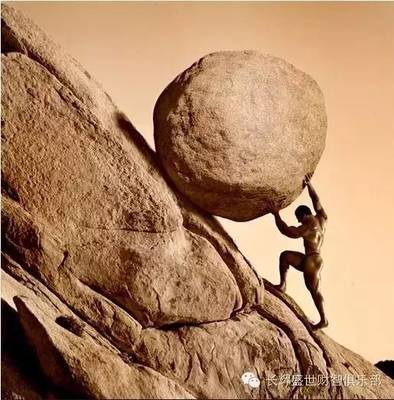Z 先 生 的 两 次 分 析
科胡特案例

一、Z先生的主要背景
出生于富裕家庭。
父亲在Z先生第一次来诊前四年去世,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那时Z先生21岁。
Z先生的母亲:一个有艺术气质的女人。
童年深得母亲和父亲的喜爱。
母亲的控制与童年早期的发展相适应。
三岁半时父亲病重住院,与一个女护士发生情感纠缠,离家,在Z先生五岁时重返家庭,父亲的关系恶化。
父亲回家后开始手淫。
五到八岁目睹父母性交。
十一岁时卷入一段持续了两年的同性恋关系。
防御性的三角关系:Z先生、他的朋友、母亲。
二、来诊原因:三角关系被打破
三、Z先生的主要症状
躯体方面:心脏早博、手掌出汗、胃部充盈感、周期性的便秘或腹泻。
间歇的疑病观念、自杀念头。
社交方面的孤独感。
无法与女孩子建立关系。
自我评价低。
缓解孤独的方式:读书、看电影、看戏和听音乐会。
四、第一次治疗
1、手淫,伴随着受虐性质的幻想。
——手淫的意义
——关于施虐与受虐
2、母亲移情在治疗中的再现:自恋的夸大,面质,阻抗。
3、治疗一年半之后态度的转变
他坚持认为,他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我对他的理解明显增加了。我以赞同的口吻谈论这个变化,并说针对他的自恋妄想的修通工作现在奏效了,病人以友好而平静的方式拒绝了这个解释。他说,发生这种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他身上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做的某些事情。他说,我的其中一个解释触到了他的无法满足的自恋需求,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当然,当一个人没有被给予他认为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时很痛苦的。”
4、从经典理论角度所做的解释
我试图向他说明,从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病人只有四岁半或五岁时,他父亲实际上已经回到家里,他坚持认为——如同在移情中发生的一样——他没有一个俄狄浦斯期的竞争者,在前俄狄浦斯期完全占有他的母亲直到他父亲回来,这不过是一个妄想。换句话说,对防御性自恋的持续做了解释,这个防御保护他免受觉察到他有一个在性方面占有他的母亲的有力的竞争者的痛苦,也让他免遭阉割焦虑的折磨,因为觉察到自己与竞争者的对抗和敌意冲动会令他无处藏身。
……
在我所做的解释性重建的努力中,我从两个方面推进:我试着让自己着眼于前生殖器期固着的要素,把它们视为与婴儿性欲相关的部分,这一部分与前俄狄浦斯期母亲密切关联,在这一点上我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随着治疗的进展,我试着去弄清并对他解释他附着于前俄狄浦斯期驱力目标的动机——或者是退行到这些目标上——也就是说,他害怕采取与父亲面对面竞争的姿态,这使得他退回到较早的发展水平上,或者,至少是阉割焦虑妨碍了他重要的往前发展的进程。
……
总体来说,我处理Z先生的在精神分析中被动员起来的心理病理的方法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完全吻合。尤其是他的受虐倾向,我解释为是他的前俄狄浦斯期的占有母亲的内疚感和他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期竞争的性欲化。我认为,通过创造一个刚愎自用的阴茎母亲的形象,他在两个方面对抗自己的阉割焦虑。经由否认人类没有阴茎的幻想,也就是说这些人丧失了他们的阴茎,经由断定他的母亲比父亲更强有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害怕父亲成为一个阉割者,他的母亲可以有效地保护他免受父亲的伤害,因为母亲拥有一个比父亲更强有力的阴茎,比父亲更强大。
……
大体上说,我那时的印象是,那段关系在最深的层面上蕴含着前俄狄浦斯期的、性前期的与理想化母亲的关系的再度激活,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段时间是男孩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公开地在情感上完全远离他的母亲。
5、第一阶段治疗的结果
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在症状和行为方面的结果是:Z先生沉湎于受虐的倾向在分析的后半年逐渐消失,治疗结束时几乎全部没有了。而且,他迈出了成长的决定性一步:从母亲的住宅搬出来,住进了他自己的一套房子。最后,他不仅开始约会,而且在性方面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姿态,与几个女孩子建立了与他的年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相符合的关系。在分析的最后一年,他当时正在做一个研究项目,开始与一位职业女性过从甚密,这位女性比他大一岁的样子,他向她咨询一些属于自己研究项目内但却超出他知识范围的问题。他主动追求她,与她有过满意的性关系,并考虑和她结婚,尽管直到分析结束时他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决定。
6、一个重要的梦
他在一所房子里,站在一扇门的内侧,门砰地一声打开了。父亲站在门外,带着大大小小装满礼物的包裹,等着进来。病人感到十分害怕,他试图关上门,把父亲挡在外面。
科胡特的解释:
出于我已经形成的对他的人格和病理学的总体建构框架,我在解释和重构中特别强调他对重返家庭的父亲的敌意、他的阉割恐惧、他与一个强壮的成年男人面对面的情境;另外,我也指出他从竞争和男性阳刚气质中回撤的倾向,要么退回到古老的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期的依恋,要么退回到防御性地指向父亲的顺从和被动的同性恋的态度中。
关于第一次治疗的一个补充:科胡特从经典理论去理解Z先生不仅因为理论上的原因,还由于他自己对自恋人格障碍者镜映移情的防御,此可见于《自体的分析》(简体本)中F小姐的案例,220—225页。
五、第二次治疗
1、来寻求治疗的原因
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仍然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他眼下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孩有来往,但前一段却有过一连串的恋爱事件。他在性方面总是能力很强——此前曾经有过的轻微的早泄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困难——但他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投入的关系中情感总是很肤浅,尤其是他的性生活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满足。随后,他很快提到——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推想这标示出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先前沉湎于手淫并伴有受虐幻想的情形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表面上看,他在自己的职业方面做得很出色,但他并不能享受他的工作,而是感到那就像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负担,一种打杂的活儿。我还记得,基于他把自己的性受虐没有再反复与对他的工作的不堪重负放在一起并列讲述,我马上推测,与我所期望的结果相反,第一次分析并没有通过结构的改变达到治愈他的受虐倾向的目标,这些倾向只是被压制下去,现在总体上转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另一个原因:Z先生的母亲五年前(Z先生离开她搬出来的时间)开始,逐渐陷入到有偏执妄想的精神病状态中。
2、不同的治疗基点
我猜想,他再次见到我之后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是他已经建立起来的移情的一个方面,我怀疑他的改善是不是与他较早期生活中体验到的良好状态相似,那个时候他的关注点从母亲转向了营地辅导员。换句话说,我开始假设——在第一次分析期间我没有这样设想过——他建立了一种理想化移情。
3、理想化移情
第二次治疗开始时的第一个梦(第一次访谈头天夜里做的)
那是一幅图像:一个黑发男人置身于一片有丘陵、山峦和湖泊的乡村景色中。尽管这个男人平静而松弛地站在那儿,但他似乎强壮而信心十足。他穿一身城里人的服饰,通过一种复杂而协调的方式——病人看到他戴着一枚戒指,胸前的口袋里突显出手帕的一角,他的每只手里都拿着东西——其中一只手里拿着的或许是雨伞,另一只手里拿的可能是一付手套。这个男人的形象看上去非常不真实而又十分显眼——就如同某些照片中的情形一样,在那些照片中,被摄主体对焦十分清晰,而背景却被模糊了。
意义:
联想显示,这个形象是一个凝缩体,包含了(1)营地辅导员(风景的确定的特征暗指夏令营的地点);(2)他的父亲(头发);(3)分析师(雨伞、手套、手帕、戒指)。那个男人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表和派头十足的举止,病人描述他所使用的钦慕的语气,都表达了与一个理想化客体的关系,也就是理想化移情。我当时并没有理解那个形象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尤其是他那身穿着打扮。但在病人的联想中,他约略回忆起了关于他父亲的那个梦,拖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想要闯进屋里,这个情景与第一次分析的结束阶段建立了一个联结——它昭示着第二次分析就如同是第一次的继续,就像我后来才理解到的,它把第一次的最意味深长的失败之处作为起始点。
4、临床处置
那时我刚体悟到面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恋移情分析师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出于这一洞识,我没有干扰病人对我的理想化的展开。
5、镜映移情
他在由理想化的分析师提供的氛围中所体验到的良好的状态和内心的安全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病人变得自我中心,苛求,坚持要得到完美的共情,对于最细微的与他心理状态的不同步,对他的交流的最细微的误解,他很容易以狂怒来做出反应。
6、临床处置
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本质上将其视为防御,一开始我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情形加以忍受,后来逐渐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姿态,而现在我以一种分析师面对重要的分析材料时的尊重、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这一现象。我把它看成是对分析有重要价值的某种童年期情形的复制品,它在分析中复活了。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带来了两个有益的结果。其一,它摆脱了对由于治疗所引起的繁复的人为结果的分析——他对抗我的徒劳的狂怒反应和随之而来的与我的冲突——我以前将其视为分析他的阻抗时不可避免的伴随情形。其二——这是我们正走到正确的方向上的一个可靠的标识——分析开始进入一个先前没有探索过的病人人格领域的较深的层面,并对这个部分加以阐释。
六、两次治疗的区别
1、对丧失的不同理解
我立刻感到很疑惑,Z先生母亲的严重的情结紊乱在某些方面会不会与Z先生情况恶化并来求助于我有关。他是否面对着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没有放弃的爱的客体的丧失?抑或他对抛弃母亲并导致她因此患病而感到内疚?他自己考虑过这些可能性,他实际上意识到了自己有某些丧失感和内疚感。但他没有认识到——我们在第二次分析过程中达成了这个出人意料的领悟——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是,他母亲的严重的情绪紊乱并不是一个把他拖回到先前的疾病中的有害的力量,而是把他推向健康的有益的促动……
2、阻抗与理想化:第二次治疗开始时的不同理解。
3、客体关系理论与自体心理学
以早期客体关系的传统思路来看,我们可以说,分析的这个阶段激活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情形,这个时期,也就时童年早期,他单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这位母亲随时准备供给他自恋满足的愉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移情的阶段看作是一种早期情境的复活,在那个情境中,他被母亲宠坏了,占优势的过度满足反而让他发生了固着,从而妨碍了他的进一步发展。但即使在分析的这个阶段,上述传统的解释模式并不能恰当地说明我所看到的Z先生的人格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种潜在的、长期的绝望,经常与这种感觉一道出现的是他的苛求的傲慢;还有,最突出的是性受虐,这个倾向再次出现,并与他的明显的自以为是形成鲜明的对照。
4、治疗师的态度
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本质上把病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主动性的中心,因而期待他会借助于精神分析的能让他看清自己情形的领悟的帮助,放弃他的自恋的要求并获得成长。而在第二次分析中,我的侧重点发生了改变。面对成熟的目标,我采取了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我设想,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和此前相比,我真正能做的是把任何目标导向的治疗野心放在一边。我以不同的姿态投入到治疗中,不再坚持以前促动我的健康和成熟的信条,而是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对他的经历的早期阶段的重构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他与母亲的病理性人格相纠结的方面。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病人处于未成熟状态中的自体,这可以从移情中看到,我们不再因为它并不打算放弃它的儿童的满足,就将其视为对改变的阻抗或对于成熟的妨碍,相反,我们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不顾一切的——通常是绝望的——挣扎,目的是要挣脱有害的自体客体,建立自己的边界,成长起来,变得独立。
5、对母亲的病的理解
Z先生在第一次分析中向我描述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对家庭以外的人扮演得很成功的形象。然而,那些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当然,尤其是病人和他的父亲,心里都更清楚,即使他们不能把这种了解提升到意识层面以便相互分享。他们知道这位母亲抱有一些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些信念转换成一系列态度和行动,从情感上奴役着围绕在她身边的人,遏制着他们的独立存在。的确,当Z先生在第一次分析中讲到他的母亲用满足的愉悦回应他时,他对母亲的讲述并没有错。他的讲述中缺少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母亲给予他情感上的馈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条件:他完全服从于她的控制,他不能让自己有丝毫的独立,尤其当涉及到与其他人的重要关系时更是如此。Z先生的母亲有强烈的、病理性的嫉妒;或者还可以加上一点,不仅父亲和儿子,甚至还有仆人,都处在她的严厉的控制之下。
……
第二次分析中的很多时间,Z先生都完全用来描述他与母亲的关系。但是,他所浮现出的记忆,尤其是他对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的实质有了越来越深的领悟,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母亲的严重扭曲的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决定了他们的关系的性质,这一切都伴随着极大的焦虑,通常会引起强烈的阻抗。他的关系的流动中断了,他不再专注于分析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表达他深深的怀疑:他的记忆是否正确,他对我的陈述中是否不带偏见。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学的领悟,不能达成这个领悟会使得推进过程最终暂停下来——他害怕涉及到母亲这个古老的自体客体的丧失,在记忆的这个阶段和修通与母亲的古老融合的过程中,丧失会对他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包括瓦解、在这些时段丧失自体——这些时段之外亦是如此——他把这个自体视为自己仅有之物。他的怀疑、他的从已经认识到和揭示出来的内容中回撤的倾向,是由于暂时的对他的记忆的压抑的缘故,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他强烈的崩解焦虑使得抵赖重新占据了优势,早在童年时代,这种状态就已经让他完全不去承认他实际上体验到和知道的事情。
……
当他逐渐能够摆脱母亲灌输给他的那种对他们的关系的看法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时,他开始认识到母亲的一些表面看来如此正常和有益健康的行为的某些古怪之处。比如,他开始认识到,他的自体对于将来的力量和独立的主动性期待一个共鸣,但他的母亲对此从来没有丝毫共情,在她的关于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图像中,她总是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在生活中获得多么巨大的成功,他们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不会离开她。
……
Z先生的母亲的行为在病人早年生活期间的三个例子,即她对他的粪便的兴趣、她插手他的个人物品、以及她极其关注他的皮肤上的小的瑕疵,构成了她对他的态度的有代表性的方面——就如同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的,这种态度表现了她无法消除的、不可改变的需要,那就是让她的儿子作为一个永久的自体客体。
……
当他大约六岁时,她对他的粪便的专注停下来,显然是突然停止的;随后她变得对他的皮肤着迷,就像她之前对他的肠道着迷一样。每个星期六下午——程序变成一个不可变更的仪式,就如同曾经的粪便检查一样——她检查他的脸上最小的细节,特别是——当他跨入青春期时越来越多地——检查她可能发现的任何生长中的黑头粉刺。
……
第二个阶段以挤掉长出头的黑头粉刺为结束,这通常是很痛苦的。这位母亲时常说起她为自己的又长又硬的指甲感到自豪,她对儿子讲述如何挤掉粉刺,向他展示挤出来的皮脂栓——一种细小的排泄物的团块——并对此心满意足,在这之后她似乎很高兴,感觉到暂时的轻松,Z先生也是如此。最糟糕的情形是,要么没有发现长出头的黑头粉刺,要么挤掉粉刺的尝试失败。
……
本质上讲,她是一个“边缘案例”。精神病的核心,最主要的是她的人格的前心理学的(pre-psychological)混乱,还有她的自体的空虚,这些都掩盖在牢牢抓住和控制她的自体客体的现象之下,她需要这些自体客体来支撑她的自体。尽管对一般相识的人她表现出一个情感正常的形象,但即便是局外人,不久也会感觉到隐藏在正常外表下面的死寂。因此,Z先生的同学和熟人,不管是小学同学还是后来认识的,没有一个喜欢去他家玩,这造成了他的社会隔绝。就算最后给这个男孩分配了一个房间,他的享受也毫无隐私可言。那位母亲坚持他的房门所有时间都要开着,而且,她经常会突然地、意料不到地闯进去,以一种吓人的、不满的目光搅扰病人和某个来玩的朋友之间进行的谈话或其他活动。
……
Z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她母亲的精神病理学,越来越理解了母亲的这种状态对他的病理性的影响,但他的这种意识和理解需要经过大量的情感磨砺才能维持下来。这方面的材料的浮现和对这些材料的精神分析的阐释屡次被严重的阻抗所打断,这些阻抗表现为莫名的恐惧被激活,我称之为(科胡特,1977,第104页)“崩解焦虑”。哪一种现实是真实的?他母亲的现实?第一次分析中建立起来的现实?或者是当前的这一种?他反复在这些问 题中挣扎。很多次,特别是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的开头部分,他把自己的探索放在确定的事实上,那就是他的母亲形成了一整套妄想,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她的观点是歪曲的。他屡屡回忆起当他第一次完全认识到母亲患了精神病时自己的反应,她藏匿在一整套妄想当中。他即刻的反应——那时他感到深深的困惑,但现在清楚了——是一种平静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内心快乐。那是一种他对于现在所目睹的事实完全放松的表达,至少潜在地是这样的,她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别是在他童年时代她对待他的方式都是病态的,并不是只有他才知道这一点。
(转换内化)
……
那些梦中母亲只出现过一次。尽管这个梦中可见的内容很简单,而且它本身是无害的——母亲的一个光秃秃的轮廓,背朝他站着——但这个梦仍然充满了他所体验过的最深的焦虑。我们接下来花了好几次访谈的时间来全面而深入地阐释这个梦。在最容易理解的层面,这个梦的意思很简单:母亲把背朝向他;她现在会抛弃他,因为他和父亲走得更近了。我要补充一点与对该梦的这个解释有关的情形,我并没有做任何提示,病人自己暗示了这个意思,Z先生举出几个例子——那是来自童年期和后来阶段的记忆——当他试图走向独立,特别是走向一个独立的男性时,母亲就冷冰冰地不再关注他。以前,病人对这个征象总是用把情感重新转回到母亲作为回应。
6、手淫的意义
在第一次分析期间,我解释为固着的表现和/或通过满足前性器期的驱力来获得快乐的向婴儿期模式的退行。我们现在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童年期的手淫的意义,其中伴随着做某个女人的奴隶的幻想,这个女人无条件地把她的意志强加给他,把他当作一个无生命的、没有自己意愿的物体来对待,还有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就材料而言,换句话说,第一次分析的修通过程正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的(我们以为这达到了治愈)。在这里,先前被我们看作是快乐的获得、驱力要求和驱力满足的一连串事件,现在我们认为是自体的抑郁,自体想要界定和维护它自己,在自体客体的心理组织中不顾一切地建构自己。我们认识到,不仅他的手淫和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未曾带给他快乐,而且在他童年的大多数时候都弥漫着抑郁的、绝望的情绪。因为他不能快乐地体验自体边界清晰的成长和独立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喜悦,他努力获得一种最小的快乐——那种失败自体的没有喜悦的快乐——方式是自体刺激(self-stimulation)。换句话说,手淫不是被驱力所唤起,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享乐主义式的确定自体的精力充沛的行动。他试图通过刺激他的身体最敏感的区域,以此来暂时获得活着和存在的确认。
我特别记得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时刻,Z先生恢复了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记忆。首先,他回想起在他的童年期和潜伏期,他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打发自己度过闷闷不乐的一天,他告诉自己说,夜晚会到来的,他会上床并可以手淫。我不会去描述围绕在这个记忆中的情感,它令人心碎地呈现了一个孩子毫无生机的存在状态,在面对几乎完全缺乏为健康的孩子敞开的成长和独立的快乐的情境中,这个孩子给自己的仅有的安慰,是想着他可以用不停地延长手淫的方式来刺激他孤独的身体——然而,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让自己从缺乏自体边界的意识中获得解脱,就像在受虐幻想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在第二个记忆中——这属于这个时期中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的最深层——他不仅回想起在形成他的受虐幻想体系之前,在一段短时间内他曾做过肛门手淫,而且——他的回忆的这个方面最初伴随着最为强烈的羞耻感——他还闻过甚至尝过他的粪便。如我所说到的,这些记忆的唤起一开始极为痛苦,他童年时代的悲伤或羞耻的再次激活有时会极其强烈。不过,在记忆呈现的相关情境中,Z先生的体验仍然保持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因为他第一次理解了,在与另一个人共情的同调中,这些童年时期的活动既不邪恶,也不令人厌恶,那是一些无力的尝试,为了给自己提供一种活着的感觉,表现了基本的自体幸存的有活力的残余部分,它现在终于在确定边界了。换句话说,他知道与母亲分开既不罪恶也不危险,而是有益于健康的。
7、原初场景的意义
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并不是一个稳定统一的、探索性的自体的健康的性好奇的表现——如果对于乱伦客体的禁忌和恐惧造成了冲突,而孩子又没有能力解决这种冲突,因而将其压抑下去,那么一种健康的好奇可能会招致灾难。对Z先生来说,原初场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没有共情的过度刺激的体验,他理解为一种想被母亲的活动吞噬的要求。他通过把放弃独立以受虐的方式性欲化,以此来顺从这个要求。
8、关于父亲
正如Z先生最终认识到的,他的父亲恋上那个护士并决定离开家庭去生活,实际上是在逃离母亲。这也是对自己儿子的一种放弃,如同病人在童年期必定会前意识地体验到的他的父亲的行为——他在第二次分析中才确切地弄清楚了这种情感。病人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父亲一直设法拯救他自己,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牺牲了他的儿子。
……
他仍然会谈到他父母的性关系。但是在前一阶段,他几乎不考虑父亲的参与——我试图强调母亲和父亲的性交并没有从他身上激起有意义的回应——他的联想(直接的记忆,偶尔是关于分析师的性生活的移情幻想)现在开始自发地、越来越多地转向父亲的角色。在这方面,分析工作所带来的最初的影响还是一种抑郁和绝望——换句话说,这是与第一阶段曾经持续过的同样的一种情绪。但他的绝望现在不像此前那样是弥散的——它越来越多地与一种明显关注的情形有关:他父亲很虚弱,受到母亲的掌控和压制。
……
在不断提到原初场景、抱怨他父亲的软弱和他父亲对他漠不关心的同时,他开始表达对我的强烈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我的过去,特别是我的早年生活、我的兴趣爱好,还有我的受教育情况;他想知道关于我的家庭的事情、我与妻子的关系,以及我有没有孩子。我把他的查问视为婴儿好奇心的再现,并指出这些好奇与他父母的性生活的关联,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变得抑郁,告诉我说我误解了他。但这依然造成了不太严重的分析僵局。尽管我没有答应他要了解关于我的具体信息的要求,但我还是告诉他,他想知道我的情况的愿望必然是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愿望或需要,在听了他更多的讲述并观察了他的反应之后,我承认我同意他的说法,那就是,我使用的“好奇心”这个说法并不妥当——我当时体验到的东西并不是童年期性窥阴癖的复活,而是一些别的需要。最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的疑问背后所包含的是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父亲,他想知道我是否也很虚弱——在性交中对妻子冷淡,不能给一个儿子可以理想化的情感支持。我的解释方式的这种转换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的抑郁和绝望戏剧性地减轻了。他放下了让我提供关于我的信息的要求——事实上,我以一种坚定的态度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最终把这种坚定看成是我的人格的长处,是我的力量的标志——他设法弄清了少量的一些信息,那是他偶然之中或者通过推论得到的——比如,我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他还谈到他的看法,那就是,至少在我身上,对心灵世界的热爱并不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能力竞争而采取的退缩,而是可以和男子气、和勇气并存的。
……
当他再次谈到关于营地辅导员时,就像在第一次分析中一样,他的言谈中流露出喜爱和尊敬,对于他们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懊悔,而是把他与辅导员的关系看成是与一个强壮的、受人称赞的男人之间的充实的友情。总体上讲,我同意Z先生的看法。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分析中我传递给病人对这种友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它代表了一种向阴茎母亲的退行——现在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他的朋友一直是他所渴望的一个强有力的父亲般的形象,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受人称赞的兄长。但是,我不同意(我没有详细阐述这个观点,只是简短地提到过一次)这种关系的性的方面是无害的。我认为,换句话说——我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如果他们的亲密关系中没有性的接触,Z先生会从与这个男人的友情中获得更持久的益处,就我的判断来说,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或许要加上一点,在这个关系的移情再现中并没有同性恋的冲突被激活,这可能恰恰表明我错了,而病人是对的。)
……
在当时浮现的记忆中,他特别专注于一个两周的滑雪假期,那是他九岁时和父亲一起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度假胜地度过的(或许是因为那时他的母亲正在应付她自己的母亲处在疾病晚期的状况)。这些回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涉及到两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他发现,他的这个看似虚弱的、形象模糊的父亲,在他清晰的人格中其实颇有一些特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质,他越来越认识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怀有一种强烈的需要,看清关于他父亲的某些事情,以解开某个特殊的、令人困惑的秘密。
……
Z先生的父亲实际上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滑雪者,并且通达人情世故。他与男侍应生和女服务员相处很有一套,不久他身边就围绕着一群追随者,他的故事令他们着迷,他们对他仰头而视。自从听到了父亲在电话里的交谈,听了父亲在读文件时说的一些见解,病人也对父亲的商务活动有所了解;他开始钦佩父亲在这方面的果断、敏锐和老练。但是,在分析的这个阶段,心理学上的本质并不在于病人发现了一些他父亲的令人惊讶的特质,或者在他谈到过的他的早年生活中,或者在他的回忆性的评估中,而在于他带着强烈的体验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独立的男人,过着一种不同于他母亲的独立的生活——他父亲的人格,就算其中的短处,并不像那位更加强有力的母亲一样被扭曲了。我在这里要加上一点,在这个阶段,我的解释既涉及到理想化移情,也与他父亲的正性特质的重新复原有关,这些解释集中在病人的两方面体验的意义上。对于我自己的或者他父亲存在的不足,我没有去面质,而是把自己限定在表达我对他的需要的理解上——在童年时代以及在当下的移情中复活的需要——他需要仰视一个被理想化的男人,他为这个男人感到自豪。
……
紧接着一个短时期的移情幻想所发生的情形是,他突然说了一个猜测:他父亲有过一个女友,并且这个女友在科罗拉多度假期间一直在那儿。尽管我们不能断定他的猜测是否合理,但我相信,Z先生也认为,证据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一个仅有的例外,病人并没有直接的记忆表明他的父亲与任何特别的女人有过亲昵。这个例外涉及到一个很小的但却值得注意的事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这个记忆的浮现受到了阻抗的干扰;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在所有关于在科罗拉多逗留的记呈现之后冒出来的。病人还记得,那是他们在旅馆逗留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带这个男孩去酒吧,那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尽管他的父亲通常喝酒并不是很多,但在这个场合他看上去变得有点兴奋——儿子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对他父亲引以为豪的冒失之举做出了反应——中间他加入了一支小管弦乐队,并接替了他们的男歌手。其他客人热烈鼓掌,他父亲收到了很多祝贺,有一个女人尤其赞誉有加,她来到他们这一桌,和男孩简短地聊了几句。Z先生当时就认为,这个女人很可能与他父亲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甚至猜测,她可能就是那个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带他父亲离开家庭的护士。
……
与结构性神经症病人身上我们在复活的俄狄浦斯体验中修复的情感方式不同,与Z先生的记忆相伴随的并不是与他父亲竞争的绝望感,而是一种以父亲为自豪的情感。进一步说,没有抑郁和自卑感,也没有孩子感到被成年男人击败所引发的结果,而是一种快乐的热情和终于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的精神充沛的感觉——暂时与之融合,以作为一种增强他的自体、把自己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有主动性的独立核心的手段。就像通常在这类案例中所看到的,分析中没有出现来自Z先生童年的俄狄浦斯期早期的材料,竞争幻想的唤起与分析师有关,而不是他的父亲。与这些幻想相伴随的不是绝望和焦虑,而是一种乐观和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分析师父亲被体验为强壮并具有男子气,因此,接受分析的儿子现在能体验到他自己。
9、关于父亲的梦
病人通过他的联想所阐释的那个梦的新的意义,把他的意思用我的话来说,并不是一个孩子怀着阉割恐惧对抗成年男人的攻击性冲动的描绘,而是一个很长时间没有父亲的男孩的心理状态;这个男孩被剥夺了心理上的资源,通过对父亲的优势和短处的无数的观察,他会依靠这些资源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男性自体的内核。当父亲突然回来取代了他在家中的位置时,病人实际上暴露在一种可怕的情境当中。但是,他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针对他的身体,而是针对他的内心。一种创伤状态使得那个梦成了仅仅是一个温和的复制品——这种创伤状态并没有威胁到他的身体上的存在,而是威胁到他的心理上的生存。在父亲缺失的那段时期,一个男性自体通过男性自体客体得到了滋长和加强,这个男孩需要他的父亲作为男性的心理资源,这种需要是巨大的。未获独立的自体逐渐形成;他设法建构的心理上的存在植根于他对母亲的依恋。在他被奴役的过程中,他尽力获取一些驱力快乐——但并不是体验到作为一个活跃的、独立的性自体的那种令人振奋的快乐。
他父亲的返回让他突然暴露在一种最重要的心理需求得到潜在的满足的情形中。这就像一个正确但不共情的、负载了太多内容的解释,可能让接受分析者暴露在一种创伤状态中(见科胡特,1971,第232-235页),因此,他被暴露在——真是极其巨大的——一种创伤状态当中,造成这种创伤状态的是,他极其突然地被给予了他背地里一直渴望的所有心理学的礼物,这些礼物实际上是他需要拿到手的。父亲拖着沉甸甸的行旅,试图进来,儿子拼命不让父亲进来以保护自己——尽管Z先生的某些联想简短地触及到了与同性恋主题相关的心理学材料的过渡体系,特别是与他青春期前的同性恋依恋有关,但这个梦本质上所涉及的是主要部分的心理经济学的失衡,这个主要部分指的是男孩的心灵被暴露在强烈希望他的父亲回来的情境中,而不涉及同性恋,尤其与基于俄狄浦斯期的消极的同性恋反应无关。
10、Z先生的垂直分裂和水平分裂
他从来不愿意听任自己放弃一个独立的自体,却在某一刻发现自己面临一桩努力数年还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开始从两个不同的、各自分开的方面体验自己——他的人格建构起了一个垂直分裂。表面上他仍然依恋母亲,呈现出一个依然和她纠缠在一起的人格,并且——通过一个单独的代理部分表达了大量的幻想,可能是被母亲掌控的幻想的复制品——服从于她的生殖器原基的作用。他人格中的下一个区域是母亲和她的病态的部分——这个公开呈现为一种夸大的部分是母亲馈赠给他的,只要他不和母亲分离开就能得到——这是另一面,被一堵拒不承认的墙壁分隔开。在这个隐藏的却又非常重要的部分中,他保留了一些理想化,这些理想化一直与他父亲相连接,被藏匿在对父亲的力量的记忆之外,而父亲的力量正是这些理想化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些理想化得自于童年晚期,那时他试图把自己与母亲分离开,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男性自体,虽然时间上已经晚了,但他的努力全部失败,这些理想化总本上都被压抑下去了。
……
在他的水平分裂部分活跃着的需要,也就是被压抑的心灵层面,以及与这些需要相关联的体验的记忆,只有两次浮现出来:青春期前的一段时期在Z先生与辅导员的关系中——我之所以相信如此,是因为它的性欲化——这段关系并没有导致真正的结构的建立,也没有形成有益健康的结果;在他的第二次分析期间,通过大量的对他的理想化移情的修通,逐渐完成了理想化的转换,这导致了一个所期待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在他童年期留下的未完成的过程得以永久地、可靠地完成了。
11、第二次分析的一个结果
在他的分析的最后几周当中,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他父母的短处有了更多的共情和容忍的态度。即便关于他母亲的人格的扭曲,这曾经对他的成长有过伤害性的影响,他现在也能表达一点点理解甚至同情。他也能不带理想化地看到她的人格的一些积极的特质,而他正是带着这种理想化开始他的第一次分析的。没有任何融合的倾向,而是以他的分离和男性气质作为坚实的基础,他承认,尽管母亲有严重的精神病理状态,她还是给了他很多。他不仅推测说,在他婴儿早期她可能是一个好妈妈,这个好妈妈对他的镜映的认可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活力的内核,后来让他能够持续地追求情感的健康,尽管在他的道路上有着严重的妨碍,他也承认,在他童年后期植入他的人格的很多最好的资源,包括那些使他在工作中有能力的,实际上是有创造性的部分,都来自于她。在这种语境中,我和他都猜想,他的母亲曾经经历过一个无声的但却是极具伤害性的人格改变——也许是对她和Z先生的父亲的关系开始恶化做出的反应——但是,尽管她的人格有严重的扭曲,在Z先生的第二次分析期间我们还是发现,她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她的生活,甚至在她被说成是偏执型精神病之后,她不仅在她被歪曲的人际知觉之外的部分保持着一颗健康的、有活力的心灵,而且还保有一点点坚定、诚实和现实的态度。
……
他在分析中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成果是打破了与他母亲的很深的融合。除此之外,他不仅保持了他最重要的才干和技能,这些才干和技能现在让他在职业上游刃有余,而且还怀有具体的抱负和理想,这些抱负和理想决定了他对工作的选择,并给这种选择注入了情感的意义——即使这些才干、技能、抱负和理想是从他现在已经放弃的与母亲的融合关系的基质中滋生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妨碍。因此,他最重要的技能和才干,还有他的抱负和理想的内容,这些都主要不是受到他父亲的人格的影响。他的自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分析期间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针对他对我的移情关系的修通,使他能够重建与他父亲的男性气质和独立性的连接,因此,他的抱负、理想以及基本技能和才干,即使其内容没有变化,其情感内核也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现在,他把这些他人格中的资源体验为是他自己的部分,他不再以受虐性服从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生活目标——紧接他第一次分析之后他就是这样做的——而是充满愉悦,就像一个独立的自体充满活力的状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