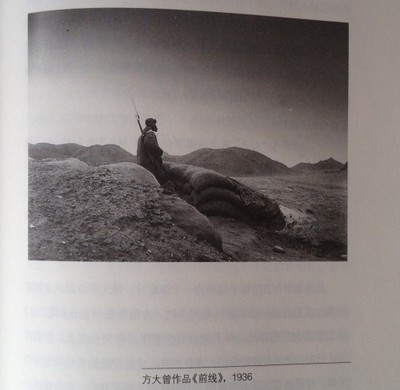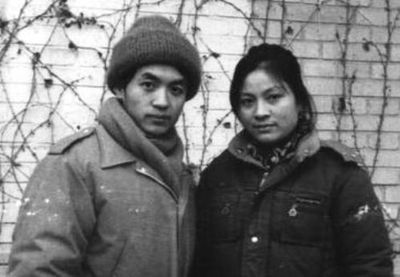由《顾准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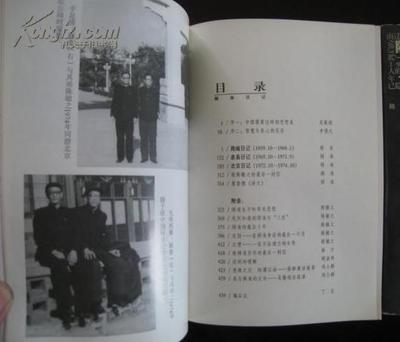
所想到的
(一)
以我的条件,是难窥《顾准日记》、《顾准文集》、《顾准自述》和《顾准全传》的全豹的。为写这篇文章,翻阅了自己所订阅的报刊中的相关材料。粗略地归纳认为,顾准的可贵之处体现在他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他的超前意识,以及为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例如,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他对于“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路线的疑虑,他对于个人崇拜(“偶像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定位和批判,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等等,无不显示他不随流俗,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对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是不无裨益的。这也是《顾准日记》引起学界关注与好评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对文革及其之前历史的反思文章屡见于报章,顾准当然是很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他以其经济学家的学养与思想家的才华,留下了供后人研究的宝贵资料和个人信史。毫无疑问,顾准是应该肯定的,顾准的探索是有益的。顾准堪称鲁迅所赞誉的“中国的脊梁”,哪怕有时是“拼命硬干”。
(二)
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人们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实,我觉得“上帝”并不是笑人们的思考,往往是笑人们坐井观天,刻舟求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形而上学。要得到“上帝”的首肯,就需要站在“上帝”的高度。尽管我真诚地仰慕顾准精神,但对于顾准们的指点江山,针砭时弊倒不以为然。
据说,“顾准对毛泽东的经济、政治思想有许多怀疑和批判。”(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载《随笔》2007年5、6期,以下《顾准日记》引文均摘本文)甚至说:“他该走了,大概也真的快走了。”(“他”当指毛泽东——引者)说毛泽东“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要”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应该感谢1959年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坏事变成好事。”凡此种种,我固然为顾准的胆识所惊叹,但我更认为他“毕竟是书生”,他不是能驾驭全局,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有人说:“假如三十年前顾准的经济思想能引起最高领导的重视,假如当时能从制度上保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国社会的发展又会怎样呢?”(钱钢:《<顾准全传>随想》,载《文汇读书周报》)
然而,设若将顾准的思想和主张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治国平天下,恐怕是行不通的。这使我想起当年鲁迅评论曹操和孔融的话:“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比方说,顾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现在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29年诬蔑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的荒谬解释。我们的国体已开宗明义,不存在抽象的民主,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说得明白。顾准探究了古希腊的城邦的民主制度,并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其实,这种民主政治,并不是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奴隶、外来人和妇女则被剥夺参加民主大会的权利的。
顾准在思考“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的问题时,提出“切实的民主制度保障”问题。不错,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需要修正和完善,这也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深思的。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就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并谈到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转引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考虑了却没有或基本没有付诸实行,甚至还有所倒退,横空出世的政治运动打乱了这一切,民主和法制建设从而夭折。
“漫天飞雪迓春回”,改革的春天使我国有可能续写这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篇。但即使在今天,民主政治也是谨慎地推进,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民主建设的确有个“经济高度发展”的问题。民主在我国运用得不适度,中国之舟将会搁浅甚至倾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再比方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今天无疑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剂良方,但建国后直至三十年前若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单纯用价值规律的杠杆推动经济的发展未必合适。某种意义上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更适于共和国草创期的必要的高度集权的治国方略。当时,政权要巩固,建设要奠基,百业要起步,国家要自立,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筹安排,很难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很难把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很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正如今天的开放搞活,三十多年前开放得了吗?“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军事大国虎视眈眈以强凌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均处劣势,那时若开放,恐怕只能是“门户开放”。怎么毛泽东刚逝世不久就有条件了呢?只能说,没有毛泽东的艰辛奠基,冲破封锁,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那是何等步履维艰的探索啊,那是何等波澜壮阔的征程啊!小平同志曾对此进行客观公正的阐述,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人们批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批评向社会主义过渡操之过急,这是有道理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毛泽东为在有生之年“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梅白:《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没法不急。而今天的改革,恰好补上了资本主义这一课,其主旋律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场精彩绝伦的戏剧,凝聚了几代政治家的心血,领衔主演的人物表上,不能不首先大书“毛泽东”的名字。
马列主义有这样的观点,历史事件只能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在这里这时是对的东西,在那里那时可能不对;顾准的思考放到今天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而若在当年恐怕是不合时宜。毛泽东做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要从全局去考虑问题。他的奇思妙想,缜密擘划,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他的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并非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啊。
(三)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毛泽东揭示的一条规律。反了右派,我们今天可以看清,立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舆论一律”;反了右倾,客观效果很明显,立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也为大跃进擂鼓鸣锣;文化大革命中反刘少奇、反林彪、反“四人帮”立了什么呢?尽管我探索有年,至今也难知所以。这个大题目,国内外研究者甚夥,的确“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邓小平语)
人们对反右扩大化及错批彭德怀多有诘难。人们同情五十五万知识分子的悲剧,同情老革命、老将军的蒙冤,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也应看到,知识分子有时也是好“胡说八道”的(这不一定指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也可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顾准现象是也)。毛泽东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二十二年缄其口,震慑的何止五十五万。凤凰涅槃,在烈火中重生,知识分子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代价巨大。
至于反右倾,1965年毛泽东对彭德怀讲:“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自述》)窃以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那时却硬是不能“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横竖都要打倒、搞臭这位在中央最敢讲话的功高、位尊、权重的老总。从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看不出忤逆“圣意”之处,其客观、善意、委婉、尊重之态跃然纸上,不值得毛泽东震怒。以毛泽东那令人景仰不已的党性修养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如此对待彭德怀的上书,不能不令人瞠目和震惊(历史旧账和“骂娘”结怨似乎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彭本人也是一头水雾:“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彭德怀自述》)粗莽地、莫须有地定为“反党集团”,的确是有悖常规的错位,难怪薄一老也说:“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我私心里认为,此无他,唯借题发挥耳。“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列宁语)借反右倾倒彭之题,使个人崇拜大功告成。
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多所诟病,这已有定论。但问题仍可进一步研究探讨。例如: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有区别吗?毛泽东是为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吗?毛泽东什么时候热衷于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又“讨嫌”而降温,其目的何在呢?毛研专家李锐有“封口”一说。他是这样说的:“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这也是从个人崇拜的角度去分析的。只是李文所批评的是毛泽东错误地运用个人崇拜的手段,而不是必要的手段,这一点我不甚认同。
而今,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也不应意气用事。暴风骤雨过后,应更深入地研究其来龙去脉,进入理性分析的高度,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仅从个人品质或道德人格上去闪烁其辞地责难,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是严肃严谨的态度。
(四)
反右运动时,毛泽东和罗稷南的一次谈话,曾引起广泛关注。此前似乎没有相关的评论,至少我没看到。仅在2008年《随笔》第1期上看到朱正先生的推论:鲁迅若“像活着的时候那样,拿着一支笔不断向黑暗势力挑战”,毛泽东“得把他关在牢里”;“如果他不再写文章了,也就是说鲁迅不再是鲁迅,而只是自然人周树人,当然不必关起来,……。”对于朱先生的推论,我觉得是很随意的主观臆断,与毛泽东的话从口气到实质,难以吻合。
据周海婴提供,1957年罗稷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毛答:鲁迅若是活着,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黄宗英以亲聆者的身份证实,毛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认为,毛的回答,有利于了解毛泽东的心路轨迹和反右决策的内涵。以毛泽东对鲁迅的一贯评价必然形成的思维定势,毛泽东似应说,鲁迅若是活着,要么会成为反右中的冲锋陷阵的英雄,要么与右派沆瀣一气甚至被关在牢中。但毛泽东却如此这般地回答: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是毛泽东设想鲁迅对反右决策不理解——“永远进击”);识大体不作声(这是毛泽东设想鲁迅对反右决策理解——参透玄机)。
毛泽东的两种估计均含褒义,两种可能出人意料,两种推测亦在情理之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毛泽东是懂得鲁迅的,毛泽东和鲁迅都是懂得中国的。
(五)
对于大跃进乃至反右倾,顾准说,“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这话讲得很对。但是,为什么大跃进中牛皮吹得天大,谎言编得离谱,毛泽东却假作不知,不予说破。以毛泽东的“聪敏”,这些弥天大谎能瞒得了他吗?正如刘源所说:“毛泽东是庄稼人出身,一时被懵,情有可原,长年不知一亩能打多少粮,实难让人相信。”(《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按照顾准的说法,这是“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过渡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且有“信阳事件”及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正常死亡,这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绕不开的事实。顾准的“消灭过剩人口”和“剿灭人口”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果如此,何来“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活脱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要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倒不如实行严格的节育政策来得更堂皇更有效。而恰恰在此期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是批“新人口论”造成出生率上升的一些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于1957年)。以不惜死上亿人口代价把经济搞上去,除非秦始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做得出来。若如此,我们还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怎样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一句“功大于过”就能服众吗?
关于这段历史,1959年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中讲道:这三件(指百花齐放、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引者注)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我们可从中略见端倪。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8月11日的讲话)都提到了“全世界骂”:杜勒斯骂,赫鲁晓夫骂,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既然如此为何一意为之呢,为何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声言,“不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法宝”来打他呢?又是怎么个“向全世界作战”法呢?我不妨“大胆假设”——掀起风雷,激起动荡,引起争论,发起挑战。随后的一个时期确实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进行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国面对着“反华大合唱”,党内国内的斗争自不必说了,整个世界都在“翻腾”、“震荡”,所有矛盾都在胶着、激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件是用来“作战”的,不是为了“跑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精通马列,怎会不知一国不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呢?——这是需要“小心求证”的。
黑格尔说过:“巨人在大步前进的时候,是不吝惜脚下的花草的。”“花草”在巨人脚下不得已摧残,人们能非常清楚地看清由若干具体事实构成的“浩劫”。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人们不会谴责黑山、塔山阻击战的血流飘杵吧?历史前进固然按一定的轨道运行,但是,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巨人“大步向前”把历史提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往往为人们视而不见的。
(六)
毛泽东从1957年后一直反“右”,即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二十年左。”“左”和个人崇拜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做了充分和长期的准备的。例如,“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进行文革不可少的铺垫。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复辟的危险性,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革中斗什么呢?同时,没有“左”所激发的狂热的民族情绪,没有集体化乃至人民公社的体制,没有共同富裕(其实都不富裕)的经济基础,没有法制不建全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能发动起来吗?而且,没有个人崇拜,没有个人专断,毛泽东能领导“拥护的人不多”的十年之久的反复斗争吗?换言之,没有反胡风,没有反右派,没有反右倾,毛泽东就不能做他的一生干的第二件事。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说:“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党史专家金春明归纳为“文革”起因十说。(见《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但恐怕对文革起因的背景的探讨,至今仍没有完结。
有两种说法是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其一,已故作家徐迟在他的散文《哥达巴赫猜想》(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中,用文学语言对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描述和评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颗颗的精神原子弹的成功试验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连续爆炸了。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股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的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险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误,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像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在罗陀斯岛上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英雄豪杰,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子播下去,就有收割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这段话与随后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多所抵牾的,故收入选本则删去这段话。但其中的某些论述又是发人深思的。诸如,“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在徐迟的笔下,文革的起因仿佛不是挖刘少奇或刘少奇一类了。特别是最后一句:“种子播下去,就有收割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其二,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说道: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
小平这段公开发表的文字所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小平原则上并没说“彻底否定”,存在的仅是运作中的“缺点、错误”。他把文化大革命称之为“一次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对“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作为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统一全党认识”的需要,不是终极结论;第三,过早地做出评价,不易为人们理解,因为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语);第四,对于文化大革命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就是说,正确地、科学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还要假以时日,还要认真研究。
《决议》是一个时期党的指导性文献,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加深理解。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纠正冤假错案,不能纠正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东西,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别是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转移,也要对宣传口径、内外政策做相应的调整。
在充分理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敏感性在淡化),应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能总徘徊于“忆苦思甜”的层面,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死胡同。
(七)
《顾准日记》几乎囊括了建国以来所有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无论专家、学者或民间思想家,都在思考着,研究着。个人认为,这种研究应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地去看,不能孤立地、静止地、表面地去看;应该放到大背景中客观公正地去看,不能就事论事或意气用事;应该分析此事件与他事件的内部联系,不能浅尝辄止,人云亦云;应该恪守《决议》中“最核心的一条”,不能越过这条警戒线,不能企望凑足材料再定性,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
关于最后一点,还要啰嗦几句。薄一老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了这么一席话:“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在今天,国人形成了共识,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而且错误还不小。以我上述的说法,是否还是“毛主席是正确的。”小可倒不敢拂逆亿众的意志,更无能量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但我坚信,毛泽东是否定不得的,包括他的晚年,毛泽东的伟大将愈久弥彰。不要若干年后,让子孙后代笑话我们,说我们连这样伟大的人物都不知拥戴(如果从战略上考虑则另当别论)。
毫无疑问,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事件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0多年了,其耳闻目睹的议论也知道的不少,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篇小杂文《我爹的烟思想》。
我爹说:“文化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是抽烟。先点火,后燃烧,一时挺红火,收获的是一股烟儿。(转引自《杂文选刊》2001年12期,作者甘否)
此说似有些道理。不是吗,十年动乱,最后不是“收获的是一股烟儿”吗?打倒的人又平反昭雪了,否定的事物又甄别肯定了,砸烂的世界又重建修复了。这和徐迟说的“播什么,收什么”正好相反。孰是孰非,“凡事总得研究,才会明白。”(鲁迅:《狂人日记》)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上述这些是偏见还是无知,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往往我们盲目地自信,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弄不好会成为未来历史中人们的笑柄。
〔本文中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没按习惯用法加引号。小平已开先例,本文引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9页引文也是这样没加引号。我觉得,指称一定历史时期的专用名词,大可不必无端加上表示否定的引号。按惯例也显不伦不类。〕
2008年2月16日誊抄完毕炕头枕上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