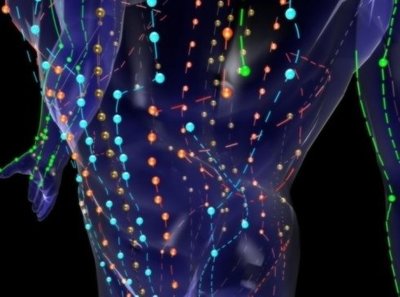民勤小曲戏之我见
许多年前,在乡下,就听几位早熟懂事的发小津津乐道所谓的民勤传奇。什么“四红”、“四黑”、“四香”、“四臭”,“四焉”、“四旺”等等。也听他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或哼唱民勤的小曲片段。我那时尚幼,懵懂无知的我常从他们扭曲变形的淫笑与嘿嘿声中领略到了小曲戏的“无限魅力”。我耳濡目染自然“受益匪浅”:
《张连卖布》:“… …四娘娃跪灶火,手拉风匣,两个儿奶头往前扎……”
如果把以上当做民勤传统文化加以弘扬,我不得不遗憾的向大家坦白——民勤小曲戏,与其说是曲艺,倒不如说是庄稼人最早的性启蒙教育素材之一。我深知,我等话音未落,道学家排山倒海的唾沫星子早把我淹死N次了,伪君子也窃喜终于找到了攻击我的把柄。我承认,我是个低俗不堪的人,在道德的审判台上,我只能乖乖投降或者狼狈逃窜。
多年前,县文化馆有一位在大家眼中德高望重的研究馆员身份的老者,他曾经私下让我看了他辑录的小曲戏曲目及台词,其中有些还配有一些图片。不瞒诸位,这些所谓的文化精粹,除了夺走青少年的童贞,唯一的功用,就是民勤城的四街八巷里,又增加了诸多搞破鞋者而已。健康优美的曲艺作品会陶冶一个人一生的审美情趣,使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及时是出生卑微的农民,镰刀锨把伴随的一生,也会留下高山流水般的清音。而在一个下流小调横行乡野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即使入了党提了干,血液里奔涌的也可能就是龌龊下作的元素,民勤小曲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后来者中不乏有良知有责任心的贤良,“取其精华,剔除了糟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带有腥臊恶臭的物质,即便再混合很多正牌调料十三香,馊骚味断难消除。忘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可偏偏有人时不时的把这破裤衩抖出来让人瞧,就不由得让我难以脱敏,这两天胃里老是翻江倒海,喉咙里也总有什么东西为虎作伥,一直想吐却又吐不出什么,每天叫苦不迭,暗忖苍天无眼,放牛的,卖布的,挖菜的,钉缸的,观灯的怎么就让我这个乡下的榆木疙瘩一下子全撞上了呢?
摸牛尾巴长大的土包子,自然没见过大世面,倒也不打诳语,实话实说,除过《梁秋燕挖菜》尚不能算丑以外,其它几出戏,要么是二流子纳凉——光摇扇子;或者干脆就是货郎哥哥走西口,把闷骚撒播到长城之外;要么就是傻女婿玩入洞房——丑态百出,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好像跻身三甲的分别是《小放牛》《张连卖布》与《钉缸》。试想,好色淫浪的放牛娃和寂寞难耐的寡妇,能演绎出什么好事呢?
按知名度来说,韩少云的《小姑贤》曲目不错,但民勤版的却是倒行逆施,剑走偏锋。《二瓜子吆车》取材《苏三起解》,本是一处苦戏,然则泪涟涟的苏三却与吆车的二瓜子插科打诨,引逗调情。《下四川》中干妹大胆提出“干哥不嫌干妹丑,咱兄妹二人配成偶”彻底颠覆了中国妇女的传统形象。《打懒婆》《二姑娘害相思》《钉缸》《瞎子看灯》《老少换》《怕老婆顶灯》是以另类攻城拔寨、以丑陋克敌制胜的。她们纷纷油嘴滑舌,以淫词滥调为先锋,迈着最丑的步伐,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丑为美的时代。
在所有的扮相中,最让人忍无可忍的首推“赌神”张连哥哥。相信很多人看过,尤其是头顶那顶夸张的牛角尖毡帽。他手摇花扇,腰里扎着一条或红或粉的绸带,在舞台上驴推磨似的转圈圈,间或还以经典镇番腔油嘴滑舌跑火车。花旦的扮相常常让人联想起不是成语的成语——婊子过堂。若是晚场,在舞台灯光的映衬下,母夜叉粉墨登场,血盆大口一张,甭说看客都有和我一样的反应,恶心得直想吐,胃里却没有供给,只得闭上眼睛,快马加鞭地想想平生每天清早条件反射般到茅坑方便时偶然瞥见的坑位风景,温习一下当初这类秽物是怎么在肠胃中发酵翻滚蠕动,又怎么等待肛门括约肌给它们大开方便之门的------
现在如何呢?众所周知,这些段子已被打造成了民勤传统文化的扛鼎之作,艺人们摇身一变,俨然以民勤文艺舞台掌门人自居,稍有闲暇便粉黛再施,红袖再舞,风骚依旧,纷纷闪亮登场。
出丑弄乖如同走邪路,走的次数多了,邪台就颠覆了正台。卖丑卖到极点,自然天下无敌。东北有赵杂毛,西北有张舍尔,小丑们的春天算到了。这年头,丢丑的价位一路攀升,君不闻“卖嘴的不富,多少是个贴补”。他们拿着丰厚的薪水,揣着由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处处出乖露丑,反正有那么多人捧场,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别看谁的肩膀上也扛着个头,他们的头里面可填满了“音乐细胞”,好歹也算与艺术家沾点边。他们特有经济头脑,水口子一堵,杈把扫帚一丢,便可发挥自身特长,卖丑走穴赚外快——人在长城之外,丑据诸夏之先。其实对他们来说,社会效益民间印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趁皱褶不多,还未把髁囊里的滥词忘干净。几个丑名昭著的爱好者“情趣”相投,还有文化部门为他(她)们搭台,何不丑态百出、好让余生丑名远扬,百年后追随张舍尔、高疯子之流更上一层丑。只要丑到了极点,那就功成名就了,自然不愁白哗哗的银子不滚进来。

同时他们还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粉墨登场,搔首弄姿,极力把自己最丑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以期搏得更多的掌声和笑声,进一步扩大知丑度。在乡村僻野没有过足瘾,就跑到文化广场来跳梁,博个丑名了事。每逢传统佳节,“艺人们”更是按捺不着自己的狂热情怀蠢蠢欲动,率诸得意门生“上台献艺”,嫡传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自家田间地头里的事情撇在一边,专门出来显丑,老中青三代纷纷涂脂抹粉招摇过市,在台上扭捏作态,卖弄祖传的资本,赚取来自文化之乡的酬金。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他们眼光独到,深知在这个教育名县里,有四大班子领导鼎力支持,有以退休干部为主要粉丝的等死队票友保证他们的票房收入,只要不在台上露骨的撒泼“放驴”,丑绝对是卖点,只要泼皮胆大脸厚心黑,丑甚至可以畅销到临河陕坝、新疆河套,因而奇货可居,自然不能轻易错过了。
多年以前,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丑到了极点也便是美到了极点。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如今他的甘肃邻居竟然会如此酣畅淋漓地诠释着这个丑陋的真理。依目前形势看,这种情况还将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文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时代里,我坚信民勤小曲戏无疑还将有十分“美好”的前景,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里,在沙井文化发祥地,还将上演多少“流芳百世”的丑剧、涌现多少“名垂青史”的小曲戏名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