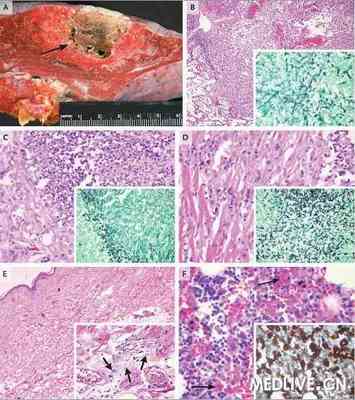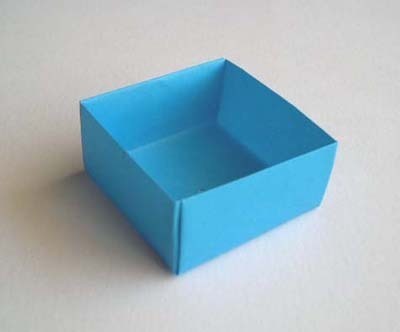对后金军队人数的考证
作者 杜车别
我们先来看各种史料记载。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萨尔浒之战的一年之前,后金攻打抚顺时动用的兵力在《满文老档》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十万。
“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十万兵征明……”[1]
是不是这个数字写错了呢,回答是不可能。下面在攻取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地之后,还有记载前后呼应
“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虏前行,……,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至边界附近驻营”[2]
也就是六万人带着俘虏回去了,而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四万人到边境驻营。(清朝的《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对应的这段内容是“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复临大明边安营。”)
那有没有可能十万这个数字夸大了呢?
回答同样是不可能,《满文老档》的记录当时是给后金统治者自己看的,汉人要看也看不懂,不存在为了虚张声势故意夸大兵力的可能。而作为事后历史记录的话,那更只有缩小己方兵力,来彰显以少胜多之神武形象,绝没有夸大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明方关于后金兵力的记录。
在一年之后,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的报告中说
“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3]
而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出任辽东经略后写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中说
“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鸟喇、恶古里、亏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4]
杨镐根据对阵官兵的报告,说后金兵力在十万左右。熊廷弼则是根据自己的估算,结论也是近十万。
《满文老档》一年前就已经记载后金光是出征抚顺兵力就已经有十万,那次后金俘获就有三十多万人畜,这其中就算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被编练成军队,到萨尔浒之战的时候,也就不止十万了,所以熊廷弼的估算还是低估了的。
另外有一个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一年之久的朝鲜人,他写了一个《建州闻见录》中提到的后金兵力,通共三百六十牛录,每牛录三百人,多寡不一,按一牛录三百人计算在十万开外。
另一处则说“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云”则是兵力至少也在十四万以上。
纵观当时各种记载,后金自己的,明方的,朝鲜的,关于后金兵力的记载,一般都是在十万左右。就如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时,就声称后金十三万人来攻打宁远。
但是在现代有许多人却宣称,后金从万历末年,一直到崇祯初年,兵力最多不可能超过六万,至于能抽调出征动用的兵力就更少了。
就如著名的网络作者capo1234,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大致上就是这一个观点,按他的说法,后金在设立八旗之初,最多也只有4万丁(是16至60岁可以服兵役的男子),而这4万丁还不可能是兵力本身,实际打仗的时候是三丁抽一,最多不过二丁抽一,算一下最多只有两万人可以用来出征。
后金在初期是200个牛录,到了天命六年(天启元年)是231个牛录,崇祯二年是250个牛录左右(capo1234根据前后数字猜测的)。
按照一牛录两百人的编制,后金八旗在崇祯二年也总共只有五万壮丁,然后按照按照“每牛录60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而————出征的时候,不能全部调用,只能调三分之一,于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动用的实际兵力就只有五千人,把不打仗的后勤民工算上是16000人,再算上从征的蒙军八千以及后勤之类,capo1234估计的后金在崇祯二年出征军力不超过两万五千(实际能打仗的只有一万多人)。
如果capo1234的推算成立,崇祯二年,后金能动用的兵力尚且如此至少,那在万历末,天启天启年间就更不必说了。
应该说capo1234是我极为尊敬和佩服的一位作者,甚至关于毛文龙和袁崇焕问题,本身我都是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深受启发才开始涉足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他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
他论证的漏洞就出在,数字的推算完全建立在对牛录数字的一些假定上,而完全把各种史料中关于后金兵力的直接记载抛在一边,不管不顾。
但问题恰恰在于后金的牛录制度本身就是前后混乱,各种记载互相矛盾的,用这些数字作为推算基础,结果势必把大量想当然的东西当成论证前提,当成事实本身。
就如capo1234的这段话
『现在的问题,就是考察一下满洲八旗的制度和人数。按通常的说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见于基本史料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这样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300人,则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400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25×8=200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231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会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这里capo1234采信所谓八旗之初有二百牛录的理由,就是二百牛录更符合五五制,也即:一共设立八旗,每一旗有五个甲喇,每个甲喇有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五五二十五,二十五乘八就是二百,所以八旗总共就有二百牛录,按照每牛录三百人计算就是六万人。而按capo1234后面的说法,当时的每个牛录还不满员,所以应该平均每个牛录两百人,只能有四万,当然这个平均两百也是他猜测的数字。
但实际上所谓的八旗五五制,大概只有八旗的“八”这个数字才是对的,其他的和实际基本不沾边。就按照capo1234自己承认的满文老档天命六年记载的八旗二百三十一牛录来说,我们直接引用郭成康在《清初牛录的数目》来说
“各旗所辖的牛录数目悬殊,最多为六十一牛录,最少的为十五牛录,每旗平均为三十牛录”。[5]
如果认为五五制的描述成立,那能直接用来证明后金初期八旗有二百牛录左右但各期牛录相差悬殊的老档的记载本身就可以否定了。
如果承认五五制的描述跟实际相差甚远,那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400牛录的理由,显然就不能成立。
再有就算按照200多牛录来计算,是否每牛录真的只有300人或200人呢?
这里的论证也是掺杂了太多想当然的因素,capo1234举了一些牛录不满员的记载,但实际上同样有许多牛录超员一倍以上的记载。
在日本学者三田村 泰助写的《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一文中说:
“还有,一个牛录三百这一数字是一个准则,但在‘召集的部众’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现据《八旗氏族通谱》举例说明,马察地方的佟氏之中,有十札鲁忽赤(检察官)之一的巴笃礼札鲁忽赤,他率领五百户来归,从属于正白旗,编成牛录。同族的雅西塔,率领满洲二百余人、汉人二百三十余人来归,亦编为一牛录。这一牛录共四百三十余人,并且半数以上是汉人。又绥芬地方那木都鲁的明安图巴颜,率领满洲一千余来归,变成二牛录,一牛录有五百人。再有,额宜湖地方的富察氏阿尔都山,招抚三百余人,编成一牛录,这是标准的数目。然而,纳殷地方的富察氏孟古慎,以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归,亦编成一牛录。从这些例子来看,可知是以三百到五百个壮丁编为一牛录。《建州闻见录》说‘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这个说法大概是合乎实际的”[6]
也就是有五百户编成一个牛录的(按照capo1234说的每户出两到三个丁,那这一牛录就有1000到1500人了),有四百三十人编成一个牛录的,有五百人变成一个牛录的,当然也有三百人编成一个牛录的。
先不说capo1234列举的那些五十多人一牛录的记载是否可信(按朝鲜人建州闻见录人的说法,当时一牛录300人以上应该才是普遍情况),就算姑且认为是真的,又怎么能想当然就得出平均是两百人一牛录?
再回到后金初期有多少牛录的问题上来,《八旗通志初集》没有记载建旗时的牛录总数,真正明确提出八旗初设时有四百牛录的乾隆时期修订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
那么《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的四百牛录说是否是胡编乱造呢?我们就以《钦定八旗通志》来说,实际上它是在乾隆时期整理和掌握了更多八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赵德贵所写的《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说
『《八旗通志·初集》虽然在保存资料方面有所贡献,难能可贵,但其征引之资料往往勘核欠佳,讹误不当者时有发现。《钦定》本则不然,在成书过程中,不仅对各类史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且对旧志资料一一核检,并将其正误得失记于案语、注文或序言之中。以“谨案”考镜史事源流《钦定》本之案语分两类:一为文中加案;二为一事开篇,提行另起加案。前者多用以注释清语人名、官名与地名;后者多为史事方面的补缺拾遗,攻讹纠谬。今据《旗分志》案语举例如下。
(一)补记各佐领之根源、来地、编立年代,以及分编、合并、裁汰等事项。《旗分志》二十七《镶红旗汉军佐领》,第一参领第二佐领条下,“谨案旗册:此佐领系天聪五年编立”《旗分志》二十九《镶蓝旗汉军佐领》,第五参领第六佐领条下,“谨案:此佐领原由内务府拨出,因所属人等俱系另记档案之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将此佐领裁汰。
(二)补记各佐领、管领、分管之初任、承袭、兼管、改旗、拨旗、抬旗情况。……』[7]
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中说:
“《钦定八旗通志》则是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背景下,以《八旗通志初集》为基础,由纪昀等人奉救撰修,集中了四库馆和翰林院等多位学者,并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以乾隆五十一年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历时二十多年才修撰成功,因此该书主修班底的学术条件和实力要超过《初集》本的编修人员。这也是《钦定八旗通志》无论在体例、内容、资料等方面都优于《初集八旗通志》的原因。”[8]
也就是《钦定八旗通志》本身是比《八旗通志》在资料收集更完备,掌握材料更准确,核定更严格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从这一点来看《八旗通志初集》没有提出国初四百牛录的说法,而到了乾隆中后期修撰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却明确这了一说法,这显然不是疏忽或者臆造的结果。
那么具体到八旗牛录的问题上,在乾隆中后期,究竟比起雍正时期开始修的《八旗通志初集》来,掌握哪些更多材料呢?
从陈佳华、刘世哲翻译的细谷良夫《《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一文中可以得知详细地记载了牛录分类、牛录来源等情况的旗册是在《八旗通志初集》的《旗分志》编纂之后才完成的。另外作为雍正时期修纂的《旗分志》基础的佐领家谱册虽然已经开始逐渐向国家档案转变,但“尚未进行充分整理”,从而导致“关于牛录本身情况记载不详备”。到乾隆时期这些原始资料才真正得到充分整理。
由此可以断定,乾隆中后期《大清会典则例》以及《钦定八旗通志》之所以要把以前老档以及实录中关于后金初期二百多牛录说法修改为四百牛录,正是在大量新整理完备的档案材料如《旗册》,《佐领家谱册》的基础上进行的。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蒙八旗,汉八旗成立的时间相当晚,但许多证据表明,在蒙八旗,汉八旗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蒙人为主,或汉人为主的牛录,这些牛录在蒙八旗和汉八旗成立之后,再从原来的满洲八旗里分离出去,在旗分志里也是放在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计算的,但追溯起源的设立时间,是完全可以追溯到蒙八旗,汉八旗成立。
所以尽管这些牛录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蒙古和汉军的名号和区分,但钦定八旗通志在提到他们的时候,仍旧有可能按照他们后来的划分而叫成是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如果不动脑筋,因为这种叫法,而认为《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是胡乱编造的,显然是没有考察事情本末原委,想当然的判断。
后金八旗牛录数目本身就在其官修史书中前后记载矛盾,混乱不堪。就算我们不完全采信《钦定八旗通志》中的后金初期就有400牛录的说法,那客观的态度也是对这个问题存疑,留待有更多原始资料挖掘出来才能解决。
实际上后金一开始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低下,各种记载矛盾混乱,或者残缺不全,是必然的事情。用一系列规则的制度假定作为前提,假设后金记录是完整的,确切的,并且实际操作中完全按照纸面规定来执行,然后只要象做小学生数学应用题一样,用几个简单的乘法就推导出后金兵力多少。这是高估了后金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了。
即便我们再退一步说,就按照后金初期二百牛录的说法,那也是不能得出后金兵力只有四万或六万。实际上根据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一文论述,许多人当作论证前提的后金兵民全都被安置在八旗系统下管理,只要根据八旗牛录数目就能计算出其人口兵力多少,这大前提就是错误的。
在八旗系统之外,还另有一个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汉官管理系统: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9]
另一部分是所谓诸申官管理系统,也就是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的系统。
“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

此外还有所谓随旗问题,用滕绍箴的话说“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他区分了四种情况“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他举孔有德等人的例子,说明汉兵随旗但不入旗
『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 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
还有如李永芳
『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
滕绍箴论述甚详,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再详尽摘录。
后金统治下汉人的数目远多于女真人的数目,这些汉人除了一部分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八旗系统。汉人兵员数目合计起来,就算不多于女真兵,也至少是相差不多。如果只按照八旗牛录数字来推算后金兵力,显然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和事实相差甚远。
总之,用牛录数字来推断后金兵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连串充满疑问的假定,是不科学的做法。
相对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料记载后金兵力的直接数字互相参照,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处记载后金兵力十万以上,这可以认为是夸大,但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记载都是如此,那其为虚假的概率只能是无限接近于零了。
[1] 《满文老档》第55页
[2] 《满文老档》第59页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辽东经略杨镐奏本
[4] 《明经世文编》第5282页,卷四百八十,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
[5]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6]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第404页
[7]赵德贵《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005年第3期
[8]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
[9]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