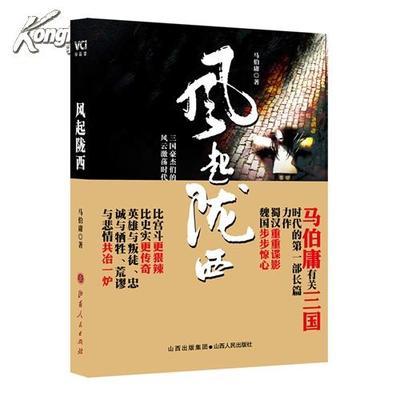
风起陇西
一转眼,奶奶已去逝十年了。至今我仍能十分真切地记得奶奶去逝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接到父亲电话我就往家赶,赶到家奶奶已经走了。之后,父亲按照老家的习俗为奶奶请了两班鼓乐队,在奶奶去逝的两天里,两班乐队用乐器配合着高音喇叭呜呜咽咽地从早吹到晚,尤其是唢呐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尖利响亮,在寒风中像用刀子在剌你的耳朵眼儿,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眼睛红红的,有着一种令人无法卒听的凄凉。到了晚上,这声音会随风飘出很远很远,那声音仿佛是在不停地告诉我们,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又一个亲人永远离开了,从此阴阳两断,再无见面的可能!
这样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奶奶下葬为止。当一座新坟立起来的时候,坟头那个硕大的花圈便在 寒风里呜呜地唱歌,嘶哑,神伤,断断续续,呜咽不止。我呆立在那儿,看着父亲在奶奶新立起的坟前磕头,看着没有燃尽的纸灰正冒着缕缕青烟,随风悠悠然地升上天空,飘得很远,我知道奶奶永远离开我们了。这个时候,唢呐也不吹了,不再有人哭泣,也没人说话,大家都静默地站在那儿,只有旷野的风从耳边吹过。
爷爷也为奶奶带着孝。爷爷和奶奶一生相濡以沫,奶奶的离去爷爷似乎没有表现得多么伤心,相反却脸色平静,毕竟爷爷已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安慰爷爷,爷爷只说了一句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奶奶一辈子不容易”。爷爷说完,再无他话,默默地坐在那儿,双眼平视,面无表情,一如平时的沉默寡言。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奶奶:奶奶面容慈祥,看着我不说话,她的头发全白,在风里轻轻地飞舞。“奶奶——”我叫着,挥着手向她跑去,可奶奶始终微笑地看着我,就是不说话。我追着追着,奶奶的身影渐行渐远,面孔也渐渐淡去。奶奶如同一缕清风,穿过人世沧桑,在岁月的轮回中消散归尘。
奶奶虽然身材瘦小,但十分要强,特别是对我母亲,能够拿出足够的婆婆权威。母亲对奶奶虽是满腹怨言,在我奶奶面前却也显得无可奈何。直到多年以后,再回想起爷爷给我说的话,我才理解奶奶的“一辈子不容易”。奶奶一共为爷爷生了7个孩子,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只活下来两个: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姑姑。也就是说奶奶一共失去了5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世间怎样一种莫大的悲哀与无奈啊!奶奶的这5个孩子有的很小就夭折,有的则是成人后死去的。今年已65岁的父亲对我说,至今仍然能够记得他大哥的样子。父亲说他小时候整天跟在大哥屁股后面玩耍,那时候到处都在搞运动,没有人理会小孩。大哥是在15岁那年毫征兆地得了急病死去的。父亲说,那个时候比较贫穷落后,医学不发达,不知道大哥得了什么病----父亲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死去的。而作为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在那个到处是饥饿灾荒的动荡年代内心里则充满了担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哪一个孩子会在饥饿和病灾中离去。自己的孩子离去,爷爷奶奶心中承受着多大痛苦?爷爷奶奶从未给我说起过。听父亲说,他的哥哥或姐妹离开后都是奶奶亲手用白布包好,爷爷用席子裹起来后亲手埋藏的。奶奶对于孩子的生死似乎已经麻木了,倒是爷爷以前曾对我说过,说那时候死一个小孩子太平常了,像死个畜生一样简单,死了就埋,没有人会太伤心。
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会给我说一些陈芝麻烂稻草、家长里短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奶奶给我说的大都是我们的一些家族往事,一大堆一大堆,乱七八遭,毫无层次。让我惊奇的是,几乎一个大字不识的奶奶,记忆力却这样好,并惊讶于她怎么知道那么多家族历史?那些家族历史有很多奶奶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显然她也是听来的。而在奶奶讲述的故事中,让我听来却有那么多不可信甚至是很可笑的东西,我很奇怪,奶奶为什么会相信呢?比如: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男性,而是一位漂亮的女人。这也是源于奶奶说给我听的。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奶奶对我说:“国家以前一直在斗小平(其实,是邓小平,在那个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每个人对斗字都很敏感,奶奶以讹传讹,显然是把邓小平听成斗小平了。在老家的方言中,邓和斗的发音基本相同),现在,小平又当大官了”。我很奇怪地问奶奶:“小平是做什么的?”奶奶说:“小平是一个大姑娘,不知道姓什么,大家都叫她小平,长得很漂亮,扎着两个又粗又长的辫子。听人说,她反对过毛主席。很多人斗她,就叫斗小平。怎么反对毛主席的人也能当大官?”奶奶看到我也不解的眼神,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了,听人说,斗她的时候,她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儿冲人笑。抬手不打笑脸人,是不是?这不,就当大官了吗?”我也就似懂非懂地顺着奶奶点点头。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奶奶就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只是想说明奶奶身上有一种纯朴的善良。很显然,奶奶并不是一位糊涂的老人,她经历过许多人世沧桑,阅历较深。也许,奶奶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有她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我只能这样解释。
而奶奶对我们家族历史讲解却让我从小就产生出了一种强烈而深邃的历史感,就像我小时候经常爬过的阴暗而潮湿的长长的圆筒涵洞,涵洞这头是黑暗的,另一头通明透亮,那一头的光亮深深地吸引着我。历史因遥远会变得很不真实,甚至以讹传讹而变得虚假。历史越虚假,越是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今天的真实。然而,我们这个真实的今天终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而后人,也许会有好事者花费心血来考证今天的真实。
按照奶奶的说法,我们老家在石梁河畔一个叫“三角汪”的村子,奶奶习惯上称那个村子为“老庄”。用奶奶的话来说,“那个村子真大,有一两千户人家”。我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搬迁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虽然现在村里的乡亲们仍管这个村庄叫“三角汪”,但在政府的命名中却叫“李庄村”,前几年撤乡并镇,现在的村名又改叫“新兴村”了。我问奶奶,那我们祖上又是从哪里搬到三角汪的呢?是什么时候搬过去的?奶奶说,听人说我们“老庄”是很久以前从一个叫“大里庄”的地方搬迁过去的,我们是一支二门,老祖宗是山河水三兄弟。这三个兄弟带领家人从“大里庄”搬到“三角汪”这个地方后便不走了,一辈一辈,生息繁衍出这么多后代。至于何时,因何原因搬过去的,奶奶就说不出来了。那时候,我年龄尚小,不知道什么是“一支二门”?什么是“山河水”?问奶奶,奶奶似乎也解释不出来。奶奶只是诉我,听老人说以前我们家族很大,家族里的人很多,家族里的人大都是识文断字的。至于家族怎么大?大到什么程度?家族里有多少人?奶奶又说不出来了。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说,到我爷爷的爷爷这一辈,也就是我的高祖时,家里还有很多土地(后,经我在家谱上查证,我的高祖是忠修公,忠修公是第十七世先人,字恕轩)。忠修公兄弟二人,弟弟道修公。我高祖忠修公生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宗贤、希贤、庆贤、招贤、求贤、建贤,我曾祖宗贤公是长子,而道修公却只有一个儿子荣贤。忠修公把自家土地分给六个儿子,六个儿子一平均,土地便没有多少了。解放后,斗地主,分田地,忠修公的六个儿子只被划为富农,算是躲过半劫,道修公的儿子荣贤便没有那么幸运了,被划为地主。奶奶说,宗贤公的四弟招贤一生都没有娶妻,死在“文革”初期。“文革”中,有一年春节,生产队里招贼了,仓库的谷子被偷去了一些,贼还顺手把一块猪肉给捎走。那个时代,粮食米麦、油盐酱醋就是生产队里最重要的家当,更何况是一块要过年的猪肉?起先生产队里没有发现丢粮食,只发现一块猪肉不见了,后来一查粮食也少了。那年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于是全村动员,非要把这个阶级敌人给找出来不可。不知是谁“告密”,说看到招贤从队里放肉的地方经过。于是,生产队长找到招贤,咬定是招贤年少好吃,偷偷摸摸把猪肉吃掉了,还偷走粮食。招贤哪里肯承认?一口否定,但招贤是个老实人,不说瞎话儿、不做坏事,勤扒苦作,显得有些木讷。他满肚子冤屈也没有人相信。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没有地方可以讲理,说你偷了你就偷了,偷生产队的东西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大好成果,就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招贤一时想不开,在春节后的一个夜晚,上吊自杀,死时不到三十岁。奶奶现在还在感叹,说小叔招贤是一个好人,很强壮的劳动力。后来,在村里一个外姓家里发现了被偷的粮食和肉,经大队查实,证明粮食和肉不是招贤偷的,但是,招贤已经上吊死去一个多月了。招贤的死,村里没有一个人为他负责,甚至也没有人挽息,死了就死了,社会主义的形势依然大好,村民们依然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奶奶讲这话的时候,我虽然仅只有十几岁,可奶奶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时脸上流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表情却让我记忆深刻。“文革”在我幼小的记忆中,让我恐惧也让我记忆深刻。
奶奶经常会给我讲述“老庄”的种种好处,让我对“老庄”充满好奇。多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去一次“老庄”看看,那个地方如今仍叫“三角汪”,只是村庄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爷爷奶奶过去生活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了。不要说远的,就连二十年前的痕迹也基本全无。按照奶奶的说法,原来石梁河水库的水一直延伸到村庄边上。“三角汪”村庄呈三角形,两面临水,一面靠陆,就像一个三角在汪洋大海边,所以才取名“三角汪”。我不知道奶奶的这种说法靠谱不靠谱?如今,石梁河的水位下降,沧海已变成桑田。原来的一些河道早已不见踪影,整个是一片黄土丘陵地。我开着车走在道路上,两边都是庄稼地,只有一些细细的河道,把大片大片的田地做了一些切割。由于是春天,路的两边到处都是小麦和油菜花,尤其是那油菜花,远远望去,一片金黄,风吹着金灿灿的油菜花,觉得脸上也是金灿灿的。我一个人走在田埂上,这时候的风吹面不寒,看着青青的麦苗一波三折,在春风的吹拂下绿浪一样,涌过来又退回去,天边飘荡着几朵白云,田野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的声音,我的心中升腾起一种沧茫的历史感。这里已经看不到旧时的东西了,仿佛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在我记忆中,爷爷经常会说起他年轻时的事情。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几个人半夜就起来,推着小车子(独轮车),天亮就赶到“大兴镇”了。那个时候,爷爷用方言讲话,“大兴镇”这三个字我听的最多,我不知道“大兴镇”指的是什么,也没想过“大兴镇”这三个字怎么写,但我知道大兴镇一定是个很大的地方,爷爷经常推着家里的独轮车到大兴镇去。这次去了“老庄”我才明白“大兴镇”今属于山东省的临沭县,位于临沭东南部,毗邻江苏省东海县。如今我推测,当年爷爷眼中的“大兴镇”就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到了“大兴镇”就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大兴镇”为鲁东南门户,有悠久的人文历史。据史料记载:明末,镇域属沂州郯城县管辖,但因距郯城太远,官府统治鞭长莫及,土匪滋生,有“羽山到磨山,毛贼出万千”之说。清康熙年间,为治理匪患,在靠近羽山、磨山的“乱沟山集”设置捕盗衙署。衙署主要官员为五品同知。首任同知李兴祖莅任后,将“乱沟山集”改名为“大兴镇”,取“大吉利、兴国安邦”之意。
那天晚上,我在“老庄”住下来没走,想了很多。我喜欢深夜,也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会去想一些飘渺的东西。有时候我感觉在夜深的时候我的灵魂才是自由的,可以四处飞翔,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想。其实,到底我在想什么,事后一点也记不起来。隐隐会记得,可能是关于老家的,但又毫无头绪,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年龄越大我越怀疑自己能走到今天是和祖上的遗传有关。比如说,和我的曾祖父有关。我从未见过曾祖父宗贤公,也没有听父亲和爷爷说起过他的事情。97年父亲和我为宗贤公立墓碑的时候,我问父亲宗贤公的名字,父亲不知道,父亲又是问爷爷和二爷,他们兄弟俩竟然也都不知道,这让我感到惊讶:儿子竟然不知道自己老子的名字。后来,村里老人解释说,宗贤公去逝的时候,我爷爷和二爷年龄太小,还不懂事。父亲和爷爷几乎都是文盲,识字很少,但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喜爱练字。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夏日午后跑到树荫下挥汗如雨地练习毛笔书法。看到我练字,村里会有年纪很大的老人走过来对我说,你随你曾祖父宗贤,你曾祖父年轻的时候就博才多学,写一手好毛笔字。如今,说这些话的老人早已先后离世,但老人的话我至今记得。我从未看到过曾祖父留下来的一字半迹,更不知道曾祖父的字能够“好”到什么样?所以无从评价。有时候我会想,我和曾祖父的区别仅仅在于时代不同,曾祖父不幸,生逢乱世。那个动荡年代充满战争和饥荒,充满疾病和灾难,很多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人是非难辩。村里老人说,曾祖父在我爷爷七岁、二爷五岁那年就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而去。可能对于曾祖父而言,安稳而富足的生活永远是一种奢望。而今天,却不同了,这种生活,触手可及。
历史无情,每个时期,总会有一批人受到时代捉弄。很久以来,我对家族的事情很好奇,一直想理清楚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来胧去脉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家族关系,但是,由于能够说出我们家族事情的人太少,加之年代久远,记忆斑驳,让我无法深究。比如说,我想知道祖上从哪里迁来的?出过哪些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一代又一代是如何生息繁衍到今天的?先祖们经历过哪些苦难历程?这个家族流转的脉博是如何跳动的?可我理了再理,还是理不清。越理越乱,沧海茫茫,大地无边,在这种追寻中,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丰厚和生命的神奇。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老一辈人都是这样说的。”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这样对我说。当然,我不会全部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呢?老一辈人都是这样说的,千真万确。”或许,奶奶说的是真的,她确实是这样听来的,她也真的只是照着这样来转述,口口相传,并无半点虚构。但是,我总是觉得家族故事的源头是有问题的。
春节期间回老家,我终于在族人家中见到了传说中的家谱,令我欣喜不已。我反复翻阅这些发黄的纸页,字里行间,先人的身影历历再现。家谱的封面上赫然写着“陇西致和堂”,这让我心中蓦然一惊,因为我知道,在历史上陇西是李氏的郡望,“望出陇西”是千百年的传承。陇西李氏走出了许多著名人物。如李广,他的军功在汉代边将中堪称第一,素有“龙城飞将”和“飞将军”的美称。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起自陇西,他们建立的统一而强大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还有诗仙李白,他在《赠张相镐》一诗中说:“白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候,当年颇惆怅。”在《与韩荆州书》一诗中云:“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可见李白认为自己是陇西人,且属李广后裔。长期以来,虽然知道李姓是大姓,肯定和历史上的李姓名人会有源缘,但从想过自己和遥远而陌生的陇西会有什么关系,更未想过自己的先祖和陇西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血脉相连。年幼时我不懂大人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家族旧事,年长后当我有寻根意识时,先祖们已纷纷离世,难以溯源。幸好还有家谱,还有字辈,真的要感谢聪明的祖先们发明了悠久的宗族文化,使我们的姓氏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成为有迹可寻的符号,而不至于在纷乱的岁月烟云中失去坐标,飘然无痕。只能说,我对陇西的费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和对自己先祖的无知。
遗憾的是,这本家谱上只记载到第十一世先祖,十世以前的先祖因年代久远失讳了。通过家谱记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家族生息繁衍的脉络,也让我弄明白奶奶在世时经常给我说的“山河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奶奶所说的“山河水”是指我的第十一世祖:李山,李河,李水三个兄弟。我是长子李山公这一支脉,家谱上仅记载李山,字秀峰,其他再无片字。在家谱上,先祖只是一个一个让我陌生的名字,或说家族符号。至于先祖有哪些经历或事由?再无他迹。后来,我联系上了本家李传亮,传亮本家热心于谱学研究,且收获颇丰。他一看到这本家谱便断定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的,不是古谱。传亮本家讲了许多我从未听过的先祖往事。经传亮本家考证:宋末元初之际,一世祖东藩公举家避祸,携七子,带着家资,具体从何处迁居江苏赣榆林头村定居,还有待考证。据说,东藩公还带来了《李姓统修世系图谱》。为防止被合家灭门,他安排七子分散居住,东藩公的七支后裔死后均葬于赣榆县林头村。如果用今天的卫星地图标注出东藩公七子在赣榆的居住地,便会发现,这七个地方呈北斗七星状分布,不知是先祖有意为之,还是一种巧合?总之,东藩公的七子之后逐渐繁衍壮大,遂有今天的盛况。
李东藩,字肇西,其被后人尊称为江苏赣榆“陇西致和堂”李氏的一世祖,“陇西致和堂”在赣榆当地李氏家族也俗称“七大支”,大概是为了纪念一世祖东藩公的七个儿子吧,也可能是为与其他李氏家族以示区别。从一世祖东藩公起至今,赣榆“陇西致和堂”李氏“七大支”已传到20世以上,经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如今李氏已成为赣榆大姓,据不完全统计后裔达20万余人,主要分布于赣榆、连云港地区、苏中地区及鲁东南沂水一带。
赣榆“陇西致和堂”李氏“七大支”家族关于一世祖东藩公的传说有很多。据说,在“七大支”中的一支后裔李亨去辽东。李亨之后,明后期与戚继光齐名的辽东名将李成梁即为李氏“七大支”一世祖东蕃公后人李亨的后代。东藩公现葬于赣榆林头村的墓碑是李氏族人于宣统元年(1909)所立。在十年浩劫中,该碑曾被毁迷失,2006年李氏族人发现其中一块,2009年又发现另一块,2011年粘合修复后重立。墓碑正面楷书:“始祖李大公讳东藩字肇西之墓”,背面亦有碑文,文字简约寥寥,仅60字,碑文曰:“公,陇西人也,元季墓于兹。二世七支咸附葬于前,某墓为某祖不可考。其西有指挥公墓,传谓有亨公迁于辽,指挥奉亨公后成梁公命,自辽来祭,殁,遂葬云。”碑文内容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大意是:“东藩公,是陇西人,元朝季年就埋葬在这个地方。二世七支都附葬在他坟墓的前面,某个墓是某世祖现在已经不可考证了。东藩公墓西边有指挥公墓,据传,亨公迁入辽东,该指挥奉亨公后人李成梁公的命令,从辽东来祭祀先祖,去世了,就葬在这个地方。”在东藩公墓西,确有一墓,墓碑上书“明故辽东世袭指挥李公墓”,该碑同样立于宣统元年,应是和东藩公的墓碑同时所立。据本家传亮等人考证,这段历史在东藩公九世孙李振翼于乾隆五年(1750年)10月份修订的李氏“七大支”宗谱中所作的《附关东分支纪略》里确有记载:“辽阳榆林有吾李分支,远年以来,传闻明季有成梁公迁辽东,以军功封宁远伯。或谓应役边城,或谓荷戈从王。文献两亡,证信无从究。未知其去自何年,分自何支。万历间,公遣官指挥者(失其名),自辽东来祭祖墓,并修书致侯族人。将归,坠马卒,遂葬祖茔西。至今有指挥坟。云其时,本支君案兄之曾祖永鑑公、敬宜兄之曾祖永泉公,不惮跋涉,亲至辽地,盘桓数月。迄归,赠有宝刀一口,命付武士;玉砚一方,金墨一笏,命付文士。并维藩公履历一本,光荣公合同一纸,由行伍军功宦游而家焉者也。及崇祯年,流寇猖獗,岁无宁日,履历、合同、宝刀、玉砚俱已沦亡。唯金墨之存于君案大兄家者,仅十之一焉,今当修谱之日,谨将往事列于篇首,以志李氏子孙于辽阳榆林大有人在……”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明万历年间,赣榆族人永鑑、永泉二公应邀赴辽,受到李成梁的热情款待,盘桓数月,抄回在辽分支谱系,并增送礼品数件带回赣榆。但李成梁何年派使者回赣榆林头村祭祖,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以确定,该使者就是“辽东世袭指挥李公”,推断当为李成梁子孙。但是,所有这些记载我都没有看到真迹,只是听族人所言,或是看到抄录的照片,不敢妄断真迹是否还密存于世。但我相信这些是真实的。
据传亮和大春本家考证:李东藩带来的宋时或更早的《李姓统修世系图谱》卷全长十米,现存七米,上有南宋洪迈、吕祖谦、赵汝愚、魏了翁等当时名流的题字和赞语,据说还有宋代名将岳飞的题词。赵汝愚是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在卷谱是的题词是:“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萃文翠。”从题词可看出赵当愚对此卷谱作出了高度评价。据说,该卷谱由李东藩带到江苏赣榆后,在这六百多年间一直由李氏“七大支”中的五支后人秘藏,几乎从不面示于人。我虽未看过真谱,但前段时间见过本族人展示的该家谱及赵汝愚题字的照片。照片上,族谱中的人物画像颜色驳落,但尚清晰可辨,书法也有宋人风貌。据族人推测,李东藩字肇西皆非其真实名讳。据传亮本家初步考证,应在南宋理宗年间,东藩公参与或是受到祸事牵连,才连夜携子带谱出逃。在清代,东藩公后人把堂号由“陇西堂”改为“陇西致和堂”,以记念东藩公迁入赣榆的年代和原因。据查证,“陇西致和堂”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清同治八年的赣榆李氏“七大支”宗谱上。李氏“七大支”后人每到清明,必集于东藩公在林头的墓地,祭奠先祖。几百年来,李氏“七大支”后裔家风清白淳厚,爱读书重信义,善持家守法纪,人才辈出。据说,我们李氏“七大支”共七支三十八门,家谱上显示,我们这一支脉是出自“一支二门”,原来奶奶一直以来口口相传的“一支二门”是这样由来的!
李氏“七大支”先祖历来对本家族排字论辈非常重视,以字辈来别长幼、定尊卑,在清乾隆五十五年便立下了赣榆“陇西致和堂”李氏“七大支”命名排字韵语表:“兆泰安穆德,融舒世亮恭”等三十个字辈。在道光二十五年,“七大支”合族商定,对韵语表重新命名排字,即:“泰安宗裕庆,传家大启祥,显文荣盛世,永锡萃群芳”。在1970左右,“七大支”后裔又合族商定续排行40字,即:“元臣祝厚泽,为善济时康,诗书从汝景,道德守奕香,中和润化育,勋业名振扬,云仍怀至宝,万代炳余光”。共计六十二个排行字辈,这六十二个排行是从十三世开始,能够延续到七十二世,这是连云港赣榆李氏“七大支”全宗族的统一排行,是宗法规定,不准族人用他字起名,以防混淆世系。吾辈生也晚矣,排在“大”字辈,“传”字辈以后的人大都出生于解放后,特别是从九十年代起,字辈、字号等已不再流行,取单名成为时尚,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知其祖,无论字辈,更有甚者,取名和其先祖相同。字辈已如“广陵散”,渐成绝响。
我原以为找到家谱,就可理清先祖的痕迹,根据字辈,可从宗谱上清晰地查找到历代先祖的名讳。可我反复翻阅后却发现极难做到,其原因是宗谱编排没有令人一目了然的树形世系传承列表,而是按字派横向归类承接。但古人除本名外,还有字、号等,修谱者又为避讳常用尊称。比如,我的爷爷书祯公和二爷书祥公,在家谱上的名字分别叫兴杰、兴仪,幸好在谱名后还注了书祯、书祥的字样。如不标注,就更难以理清了。
在家谱上可以发现一些家族蛛丝马迹的旧事。比如,家谱记载:十五世建春公的长子继田公迁居扬州,但继田公是何时迁居的,家谱上没有注明,只在继田公的名讳下面写了“迁扬州”三个字。按年代推测,继田公迁扬州的时间应在1896年左右,不知道继田公迁扬州时,是否带有家谱?以便于后人认祖归宗;比如我爷爷,按排辈应该是在“传”字辈,父亲应是“家”字辈。可现实中爷爷却是“书”字辈,父亲却是“国”字辈。问询家族中的老人为何不按“传家大启祥”这样的韵语排辈?老人的解释是,很久以前,我们这一支脉因迁移已久,和李氏“七大支”失去联系,不知何因,无法修谱排辈。因“老庄”靠近山东,便随山东一门李姓的辈份取名了,如此几辈,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和李氏“七大支”接上,重修家谱。老人的话从侧面也印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修订家谱的这一事实。我想,如果我现在不记下个中缘由,恐怕后世子孙又要为之头疼了。
今年清明,我又一如既往地赶回老家祭扫先祖,站在二水交汇的先祖墓群前,一块块先祖的墓碑,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让我深刻感受到家族的意义:无论命运如何雕塑一个人的生命形态,都改变不了其与生俱来的家族血统。而顺着这个家族的根源上溯,便可以追寻到一个家族如烟的往事,尽管山高水远,有的已经模糊难辨。这次回老家,让我感慨万千,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家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会越来越对家乡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保持着这份深深不渝的情感?老家除了父母,还有什么在吸引着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可能是在我骨子里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渗透着这个村庄印痕的浓浓水土气息。我想,应该还有,那就是家族的血脉,虽然我远在千里之外,但内心深处时常会感觉到有来自家族的风吹过。那是来自陇西的风吗?
那个上午,给爷爷奶奶上完坟后,我跟着父母来到自家的菜园子里,看母亲种菜、浇水。我在旁边插不上手,干脆就什么也不帮,在田埂上走来走去。春风拂面,吹面不寒,从父母默默劳作的神态,我能够看出生活对他们的诠释是多么简单。风过不留痕,却留下了岁月的沧桑,看着父母已经花白的头发在风中轻轻飞扬,看着他们身上脏兮兮地沾满了水和泥,看着父母的身体越来越佝偻越来越老迈,我知道在他们身后是先祖们祖祖辈辈走过的田地,先祖们在这块土地上简单而又实在地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生息繁衍,自强传承。先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无非是吃饱了穿暖了,要求不高,可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在他们身上也没能实现。幸运的是我和父母都没有生长在那个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的时代。但是,如果没有先祖们一代一代含辛茹苦、自强不息地繁衍,又如何有我们呢?我站田间沐浴着习习春风,远远地看着父母亲,看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在这样乡村的风的洗礼下渐渐烙上了一条又一条岁月痕迹,我知道自己早晚也会和他们一样老去。而我和父母不同的是,无论我愿意不愿意,归宿都将会在城市中那些又冷又硬又苦又涩的风里,不会像父母那样有福气,能在祖祖辈辈沐浴过的风里相伴一生,幸福终老。
而无论如何,比起那些老家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灰飞烟灭的游子,我还是幸福的。有了老家,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根,顺着这根就能够上溯到先祖的历史,老家使家族血脉相连,就像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一样,期间的每一个水分子都有着他们的来处,无论离开的时间多么久远,总可以溯流而上,找到源头。
起风了,这是一袭瘦长的风,自三千年前蒹葭的传说中吹来,从我先祖的陇西吹过,翻山越岭,万里跋涉,驰骋纵横,浩荡无羁,无所拘囿。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