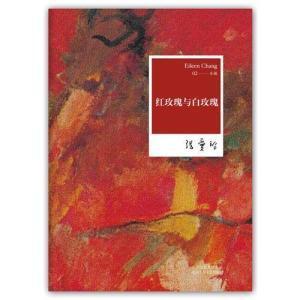惘然记
惘然,与慷慨不同。慷慨是一种激昂和喧哗,波浪式的。惘然是静悄悄的,像黄昏的日影,从这边,移到那边。然后,不见了——但又并没真正消失。
慷慨是火,惘然是灰烬。
惘然,有一点无奈,有一点迷茫。像一根线,那么细,那么长。剪不断,理还乱。缠来缠去,搁哪里,都不合适。最后,只得揉成一团,攥在手心。
惘然,离惆怅极近,近到零点零一毫米。几乎就是惆怅。叠在一起,就是怅惘。这种感觉,在很多中国文人内心深处,总是挥之不去。很久很久了。几千年来,像黄昏的日影,移过来,移过去。然后,不见了。
然后,又出现了。
怅惘,如果再进一步,也许就是绝望。再进一步,就一脚踏进沙漠里了。茫茫几千里,除了黄沙就是黄沙,就是看不到人烟。
但越是看不到人烟,却又越感到人生的苍凉。

惆怅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人化的?《诗经》里的喜怒悲乐还比较单纯、直接。《九歌》里面,已经有了惆怅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男人和女人,最早开始了怅惘。到了张爱玲的世界,男人和女人之间,怅惘格外普遍。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就惘然,真是够早的。那么,压根就不开始,如何?但,由不得自己的。其实,还有很多事,还没开始,就已经惘然了。
所有的情缘,说到底,也都只是世缘。
惘然记,记的其实是张爱玲的《半生缘》。
半生缘,倒换来了一生惘然。
2014-8-20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