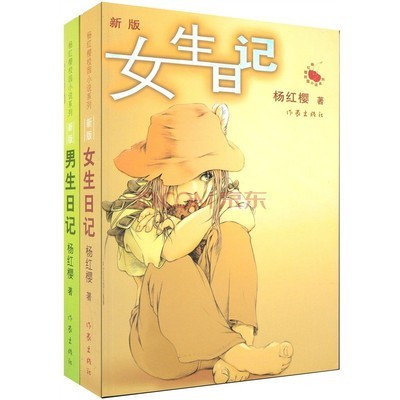神灵的词语,或雪粒划破空气的声音
——读诗札记:阿信的《草地诗篇》
这么说吧,即使阿信以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地为背景已经为我们写下了如此绚烂的诗章,我们仍然认为不够——阿信的《草地诗篇》引人注目并带给人们重要的幸福感,这就是好诗永远不够的原因。以我的粗浅阅读经验,阿信的诗,需要慢慢的细读(至少我不舍得一口气读完),词语在他的诗中总是能被安置到最令人信服的位置,那种小心翼翼的分寸感,让人有种(像本雅明提到过的真正的普鲁斯特的读者)“无时无刻不陷入小小的震惊。”必须说,这来源于阿信“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惧”信念,他是一个容易在接近写作对象时的受惊者,他永远不会旁观,在孤寂的深处或瞩目于秋原之上一只黄金的杯盏,或聆听只有雪粒划破空气的声音;他对事物有着每每返顾自身的入迷,对诗歌的敬畏感从来都不需测试,他写道,“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速度》)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诗人里,我认为阿信的诗是唯一紧紧地贴着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地的,那种紧贴的决绝如他的命运和生活,突然间的,固执,疼痛,毫不犹豫的服从,有着普遍的寂寞;如果说阿信的诗中有神的声音,我认为不完全如此,或者说这是一件很可疑的事,阿信的诗并没有表现出来说出真理的晦涩玄虚,他的诗严峻而伤感,很多时候有种像弗罗斯特那样“一边叹息一边叙说”的味道,诗句大多时候读起来有种抑扬顿挫的音律感,这也是汉语诗歌的独特的魅力之一;阿信还善于机敏锐地运用语调,利用标点符号的节奏,适当的停顿,合理分配词语的序列,但多数诗篇被修辞性的感叹修饰了,不免产生了与散文相近的阅读效果。人们对散文的警惕其实就是对诗意流失的担忧,但在阿信那里,他对自然和心灵的事物有着凝炼的洞察,所以他的每一首诗几乎都具有光彩照人的庄严感,纯粹,明确,河流般的宽度,个人的声音,富于美感。
***
和昌耀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谈。我曾和人这样谈阿信的《草地诗篇》,我可以举出《斯柔古城堡遗址》这首诗对比昌耀的《哈拉库图》作例子;结果,我必须说,一半的人并不喜欢阿信的诗,不喜欢的原因是以前那个大诗人昌耀写得比阿信更孤绝。每次说到昌耀反倒对我是个及时的提醒,阿信的诗确有一部分昌耀诗歌的因子(影子),比如你发现了他们是如何让诗与自然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他们常常明确的表现出了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以及逆境中一个诗人的强力信念;看起来他们都像是与尘世隔绝的诗人,不妨说他们的确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在中国,这种陶醉于自我的伟大或许更像是一种孤独的品质。
阿信的诗在近些年越来越呈现出了强烈的形式感,这种素描式的表达形式对词语有着眩晕般的要求,也就是说,词语在诗篇里要么是黑白的,要么是苍黄色的,还有线条与结构都作为一首诗的重要元素构成文本,至少,阿信的诗在视觉上首先阐明了他的理念——形式即实体。比如《在草地上》有两个词分外耀眼,“菌类植物”“一柄巨锤”,这是一首冥思的诗,怎么说呢,有点“道成肉身”的意味,“道”使词语产生了“肉身”的此在意义,“在广阔的时间上久坐:我,和谁?”不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要把这首诗和昌耀的《斯人》拿来对比阅读,“静极——谁的叹嘘?”昌耀的拙朴壮阔和阿信的语言线条美不可等量齐观,但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诗都是形式和观念相互融合为一体的雄伟样本。
事实上阿信要比昌耀柔韧的多,昌耀的力量在于,举个例子,就像奥克塔维奥·帕斯对亨利·米肖的评价,“他从不犹豫于折断一个词的脊梁,就像一位骑手从不犹豫于勒住缰绳。”而阿信的柔韧在于用词语表达可表达之物的无限性——无处不在的线条,不可描述的涡旋,事物的现形,彼处的符号,此处的沉思。
***
位置感对阿信而言是非常敏感的认知模式,哪怕他描述最隐秘的事物时也会同时将自己说出;仿佛说出才有意义,说出才有“我存在”的了无遮蔽的时间-空间感。为什么要强调阿信的位置感,从阿信的诗中我们可以轻易的体味到他的安宁的神思,若神思不宁是无法取得与他原初的思想相和谐的位置感,也就是说,阿信为他的诗写苦苦寻觅激情至简的观念之乡。
“最初我是从一片洼地开始起步,现在/我想我已经来到了高处。(《9月21日晨操于郊外见菊》)”这就像写小说一样强调第一人称带来的那种当下的存在感,他无需臆造心目中的光芒普照的净土,位置感不是屁股下面某片地方,而是譬如从“洼地”到“高处”的为物象所伏的凶险,或者是背道而驰的幸福归途。这种位置感的文本典范就是《加油站》,它有借助想象的细节:“一间巨大的心室,连接动脉、毛细血管,持续泵出燃烧的液体。”这首诗关注的是可以验证的假设和需要被我们重新省识的隐秘初衷,诗意转瞬即灭,“不能想象一夜之间所有的加油站发生类似短路或血栓堵塞那样的故障,道路瘫痪像一截截被打断脊椎的蟒蛇,紧紧缠绕在这个星球上:直到窒息。”叹为观止的想象逆转是对死亡的思索,或如剧情般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错觉,“如果有个疯子,在每一口油井,插入一根捻子,在圣诞或平安夜同时点燃。”怪象仅仅是表达的问题吗,他的奇特的修辞是,“一只巨大的红色蟾蜍,蹲踞在必经的路口不避晨昏,”它到底要表达什么?自我救赎抑或吐纳观念,在形成惊险对峙的位置上,马拉美用过的“偶然”一词即使多用几遍也晦暗难辨,阿信困惑的是每一次的自我的身体,构想它和客体的距离,“绕也绕不过去。”
如此来说,在意义的空间里,我理解的阿信的位置感乃在场之中的打量,这是一项难以察觉的诗写传统,倚仗诗人的词义精确的技艺,“一个哈萨克牧羊人,背对着风,向我借火。”(《在当金山口》)
***
我们可以认为阿信在诗中给自己定义了一个平和的人,庄重的,遵守天人的秩序,清澈却非幻象,“晚年,他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破败的故乡。”(《唐·一个诗人的消息》)或“我恬退、怯懦,允容了坏人太多的恶行。”(《墓志铭》)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惟其本质上的素描,这是阿信的如此本原的自画像,我们识得其中的自谦和诚实,他对自己太过严苛了。
“我于这样静寂中每每返顾自身。我对自己的怜悯和珍爱使我自己无法忍受。我把自己弄得又悲又苦由绝望又高傲。我常常这样:听着高原的雨水,默坐到天明。”(《独享高原》)人即风格,我这么看阿信是想表达我对他的可怕的孤独表示一种敬意。阿信的风格(或趣味)是古典主义式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阿信对现代主义式的荒诞风格是持敌意的,他感受到了人类的苦难却断然拒绝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犹如茨威格对罗曼·罗兰说的,“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突然荒诞而让自己随之乖戾。”世界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设想为一个悲剧,问题是世界并不恐怖,相反有一种联结着一切和人有关事物的怜悯,作为诗人的阿信,他对世界的悲剧性一面是屈从的——他是那种秩序的一部分,意识,古老的传说,敏感于万物的本质,理解力。
所以阿信的诗多第一人称,他多仰视,或“星辰居上”或“云朵乍现”,也远眺,或“遍顾无人”或“晃荡不定”,更多的如昌耀俯首苍茫,或“我更像个匠人”或“……但我想,我是有点痴了……”,目光追逐着所视非物,仿佛奋不顾身地样子,他将植入心灵的事物对我们陌生但对他却是熟悉的世界,他太热衷于那种世界了,“与一盆牛粪火靠得这么近,”“与一对夫妻睡得这么近,”“与一座天空贴得这么近,”“与一场霜降离得这么近,”(《帐篷中的一夜》)阿信沉迷其中的持久的单纯,一如苍茫夜色中的沉睡者,幸福与倦意横生的阴影才是其真实的存在。
***
阿信似乎常常为形式感而不安,他也确信形式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有着实质上的困难(谁还没有困难呢),困难在于形式感是一种风格的局限,但他的核心解决方法常常令我惊诧不已——逗号,句号,冒号,省略号,破折号,等等,沉闷无趣的标点符号像播撒种子一样被赋予了文本意义。令我惶恐的是,我这个荒唐的发现会不会得到阿信本人的支持,他会忍俊不禁还是正色以对?
阿信表现在形式上的理性规律首先是一种克制,他没有被虚幻之美震撼以后的极度亢奋,他怀着谦卑的虔诚,“以神的名义:我不能被发现。”(《秘密的时辰》)这首诗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它的出发点却是世俗的,在我们忙于应付乱七八糟的生活时,总会碰到一个“秘密的时辰”,“这是仅属于我俩的秘密时辰。”阿信的专长是,他能够把古怪的众人参与的行为处理到个人的命运纹路里去,这不是最大胆的黑色幽默,我确信出自他的正常的内心世界的声音。
阿信为什么要使用标点符号来结构他的形式,这才是个古怪的行为,我的分析,他努力在把无意义事物投入到了有意义的事物里面以求得对立层面上的意义,或许,如此这般意义构成了他需要的秩序局限。在《挽歌的草原》中,他使用了5个冒号和5个破折号,重复是这首诗的核心技艺,“挽歌的草原”,然后加了冒号;在冒号的后面,所有的诗句都用于一个目的,对“挽歌的草原”注释,破折号句子则是起转折作用的补充注释,但功能更强大,更具戏剧性,“——但忘记了弦子和雨伞”“——但没带箱子和缀铃的铜圈”“——但一桶酥油在山坡打翻”“——但鹰还在途中”“——但远处已滚过沉闷的雷声,雨点”,完全是视觉上的宏阔而素描式的画卷。
仅仅是标点符号的形式感么?标点符号的形式感是一种诗写局限,阿信的形式感局限表面上看是受限于必要的停顿(须借助标点符号的卡位),实质上,他果断的意识到了卡佛式的留白局限,瞬间乍现神的虚象以求得全知全能的寂静效果,如“而一切的幻象:匆匆,无痕”。(《有雪的风景:拉卜楞》)
***
说到对细节的考查,阿信的诗篇里蕴涵着一种力量,这力量来自他对书写对象的细节的详备考查,尽管险境昭然但他绝不迷茫也从无畏惧,而且往往在这个时候,他有随时献身的意愿和应运而生的词语,但他对语言的晦涩却是持警觉态度的。
《夜》里有一句是这么写的,“睡眠里我像一枚掉在路上是土豆”,这首诗异常安静,仅有的一点点声音的迹象都被取消了,仿佛睡眠设置了“我”朝圣者般不慎中断的旅程,但依然在敲通向村庄的大门,那个村庄,是“我知道有鸟掠过今夜的村庄。”“薄薄的银子的村庄。”阿信用词的节俭习惯使得他用词清晰,虽过滤了很多丰富的感觉,但却有一种疏朗坚硬的质地;他写鹰如画像,“鹰,肉体凡胎。”“鹰:一个真正的汉字。”(《鹰》)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鹰原来是这个样子,孤寂而亲近。
《在尘世》是我读到阿信的最难以忘怀的诗篇——它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日常生活的截面,也是阿信罕见的一次对自我的异乎寻常的审视,他在诗写中保留了小人物艰辛而顽强的东西。这首诗阿信一反常态抛弃了自己的抒情天赋转向了舒缓的叙事,“在赶往医院的街口,遇见红灯——车辆缓缓驶过,两边长到望不到头。”接着阿信靠叙述的细节推进诗意,“我扯住方寸已乱的妻子,说:不急。”这里面有一种从侧面过来的均匀的气息,我太喜欢了,“初冬的空气中,几枚黄金般的银杏叶,从枝头飘坠地面,落在脚边。”这个过渡的句子有点油画的构象意思,就像随后阿信夫妻二人的卑微,“我拥着妻子颤抖的肩,看车流无声、缓慢地经过。”接下来的诗句的力量让我深有感触,“我一遍遍对妻子,也对自己,说:不急,不急。”如此令人信服的宗教般的宁静和隐忍,“我们不急。我们身在尘世,像两粒相互依靠的尘埃,静静等着和忍着。”
至少我已经获得了一个朝圣者的固执而谦卑的形象,一个诗人孤独的形象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他没有忧郁的情态,也没有愤世的不满,他很稳定,他的意志如他写下的一句诗,“我将要沉入那黑沼的中心”。
***
臻极化境的语言。这话用在阿信的身上有点危机四伏的意思,不可能无人置喙,谴责和反对一应俱全的正常,但我的偏执虽面目可憎却也是傲慢的,坦白地说,我认为阿信的语言有着殿堂般的辉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绝没有说阿信的语言是悲剧的、神圣的,我说的是,阿信的语言关注人的命运局限,也正因为如此,他让他的诗拥有了普适而持久的力量。
昌耀和叶舟的词语、句式,对阿信而言,这不必作过多评论,我只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斯柔古城堡遗址》和《草原(之一二三四)》。拿阿信的《斯柔古城堡遗址》对照昌耀的《哈拉库图》我不需要解释任何动因,只是我崇敬而已——自具面貌,结构匀称,奇节横生,虽有工巧造诗之嫌,但语言更臻纯熟细腻。昌耀是一代横绝之巨匠,他自有一种爆裂的力量,并不知疲倦的制造了自己的语言、结构、诡辩、况味等养成格调,愈老愈形质坚苍,与时代的病苦美学标准对峙。显然阿信在这首诗上受了昌耀的启发,确切地说,令人怦然心动的心醉神迷使得阿信如此真挚的迎接了诗的大忌——他能掩饰接近的距离么——对昌耀的靠近和遗忘?叶舟的风格在写《大敦煌》的时候就固定了,那种疾速和散漫,转换和错位,透明和碎散是他本人敞现心灵的唯一画像,但不接地气——阿信的《草原(之一二三四)》如此,我称之为绝对的奇迹诗写,但奇迹这种东西是无根的,呈现出来的形象悬浮于虚空中,最后靠精心筹措的语言点亮文本的透明性。
阿信的语言是刻意经营的,如同托钵僧式的坚持他的法度之严密、声调之跌宕的变化,他仿习但剧变,“这一切,都是在一场持续数月的热病中完成是。”“我尽可能保持这种冥想和高热的状态,直到奇迹出现,”(《一个酥油花艺人与来自热贡的唐卡画大师的街边对话》)那种语言就是跳出了事物或人群中的语言,呈扇形逐次展开的语言,没有固定位置的语言,相互凝视的语言,舞姿同一的语言,穹窿般的语言,对现实冷漠的语言,匠人的语言,臻极化境,不知死亡为何物的语言。
***
在阿信的诗里我们感到了强劲的诗意。我想说,诗意即风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个人来说,诗意很有可能是一种狡诈的圈套,抑或执拗己见的偏好。但我们必须确信一个事实,对一个人来说,一首诗只有纯净(这个词容易被误解)的诗意才可能真正触及心智,哪怕如阿信对草地农牧民苍凉生活的准确描摹,“十月霜重,一个挨家挨户分发新鲜牛奶的藏族妇女,用腰际叮当响的银饰,把这个黎明提前唤醒了”(《十月》);或将一只甲壳虫视作“草棵间一座失而复得的古代宫殿”。(《甲壳虫》)困难在于,我们如何给“诗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不使我们失望——比方说,诗意是一个神秘而煽情的礼物,诗意还可以是一种复杂的地形;诗意是无生无死的睡眠,诗意是向幽灵敞开的一扇窗户,诗意目击了一坨牛粪。
关于诗意,不管愿意不愿意,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总是受困于可笑的幽默和可憎的事物,而不是如莱辛说过的两句诗,“那激动他的,也在激动。那愉悦他的,也在愉悦。他得体的趣味也是整个世界的趣味。”我个人的体悟的是,诗句转换为诗意这是诗的基本要求,在于展示不可见的精确和在于展示可见物的陌生,在于密室中的微弱星火点亮幽暗的颤抖和返乡之路的居停歧途,在于豁然和不解。阿信是这样处理诗句以生发诗意的,如“落日炉膛中,一块燃烧的焦炭。”(《扎西的家》)如“劈柴和牛粪垛子高大的轮廓。”(《折合玛》)如“昏暗光线中的肉案和砧板上忽明忽暗是刀子,一具冒着热气的牛头骨……”(《玛曲的街道》)难逮的诗意被捕捉到了一个遵从于现实的角度,似幻觉的含糊其辞却又勾勒出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生命的表象,在阿信那里,诗意还是莫名伤感的“天色暗下来了”,(《天色暗下来了》)也是怅惘的“你看我又一次两手空空,出现在这里”,(《秋天记事》)更多的则是被盘问的“一个有关灵魂方面的问题”。(《九月》)
***
对地理名称的热忱书写可以理解为阿信对返乡之路的寻觅,有时他有点炫学和专研典事的意思,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我不会将阿信的用意曲解为受时风所染。他写草原因为他不是一个牧人,他写寺庙更不能证明他皈依佛门,他与神的关系,中间隔着返乡之路上的草地、山口、寺庙、沼泽、河流、城堡,甚至加油站和祭坛等等,明晰、优美,尽于夸饰,但不乏怀疑论式的深刻。
这些地理名称——阿信的登程习惯:流连而忘返,迷途而未觉——有一种另存他解的永恒性,举一例:“黄河边上,低矮的棚屋,入住了最初的居民:筏子客、篾匠、西域胡商、东土僧道……之后是不绝的流民和兵痞。”在这首题为《兰州》的诗里,阿信若手持一把弧形单刃的阔面刀器,将兰州的风貌不嫌拘牵琐碎一一剔出,符号般用字铸句,“羊皮筏子”“白塔”“铜佛”“开窟造像”“设立王廷”“清真寺”“民国”“炼油厂”“公社”“解放牌汽车”“河面”“铁桥”等等,使得如“来自靖远的师傅发明了一种把面团拉扯成细丝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也在他的诗里成为兰州的典型,这也是名词写作的长处,形貌宏伟,肤阔闳丽,虽繁缛但情味重,耐住一而再的阅读。
还有一部分诗阿信写到了寺庙,举凡“郎木寺”“大金瓦寺”“拉卜楞寺”等,在寺庙里他按住了人们通常的形容佻达,举止逸荡,不以谵语描述寺庙名物璀璨,“远离尘嚣,穿过一条藻井和壁画装饰的长廊。”(《大金瓦寺的黄昏》)“一个廊柱和壁画间轻轻打鼾的喇嘛,一个角落里浮现的神,和四株菩提。”(《一座长有菩提树的小院》)“触手可及的经卷、巨、僧舍,以及娜夜的发辫,”(《正午的寺》)此间可见阿信不厌其烦追求熟巧,他即便雕凿奇警也是必要的技法。
阿信在他的诗中并没有给予他写下的地理名称以种种形象,他无意轻鄙他写下的事物,因为他的诗本身就是这些形象——我们若以诗的方式理解阿信与地理空间的意义深长的关系,就会发现他在其间的敏感角色,身体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阿信昧于侧身于此的妄嗔消散的秘密。
***
阿信也不例外。局限的存在是必然也是屡见不鲜的情况,其实每个诗人都在各种局限的真实中写作,局限让文本呈现它的风格性,这也应了臧棣那句话,“从秘密的角度看,诗的风格类似于一种信仰的风格。”
这就回到了关于诗歌的古老的永恒性问题上——诗歌不去定义什么,而是诗歌界定什么?这就是局限。比如,当我们读到“一部命运之书:三个可疑的读者”(《星座》),是不是读出了转瞬即逝的东西、盲目的屈从意识和探囊取物般的幸福感?如果是,那就说明了诗在本质上是一种巨大的局限,诗歌界定了存在的事物。阿信的诗在基本格调上属于缅怀性质的——文本出之以回忆、唱酬、幽黯、崇敬,他既“和一只黄羊面对整个黄昏”,(《草原之二“黄昏”》)亦如“独奏于叶茎之上的一只秋虫……”。(《日暮,在源头》)甚至,阿信的诗写是消极的,消极局限使得阿信的诗看起来总是思虑事物彼此间的相互确认,比如昼与夜,衰与荣,纯粹与瑕疵,冷漠与热烈。
阿信的诗大部分非常简单,我的意思是,阿信的诗像三缄其口后的产物——他擅长克制喋喋不休的情绪和制约桀骜不驯的性格,没有不明底里,他的词语和观念惊人的对等;简单的局限带来的后果是想象力的被剥夺,阿信的诗貌似如此,他的诗有一种描述的秩序需要,事实上,阿信的有意使感受力钝化但文本却呈现了声音、线条和色彩的结构,“夜晚的女儿:手执银壶,头戴璎珞,星眸流转。”(《陷入》)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荒诞事物有害于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诗歌列入荒诞事物的序列中大抵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这是个恶作剧式的话题,意在嘲弄人的无能为力。我其实是反对一切因果机制事物化的,在这里我想说阿信的诗,他拆开了荒诞的事物,让我们洞见了结构清晰的使我们感到惭愧的生死意义——人不能屈服于现存的事物,但不能不敬畏现存的事物。这,也是威廉·布莱克的伟大局限,他的局限也是阿信的——无法对物质主义作出任何让步。
2014-07-26/2014-07-3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