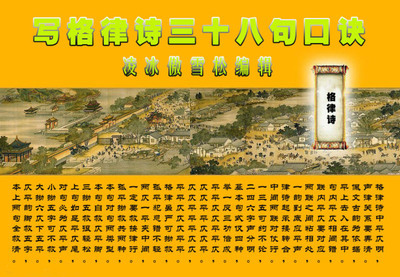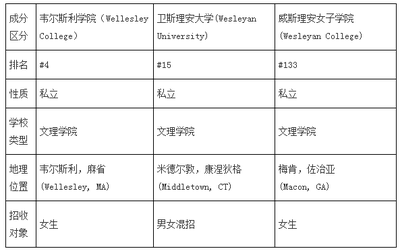【原创】花季中的碎片
——大山深处 我家三姐妹第一批赴顺昌插队
作者 老猫侠
1968年11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由福建机器厂等组成的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福州一中、八中等五个单位。
1969年1月23日,福州市革委会举行“福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欢送首批1264名知识青年赴顺昌县插队落户。
——福州大事记(1949—1999)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令,我与大姐、三妹同属“老三届”,只能别无选择地踏上这条道路。
当时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不仅不能回家,而且工资也被造反派扣发,全家老少的生活重担全都挑在母亲孱弱的双肩上。以往的亲朋好友因避嫌都离我家远远的,母亲欲借贷也无门可入,让我们幼小的心灵过早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寡薄。我的二舅当时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一个采石场采石,劳动强度相当大,而且家庭负担也重。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二舅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帮助母亲,让我们全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这份深情我们永世难忘!
自从知道我们三姐妹要同一天去插队以后,母亲的话语就明显少了,强忍心酸,默默地为我们整理行装。我的记忆深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幅清晰的画面,在龙山老屋昏黄暗淡的灯光下,母亲与幼小的四妹在埋头为我们缝缝补补,母亲的两鬓已露出白发,苍老了许多。这幅画面象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直到如今不能忘却。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69年1月24日,终生难忘的日子。福州四处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我的学校福州一中是福州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地点在闽北顺昌。就在这一天,我和大姐、三妹,携带简陋的行李,就要一起奔赴山区顺昌。
离别的那天,我们在福州火车站登上的是闷罐货车,所有的车窗都紧紧关闭着不能打开,站台上站着一排带枪的士兵,不让送行的亲人靠近。记得在火车站广场列队等待上车时,由于文革时期的派性关系,一中“东方红”一位高一男生的臀部被一中“八.二九”的一位男生用刀给捅了。当时只是简单包扎了伤口,就跟随大家一起登上火车出发了。
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开动了,站台上锣鼓敲得更响,送行的亲人挥舞着双手。在连续的汽笛声中,车上车下哭声渐起,伴随着车轮的哐啷声,哭声越来越响。一位女生双手死死拉住车门不让关上,嚎啕大哭,为的是要再看一眼故乡,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随着列车的奔驰,福州离我越来越远,我的心里充满迷茫和悲痛,此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我的家乡?不知是哪位领头唱起了歌,渐渐地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天黑了,刚才唱歌的人累了,车厢里沉寂下来,月光从窗缝透进来,冰冷冰冷的。我闭上双眼,但怎么也睡不着。朦胧中,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有个人在高声喊叫:“洋口到了,去洋口的下车了!”我与大姐、三妹不在一个地方插队,我在洋口上凤,大姐与三妹在大干罗坊。我在洋口下车后,想看看大姐与三妹在哪个车厢,但没有看见。马上列车又开动了,渐渐的消逝在黎明的晨曦中。
在洋口下车后,马上就有大卡车载着我们与行李,沿着富屯溪边的公路急驰。前方传来一阵阵狗吠声,接着欢迎的锣鼓敲了起来。上凤大队干部将我们带到大队部搁楼上,男生与女生各一间,地板上铺着稻草,我们全部睡在地铺上。紧接着开始了几天的政治学习与活动,再后来,就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大队与小队去。
在我记忆中,最不能忘却的,是当时分配到富屯溪对岸、铁路边的潘坊大队的知青们。对比起来,那里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公路,去县城、去公社都只能靠双脚,要坐车、要收寄邮件就要靠小木船过渡到我们这边来。在他们去潘坊的那天清晨,浓雾迷漫在富屯溪上,凛冽的山风卷着地上的枯叶,天气异常寒冷,我们留在上凤的知青去送别他们。只一夜时间,男生头上的青丝全部剃光了,光秃秃的泛着青光。是削发明志亦或是出家?我不知道。现场气氛十分压抑。渡船靠岸了,搬上行李,人也上船了,那种悲壮的神情,充满“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走的与送的均无语,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渡船渐渐融入雾中,富屯溪上传来歌声: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寒风吹干了我的眼泪,却吹疼了我的心,这一幕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深藏在我的心里。四十余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么难以忘怀,那泛着青光的头皮,那悲壮的歌声,那十几颗年青的心……
上凤第一生产队本地人叫“伏(ku)州”,我们6男9女“插友”在这无福而有苦的小山村安顿下来,开始漫长的插队生活。
下乡的第一关是煮饭。我们的厨房是村民用竹蔑扎成的,到处都是窟窿,寒风肆无忌惮地在里面穿梭。中间摆一张摇摇晃晃的旧圆桌,还有几张旧竹椅,一坐下就吱吱嘎嘎响,坐不到椅子的就站着吃饭。那时吃饭很简单,粮食按工分发,菜靠自己种,经常无油无菜,就搁些盐巴调饭吃。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饭量本就大,但因为粮食有限制,不能多吃,每天都处于饥饿之中。
厨房里用砖和泥巴砌着两个大灶,上面支两口大铁锅,前面一个煮饭,后面一个煮猪食。在那里,每家每户都要养猪,杀猪要队里统一安排,逢年过节或农忙时,才可杀一头猪,全村按户分肉,那时才可有些油水滋润一下我们干瘪的肠胃。
大灶边堆着一堆半干半湿的木头,那是我们去很远的山上砍柴挑下来的。我们村在马路边,烧火的木柴很缺,每次砍柴都要花大半天时间,才可挑回一点,那时我们最害怕去砍柴了。
知青队长按名单写张表贴在竹墙上,按照名字顺序,每天一个轮流煮饭。轮到我时,我提前一夜就开始准备,找了很多纸张、细木条、松枝,整夜不敢睡着,怕早上起不来。第二天房东家的大公鸡还未打鸣,我就起床,在黑暗中到了厨房。按村民教我的,先架上松枝,然后卷团纸点着,塞进松枝下面。很快,松枝霹霹啪啪响着烧着了,我把细木条加入,火烧得更大了,我赶紧架入大木头,可是随着一阵阵浓烟冒出,火渐渐小了。我赶紧又把纸塞进,所有的纸都烧光了,火不仅没着,反而灭了,一股股烟从灶口涌出,呛得我直咳嗽。天渐渐亮了,我更着急了,越急越没办法,怎么才能让大木头烧着呢?烟呛得我哗哗流着泪,我加紧用吹火筒不停地吹着。正在这时,我们称为“管家”的大姐起床了,我一见到她,就象看见了救兵。她边安慰我边帮我,很快,火苗又蹿出来,火着了。一大锅饭还夹生的,出工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赶紧三口两口划拉完碗里半生不熟的稀饭,望着满脸黑一块白一块的我,没有一个人责备我,默默地扛着锄头出工去了。
每天煮饭的人都要去江里挑水,十几个人一天的用水量很大,去江边没有路,又陡又滑,特别是下雨天,就更难走了。我个子小体弱,一次只能挑小半桶,下雨天时还经常滑倒滚一身泥巴,有几次居然还把木桶摔散了。
山里的杜鹃花开了,红的白的紫的,山风吹过,带来阵阵幽幽的香味,不由自主地我又想起了龙山老屋,父亲亲手种的杜鹃是否开花了?
每天晚饭后,从男知青房中就会传出一阵阵经他们改编过的歌声:
“我的家在福州……
一.二四,一.二四,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告别那衰老的爹娘,
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见到我那亲爱的爹娘?”
如泣如诉的歌声,传到了女知青的屋里。让我们这些思念家乡、想念父母的女知青,一个个听得泪水汪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重劳动,耙田、插秧、施肥、耙草,春耕、夏收、夏种、秋收、秋种,面朝泥土背朝天。我们的衣服辍满补丁,我们的娇嫩肌肤变得粗糙,我们的双脚粘满泥巴,我们的外表像农民,可是,我们的思想呢?
那一天,从男知青房中传出一首新的歌,那么沉重、那么缓慢,催人泪下: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名为“南京知青之歌”。再后来,凡是有知青的地方就有人唱这首歌。这首歌伴随着我们度过漫长的知青岁月。
我的大姐与三妹一起在大干公社罗坊大队插队。大姐从小聪明、勤奋、好学,在福州三中念书时,数学成绩特别好。父亲经常感概地说,见过许多好学的学生,她是最勤奋的一个。读高二了,只差一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在大姐加倍努力读书时,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从此彻底改变了大姐的命运;同全国400多万“老三届”一样,大姐经历了人生最迷茫、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她含着热泪收藏好珍爱的书本,因为她坚定地相信,这些书以后总有一天会用得着。在插队的日子里,她样样农活都干过,在痛苦的煎熬中,盼来了招工的机会,虽然只是建设兵团农业师,但她还是义无返顾的去那里养猪。后来农业师撤销了,她去了龙岩特钢厂工作。
“文革”发起时,我的三妹刚刚迈进中学的大门,上山下乡时,她刚满十五岁。按照工龄计算,是个名符其实的“童工”。但在那疯狂的年代,她只能毫无选择的打起背包,跟随大姐和我一起插队去了。在劳动中,她拼命用汗水努力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可是因为年龄小,又没门路,每次招工都没份。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留下的人越来越少,知青点里冷冷清清的,三妹在孤寂的大山深处艰难的度着日子。
自从大姐去建设兵团养猪后,我去看过几次三妹。从我插队的地方步行10余里到县城,坐火车到浦上,然后沿铁轨步行,再转乡村的泥土小路,大清早出发,到达三妹那里,太阳都快下山了。记得有一次去看三妹,半路上下起了雨,我没带雨伞,天气又冷,只见那雨细细密密的,如烟似雾,笼罩在寂静的山间小路上,我又冷又怕,好不容易走到三妹住的村子,全身都湿透了。三妹还没收工回来,我到田里去找她,只见三妹头戴竹笠,身披蓑衣,弯着腰,卷着裤腿,在田里耙草,几只大蚂蟥叮在她腿上吸血,吸饱了血,身子涨的有小姆指大,我吓得大叫,可是蚂蟥吸得很紧,掉不下来,等吸饱血才自动掉下来。那时,我脸上都是水,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记得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眼泪,咸咸的、涩涩的……
后来,三妹是最后一个离开知青点,招工到南平纺织厂。
岁月是无情的,活着的人记忆或还如昨,可两鬓早已染霜;夭逝者遗留的浅丘,荒草萋萋木已成拱……人的生命总有尽头。我希望一代代亲历者,能在有生之年、不畏难辛,搜集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让它轻易湮灭,而是把它留在现实留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让历史的天空不再布满阴霾,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