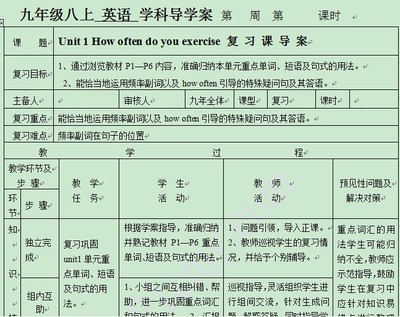浅谈对“文以载道”的理解
文以载道最早见于周敦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这样可见周敦颐最早提出这一观念。对道的说法理解种种,我认为这一成语真正含义先要弄清楚字面意思,载:装载,引伸为阐明;道:道理,泛指思想。指文章是为了说明思想道理的其实“文以载道”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
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实即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道”,究竟是什么?其实从荀子的“文以明道”到现在的“文以载道”,道”的内涵与外延都因时或人而改变的。在本文中“道”的释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那种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意思。换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人类良心,社会责任感。
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文学观念偏于文学的教化目的。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其实“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最早儒家的“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说”中,便已滥觞有这种思想。以后,到了唐代时的韩愈、柳宗元更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说。但“文以载道”一词的出现是在北宋时周敦颐的《通书·文辞》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此后,“文以载道”作为历代正统文学观念,牢固地占据了国人的心灵。
“道”究竟是什么?今人泛指思想体系、规律目的等。而古人之言“道”,各家的内涵并不相同。大多是指儒家之道,指经国之方略大道。“文以载道”理论的提出,往往都带有反形式主义、维护政治统治等色彩。而且就史实看,刘勰之前的理论批评,尚能辩证地看待文与道之关系,唐以后,逐渐向“载道”倾斜。一方面,古人反对为文而文,反对言之无物,讲求内容与形式、人品与文品、道德与文章的完美结合,要求社会的人们要有的责任感、道义心。这方面,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进而成为精髓。但另一方面,在反形式主义的同时,人们往往矫枉而过正,不适当地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夸大了其功利作用。文章当“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经纬天地”、“救治人弊”等等,都是中国文人烂熟于心的古训。文学作为作家精神的产物,审美怡悦、消遣娱乐、熏染性情、陶冶情操、拓宽视野是重要的功能,但教育引导之功利作用确实不可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作用。
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成了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途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利禄,功名利禄也造就了知识分子的依附意识。这种在王权政治、科举制度下滋生的依附意识,使历代文人大都心甘情愿地“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并在思想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地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政治统治服务。历代文人之所以如此地夸大文学的作用,与当时落后的农业经济也有关系。今天在商品经济和各种传播媒介比较发达的中国,人们虽不会忽视文学,贬低文学,但也就会以比较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可是在过去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介尚未出现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赖以传道的工具只有“文”(包括文章、诗歌、戏曲),于是,中国历代文人近乎失衡地重视文学,夸大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功利作用,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今天要写好文章,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天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今天随着媒体的增多,传播思想的渠道显然增加,但即使在今天如此发达的社会,文学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照样传递的是政党的思想,传递的是人民的声音。在教育这块土地上,我们的职责自然仍要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的学生----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教育学生,不仅要重视其文本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我们今天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民族的责任,个人的责任,从小就要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人应该担当的责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儒家的思想有着合理的内核,有他的精髓。我们也应该像古人学习,要有经世之才,更要有儒家那种敢于担当天下的责任和勇气,勇挑社会责任,应该以“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去教导学生,去感召学生。
文以载道,作为我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长久以来发挥了传播真善美、针砭假丑恶的功能,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发展中功不可没。近现代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得到有理想、有责任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用文学艺术的形式鼓与呼,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家艺术家自觉发扬文以载道的传统,唤起人们关注现实、思考社会、展望未来,使文学艺术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时代先锋的作用;它不断挖掘反映现实、人生的深度,不断提高表现社会、精神的高度,为塑造健康人格、鼓舞大众精神、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可见,“文以载道”的文学艺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广的。
文以载道的理念强调文学艺术的目的、功能、方向,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性、社会性、导向性。但它和文学艺术所追求的艺术性并非矛盾,而是一致的。优秀经典之作,也往往都是“载道”之作;而“道”也需要完美的“文”来承载。在这里,“文”使“道”彰,“道”使“文”传,“文”与“道”做到了完美统一。与之相反的是,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近现代文学艺术思潮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以便文学艺术获得自由的、独立的地位,从而复归文学艺术本位,成为纯粹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这样的思潮对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样的文学艺术观念只能是一种理想或幻想。文学艺术家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能没有思想情感;作为表现人的生活和精神的文学艺术,不能不表现思想情感;而思想情感又不可能没有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艺术又怎能成为完全非功利性的文学艺术呢!实际上,文学艺术不可能离开“道”、也不可能不“载道”;文学艺术如果离开了“道”,就只剩下一套形式的空壳,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怎能成为纯粹的、真正的文学艺术呢?对于文学家艺术家来说,不是要不要“文以载道”的问题,而是如何“载道”和“载”什么“道”的问题。在这方面就显示出文学家艺术家的智慧和追求,同时也将决定文学艺术作品的境界和生命。如果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讲,“文不载道”,也将“行之不远”。
文以载道正是文学家艺术家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的体现和实现。文学家艺术家也是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理应承担起一份社会的责任。那么,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创作“载道”的文学艺术作品。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追求美好人生的愿望,能敏锐地把握生活的本真,具有道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的本事;他既是在说自己的心事,又是在替他人张目;即便是描写丑恶,他的胸中也抱有美善;即便是批判,也是因为他怀有理想。他的创作冲动,就来源于这种古道热肠,来源于一腔热忱,来源于大我、超我的要求;一句话,他能够通过感性的形式来表现普遍抽象的“道”。对于严肃的、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来说,文学艺术已经和他融为一体,成为他的第二生命。这样,文学艺术就不是用来“玩”的,而是文学家艺术家生命的外化,寄托着他的思想、情感和向往。同样,对他来说,文学艺术也不是那么好“玩”的,而是呕心沥血、赋予美好形式、塑造鲜活生命的创造物。因此才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其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往往能自觉地实现“文”与“道”的统一,不断探索、创新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不断开掘生活、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思想、精神的高度和精度,用真善美来感染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起到灵魂工程师的作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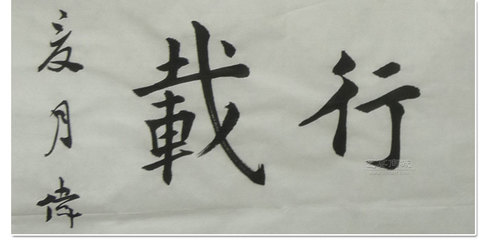
事实上,文以载道的理念并未妨碍、压抑文学艺术的发展,因为文以载道是一个具有极大开放性的命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广义来说,它所要求的就是要用新颖完美的形式来表现真善美的内容。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无边界,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表现自我,强调表现人性。这些观点应当说都有其合理有效的一面,但如果在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表现自我、强调表现人性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文学艺术的自觉追求和约束,这样的创作将很难取得应有的成效,因为这样的创作没有考虑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以为个体的便是社会的、独特的便是公共的;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是难以表现具有普遍价值之“道”的。因此,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以载道”应当是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呈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东西,即“道”。这里的“道”,当然不应是狭隘的一己之道,也不是束缚人性、压抑科学的腐朽低俗之道,更不是歪门邪道,而是真善美之道。对于“道”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表现,有利于提升文学艺术的境界。文学艺术作品因为有了真实科学的“道”,其表现生命、揭示生活的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其感染人、塑造人的能力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创作是“码字”、文学家是“码字工”的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这种说法的立意如果只是在于打破文学家、文学创作的神秘性、高贵性,特别是将文学家从各种条条框框下解脱出来,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这种说法的目的只是在替放弃社会责任、不顾社会影响的创作寻找理由,那么它就不利于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易经》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没有高远的追求,没有仰望星空的敬意,而是仅仅满足于挣钱糊口,仅仅满足于娱乐宣泄,恐怕难以创作出流传久远的精品杰作。
现在还有一种娱乐的文学艺术。在一些人眼里,这样的文学艺术似乎是无功利的文学艺术,体现了文学艺术的解放与人性的自由,体现了所谓“游戏”的精神。这种文学艺术的极端是“娱乐至死”的文学艺术。这样的文学艺术其实已沦为娱乐的工具。娱乐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的一项重要功能。没有娱乐性,文学艺术就不是文学艺术;但是,单有娱乐性,文学艺术也不是文学艺术。现在一些人片面追求娱乐性,片面追求刺激、“笑果”,用各种离奇、惊悚、血腥、色情、感官、欲望等等的东西来吸引读者、观众。这种“文学艺术”的流行不仅遮蔽了有品位、有思想的文学艺术,而且用“娱乐至死”取代“寓教于乐”,消解崇高,嘲讽善美,让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无益于甚至有害于人们身心的健康和谐。这样的“文学艺术”很难说是有理想、讲境界、负责任的文学艺术。
其实,“文以载道”与创作自由并不矛盾;它反而要求文学家艺术家能够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文学艺术的创造是要求对生活、对现实有所超越的。没有超越的文学家艺术家是短视的;没有超越的文学艺术是平庸的。正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如何超越呢?除了创作时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外,还要用一定的眼光、一定的高度来审视生活;同时,还要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对文学艺术一往情深,能够排除非文学艺术因素的干扰。现在一些文学家艺术家把名利看得很重,把“载道”看得很轻,一旦成名就再也无法超越,为名所累、为利所系,不能开展独立的、自由的、认真的创作活动。这种情况对于文学家艺术家本人来说是个悲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个损失;因为他的才华、他的精力、他的生命,都消耗在没有文学艺术价值、没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中,消耗在一时之作、应景之作的炮制中。而有追求、有责任的文学家艺术家则往往能够潜心艺术、耐住寂寞,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进行创作,用生命实践“文以载道”的理念。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往往能够取得较高的成就。由此可见,“文以载道”与文学艺术本身并非对立的关系,相反,还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提高。
总之,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有“文以载道”的自觉,担当起“以文化人”的崇高责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王文革)
中国古代文学家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这种传统被表述为“文以载道”或者是“文以贯道”,不但成为历史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这也许就是我对“文以载道”的思考,韩愈的声音不时回荡在我的耳边,古代的先贤们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学子们殷殷的目光,让我看到了未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