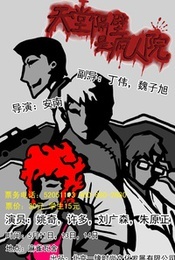昨天再次陪闺蜜去看医生,原本抱着个大大的希望,觉着市级甲等精神病院的心理科医生不比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一定医术盖世,药到病除,能医好我闺蜜的心病。却不料一盆冷水下来,我一身的冰凉。
在候诊室坐了将近半小时的冷板凳后,我如愿见到了第四军医大出身的主治医师,这里的王牌。刚一落座,那厮的肉脸就习惯性地团成一派和谐状,眯着眼睛嘘寒问暖地询问我年龄学历。本来就抑郁的闺蜜顿时表情更显阴沉。弄清楚状况后,那前辈很快转移大方向,一本正经地开始了民警讯案般地问答。在弄清基本情况之后,我一脸兴奋地等待医生的定论。结果,那胖子顿了顿,很犹豫地开口说,“按你现在的状况,应该属于…一种认知障碍,嗯,有关身体认知方面的…障碍,体型…障碍?”——“体向障碍?!”一旁着急的我不禁插嘴道。“对!体向障碍。是一种认知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balabala…”看着医生开始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地演说,我内心热乎乎的小脏器发出“喀吧喀吧”的脆响,碎了一地。
在那套用各种专业术语搭建起来的华丽演讲完美谢幕后,医生从容地端起水润了润嘴巴,仿佛等待病患们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甚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但结果是,除了我的一声叹息外,其余的人都没找到刚才那段话的重点在哪儿,于是纷纷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去了。。。。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的胖叔叔一脸的便秘,开了张单子没好气地打发同学做人格测试去了。
接过费用单据后,我呆了。一项“明尼苏达性格量表”就要140块大洋,还是自付费,结果分析费还要20块。我了个擦,简直是抢劫啊!再看看那个所谓的“心理CT”室,我再一次石化了。两排显示器,一个护士坐在前面负责开机和打印结果——不就是个机房嘛。擦。
两个小时后,同学被568道题折磨得面容憔悴,拿着报告单挪向诊室。又见到那个胖医生了,依然笑容可掬。结果报告单后,皱着眉头看了一会,然后一脸轻松地说,“我给你开药吧!”说着抓过处方单就往上写。尽管同学一脸的不情愿,还是被那胖子的气势征服了。依然是抗抑郁药,依然是做心理咨询,同学依然痛苦。
其实,那个医生只是中国众多心理学工作者的缩影。
面对人流如织的精神科室,面对形形色色渴望得到解救的人们彷徨的表情,我这个正在茁壮成长的心理学接班人,满心愧疚。在陆续接触了变态老师、实习单位的各位精神病医师以及天津的两位“王牌”心理医师后,我慢慢认识到,即使我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理论,对心理学各种流派的观念烂熟于心,对各种统计、测量的检验方法应用自如,这些对于一个真正需要救赎的人来讲,又有什么用呢?
就像那个笑容可掬的胖叔叔,对于量表的测量学理论背诵得毫无遗漏,对“信效度”的解释,我挑不出任何差错,尽管那些并不是病人及其家属能听懂的——也不是她们想听的。但对于同学的病情,胖叔叔的解释就明显很是牵强附会了。甚至都动用了“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来游说闺蜜。一向锱铢必较的闺蜜自然不买账。一句“自欺欺人”就把医生回敬得无言以对。权威感被严重伤害而又一时无法扳回的情况下,胖叔叔决定撕破笑容可掬的教父招牌,重重地丢下手里的处方单,小眼睛瞟向显示屏,直截了当问了句“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药还开吗?!”一副“逐客”的架势,弄得场面非常紧张。同学家长不愿抛弃那根胖胖的稻草,赔笑道:“开吧,开吧!都听您的!”胖叔叔那才拾起笑眯眯的表情,一脸平易近人地开了药方,嘱咐同学如何服药。然后一行人装作皆大欢喜状走了。
一路上我都在反思,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把焦距拉得近些,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我,要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是一如既往地朝着自己的职业理想坚定地迈进,还是像那位胖叔叔,尽管在医科大学的是内科,但无奈被分到心理科,所以考了心理学的研究生,然后坐到了如今主治医师的位置,一周有半天坐诊时间,忽悠忽悠病人,然后参加个商业性的咨询机构,大把赚外快,有时间上文库,东拉西扯攒篇论文,接着进阶,评职称?!
如果是坚持理想,也许我连最基本的面包都吃不饱,可如果选择后者,无疑财源滚滚,当然,前提是我有“魄力”踏平一切渲染着铜臭的门槛。。。。
虽然青春期激素分泌旺盛的我,现在还不忍心妥协于一板一眼的现实,不屑于跟污浊的社会沆瀣一气,但纵使我有冲破黑暗的勇气,可仅凭我一个小女子柔弱的身躯,又能低档多少风雨呢?
敬爱的弗洛伊德祖师爷,如果您在这个时代,还会继续以前的路吗?
请告诉我,我要怎么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