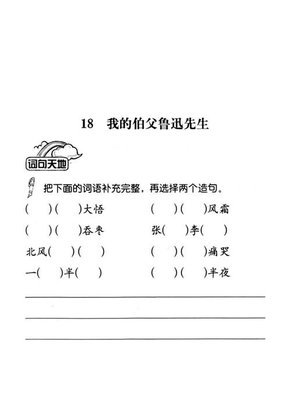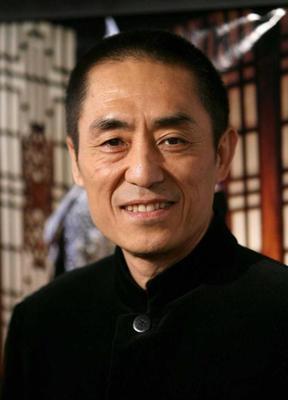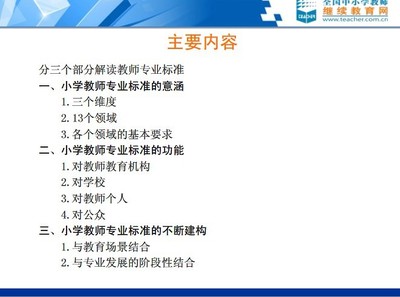《陈奂生上城》再解读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张 琼
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写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小说,其主人翁陈奂生形象的塑造仍让人觉得有不少可回味之处。究其原因,就在于陈奂生其人的命运反映了特定时代里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其人的性格毫无造作,朴素而又真实可信。陈奂生形象的塑造,无疑是作家高晓声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民群像塑造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自小说发表后近30年来对陈奂生形象的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多从其身上的奴性因素、与“阿Q”形象之对比以及探究作品的主题意蕴等角度人手。已发表的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如赵小明的《论阿Q与陈奂生》(《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杨建祥的《<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科技信息》2008年第9期),张继涛的《浅谈陈奂生形象的奴性因素》(《科教文汇》2008年第6期),张丽军的《农民陈奂生的精神溯源与当代启示》(《语文教育》2005年第7期),石立干的《旨在塑造更美丽的灵魂——<陈奂生上城>主题新探》(《名作欣赏》2003年第l2期)等。本文试图将陈奂生形象还原至20多年前的典型环境中去,期待在典型环境的观照下,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陈奂生这个被研究者认为背负了国民性思想包袱的中国农民典型给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增添了怎样新的意义。
文学形象(包括人物、场景、氛围)的典型性的高低,历来是衡量作品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一条重要标准。别林斯基说:“典型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艺术性在于反映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何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充分地表现出来。”(《别林斯基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卷 第26页)
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对于典型人物来说,是指“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环境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典型环境是指作品中人物所生活,所活动的那个具体环境,同时也指支配人物行动和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的、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它是具体的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家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相依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此子宜置丘壑中”(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的观点,它揭示了典型人物的塑造不能脱离典型环境,人物和环境必须相互渗透、和谐统一。这也是艺术典型论的基本内核之一,特别值得重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是19世纪以来基本左右中国政治高层和大众共同审美习惯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因而一度曾是我国大多数作家进行创作的行动准则。
描写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形象是高晓声文学创作的全部内容和主题,也是他文学生命的唯一重要的展现方式。农村有如一眼老井、一片厚土,它积淀了由古而今历史长河里丰富的文化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就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高晓声笔下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之所以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活灵活现,就是因为作家能够把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进行建构。作者通过塑造这些文学形象,以史家的姿态,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画面,从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揭示出农村政策的改变带来农民命运的变化。作者从农民最基本的衣、食、住等问题展开情节,展示了农民多年来坎坷、复杂的命运史,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一代农民的奋斗和痛苦、希望和失望。农民的生活是复杂的,决定了农民的性格也是复杂的,如何去表现好这些农民复杂的个性及典型性,则是高晓声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文学是人学,又不仅仅是人学,而应该把握人的生活和灵魂的一种历史审美学。”(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对人的描写、人性的挖掘、灵魂的剖析,就成为艺术表现的聚焦。作者以农民生活的典型社会环境作为切入点,既描写了农民具有的智慧性和创造性的正面,也不放过他们具有的奴性和惰性的负面。
要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所呈现出来的性格心理,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便是把他们放置到当代农村急剧变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去加以考察,高晓声描写农民的小说正是发挥了“系列小说”这一“纵深”优势,把陈奂生放置到这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去,让其命运的不同遭遇和性格的多重侧面在变动中得以充分地展示。在小说《陈奂生上城》里,作家把陈奂生调动起来,让他离开他所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到他所不太熟悉的城市,“悠”出了一段奇遇,演出了一场活剧。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文本的解读上去。
高晓声在小说中给我们建构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典型环境,即改革的启幕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普遍还没有来得及在社会转型中完成漂亮的转身,陈奂生们茫然、尴尬、坚定、期待的表情被作家精准地记录了下来。陈奂生普通平凡、勤俭朴实、吃苦耐劳,具有中国农民传统的优秀品格。然而,陈奂生又处在文革刚刚结束,新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的转折时间段,他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新的生活带给他幸福,带给他生活上的丰裕,因而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此时的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可他的身上同时也带有着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滑稽可笑的缺点,这些缺点同样也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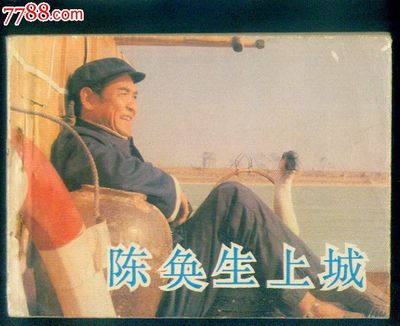
小说写陈奂生在解除了口粮之忧后,开始萌动了精神上的追求,渴望改变自己过去因贫穷和口讷而落于自卑的精神状况。高晓声在小说中利用农村寻常的“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的典型场景,给我们生动地刻画出陈奂生“只听不说”的自卑形象。陈奂生“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话可说。”可以看出,在农村茶余饭后人人争相展现个人见识的时刻,陈奂生是极其没有底气的,这与他之前头上所戴的“漏斗户”的帽子有很大关系。文化大革命以来,陈奂生“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在物质生活极端贫瘠的生活状态下,他不可能去关注所谓“精神生活”层面的追求。上城之前语言的局限使得他在村中的无数次话语权分配中一直落败,以至于“就像没有他这个人”。陈奂生无疑是笨口拙舌的,在他的语言世界和心阈视界中,只有些别人都知道甚至先于他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当专家提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时,他表现出对一个说书人的佩服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晓声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安排陈奂生由上城前的“想说无可说”,到上城后“身份显著提高了”“从此一直很神气”的关于“说话”的首尾照应,极好地凸显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民在全新生活环境的改变下苍白的精神底色。这里,陈奂生的精神提升,并不是借助切实的努力,真实地改善了自己的精神面貌;相反,也和阿Q一样都带有虚妄的成分,只是通过一种偶然的生活巧遇,来牵强附会地借机夸耀,其“自欺欺人”之处显而易见!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合理的“善”的欲求,往往会因为追求主体素质的局限,在实现过程中逸出正常的轨道。这种寻常百姓的交际现实,陈奂生们对于自我尊严的找寻,正是作家在典型环境中塑造起来的典型人物形象,陈奂生在上城“悠”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从未离开过的生活原点的现实。
高晓声在小说中着笔较多的另一处是放在了陈奂生对于数字的敏感上。小说中多次写了陈奂生的算账。如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后,明白了是县委书记吴楚把自己送进招待所,便感激万分,回想和吴书记的交情,“平生只有一次”,吴书记在大队蹲点,去他家体验“漏斗户主”生活改善的程度,“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再如小说中写到陈奂生付了五元住宿费后回到房间“又肉痛起来”,五元钱之所以能让陈奂生捶胸顿足,是因为困了七八个钟头却顶他“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还够买两顶帽子。“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这样一种算账法,这样一种换算方式,对于揭示陈奂生的性格特征,对于刻画陈奂生的形象,有着显著的功效。货币对于陈奂生们来说,已由改革开放前符号化的表象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但其对农民的长期打压已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道暗影,在陈奂生们看来,经济损失是自己遭受的最大损失。他可以忍受大姑娘在洞察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之后对他的怠慢和瞧不起,但却久久不能对自己如此不划算的经济损失释怀。高晓声在这里给我们刻画出来的斤斤计较,不是为了凸显陈奂生们狭隘的小农意识,而是为了加深陈奂生的辛酸履历及其苦海人生的深度背景,也证明在社会变革初期农民真正的富裕还并未来到。那种“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并不就是真正的富裕。高晓声将陈奂生放在城市中、招待所里、商场里并不是为了出他的洋相,让他把自己的局促和露怯晾晒在世人的面前,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关注到农民的心灵深处,关注在城市作为陌生地的强势文化威压下的农民怎样才能摆脱精神苍白,摆脱与社会的“格格不入”。
马克思曾经说过:“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细细品味陈奂生这个典型形象的意义,我们尤其能体会出这段话的深刻含义。高晓声在改革初期这个典型环境观照下塑造出来的陈奂生形象,让我们更关注人的本体地位的回归。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陈奂生和他的弟兄们已逐步摆脱贫困,生存权已得到了保障。但是仅仅从经济上让他们得到解放是不够的,像马克思所说的“政治”上的“实在的、实际的解放”,应该包括唤醒他们的人权意识。精神和思想的贫困是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为可怕的事情。要真正让富裕起来的陈奂生们真正解脱精神和思想的贫困,在我们眼下,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
高晓声是一位目光敏锐的作家,他及时地通过小说形式表现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反映出了新时代给人的新生活。同时,高晓声又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他塑造了一个有着许多优点而又有着十分显著缺点的历史转折初期的陈奂生形象,让读者让社会更多地思考反省,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高晓声《且说陈奂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