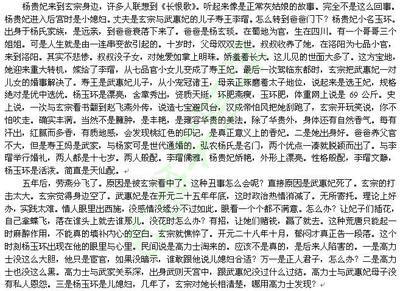本文摘自:《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作者:杨宪益,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9月版
一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了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是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迭在努力把自己融进中国。
二
1938年的英国。
母亲惊住了:刚刚20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
对于身为传教士的母亲来说,女儿戴乃迭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说。
母亲有她的忧虑。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国传教,在那里生儿育女,那里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对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她为女儿的未来而担忧。
“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这样说。此时,她已经在中国有过诸般经历: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文革”期间蒙受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4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出狱后,惟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终于在1979年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难,令她在回忆母亲当年的警告时,心底难免会掠过一阵苦涩。
然而,她镇静,她无悔,她还是充满自信与坚毅。
因为,她爱中国古代文化,她爱所有的中国朋友,她爱她选择的终生伴侣———杨宪益,是他在漫长日子里带给她快乐与温馨。对于她来说,情感与精神上的满足,远远超过一切。为杨宪益,她愿意也能够承受一切。
三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随父母在中国长大,后来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下了。无论走了的,还是留下的,他们未来的发展和命运注定要与中国有关。于是,在历史场景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活跃的身影。仅以美国人为例,便可列出一串人们熟知的名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戴维斯,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罗斯,《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细细搜集,几乎在中国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政治、教育、文化、工业、商业等方面,都不难找到传教士们的后代,那一定会是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也不管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口碑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我们在审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时,他们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对于戴乃迭,她并不习惯于做抛头露面、风光十足的公众人物,只愿意平静地与丈夫呆在一起,专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精神的满足中愉快走着。因为,最终把她和中国联系起来的,是对杨宪益的爱,是对童年的北京生活美好而甜蜜的记忆。
戴乃迭于1919年在北京出生。中国留给童年戴乃迭许多美好记忆。她亲身感受到的快乐,亲眼目睹的丰富色彩,使她从感情上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四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脸色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迭,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戴乃迭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只是在年满21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龄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着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戴乃迭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戴乃迭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五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剧烈的冲击。戴乃迭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叹息。
第二天就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
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有关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迅速被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到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先去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来逮捕他们的。
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有人来把戴乃迭带走。
戴乃迭4年的囚禁生活从此开始,而单人囚禁带来的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
据杨宪益回忆,他们的入狱,主要起因在于早在40年代,他们和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好朋友,来往密切,曾经常一起在江南旅行。20年过去,这段经历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间的锒铛入狱———他们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但是否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动乱的年代,一切都处在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一点在他们的遭遇上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
杨宪益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却无缘相见。
杨宪益惦记着戴乃迭,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么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迭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为安心。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着。他们都在牵挂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虽然牵挂,但他们不曾料到,长子会在他们坐牢期间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
六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4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回家了。
释放回家,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孩子们调回北京。不到三个月,儿子先调了回来,其次就把在东北劳动的小女儿调回来,大女儿稍晚几个月也从沧州正式调回来了。一家终于团圆。但儿子的病情却让他们为之苦恼。最终,儿子在英国自焚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为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下了一首《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着。
相濡以沫将近60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尽管儿子的结局被她的母亲不幸言中,戴乃迭却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