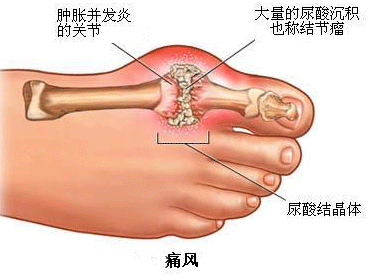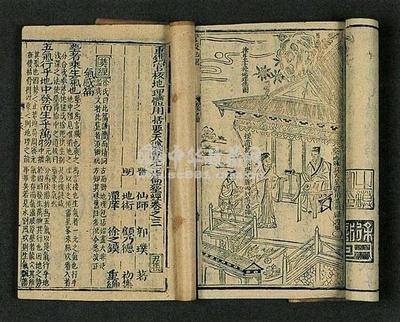一、三眼族群
至今在当初氐人生活过的甘肃南部,依然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比氐人还要古老的上古时代,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三眼的族群。他们除了与我们一样的两个眼睛,在额头上还有一个直立着的眼睛。但是因为气候变化,雨水浸入了那只眼睛,导致这个族群集体生病消亡了。他们认为一些他们在当地偶然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现在我们叫它寺洼文化)就是当年这些立眼人使用过的。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人在成都看到这种立眼人在街上闲逛——氐人的后人为了膜拜三眼神,用刀割开额头,将墨涂在上面,呈眼睛状,等痊愈后,就形成了额头上的“眼睛”。
这些传说借助神话的形态,保留着一些氐族先民的零散原始记忆。事实上,寺洼文化的居民,正是氐人的先祖。这些原始记忆,随着千年的流传,几经改变,最终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点关于它的线索。
在寺洼遗址中,我们发现他们从那时就开始施行火葬的习俗。
当汉族人攻入氐族部落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氐族俘虏们不担心被俘虏,而担心不被火葬,可见火葬观念对氐人的重要意义。作为渊源极近的汉族和氐族,为什么在丧葬上有巨大的区别?我认为答案还是和氐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我们知道如果任由尸体暴露在空气中腐烂,很容易引起瘟疫等疾病的流行。所以各民族都会葬掉尸体。葬礼可以使瘟疫远离人群,又可以寄托生者对死者的感情,于生理和精神卫生上都是人类的一大创举。
掩埋尸体和烧掉尸体,一样可以达成目的。中原大都非常平坦,人最初能生活的地方也大都是被河流冲击形成的平原,土壤层很深,挖一个坑,甚至挖一个深坑都很容易。而在氐人生活的山区,土层和石层之间错综复杂,山地地形更因降雨风化等原因,不断因泥石流、塌方等发生改变,而火葬只需要点一把火就可以,所以寺洼居民自然地选择了火葬。
山区土葬之难,在工具成熟的今天依然可见。我就见过有人在山坡土质较厚的地方建坟,数年后改葬时发现因为土坡呈缓慢下滑的形态,棺木在埋葬地点数米外。而在深山中,近现代山民(汉族)的丧葬习惯也与山体形态不无关系。他们将人葬下后,上面并不像中原坟茔一样用土堆成,而是用当地常见的页岩垒成坟形。坟边种植松树。现在川西北的羌族建筑就是用石头垒成,非常结实,甚至在地震中也有卓越,同时这些羌族山寨上方的树林也严禁砍伐,这样的山寨非常安全坚固,很少会担心因地震和滑坡引起的灾害。回到我们的话题,石堆和树根都对山岭之间坟墓的加固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推断,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氐人选择了火葬。当然,这是我的推断。
实际上氐人也并不全部都是火葬。一般来说,民族风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整齐划一、由各种标志元素组成的。通常一个民族的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别也可能会很大。好比北京人、陕西人、四川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属于汉族,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形形色色氐人的群落,像光谱一样分布在群山的褶皱之间。他们的情况也不例外,有不少氐人部落就是实行土葬,比如略阳氐。略阳氐与汉人居住区相接壤,受汉人影响非常大,身为略阳氐的苻坚和吕光都是土葬。还有一种是分季节轮流使用火葬和土葬,比如白马氐。氐人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处于羌族和汉族之间,同时受着二者的影响。所以在风俗上,也有不同的层次纹理。
火葬的例子是为了说明环境对人的信仰和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上古时代,原始宗教和科学的功用一样,都是用来解释和合理化日常生活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氐人没有文字,除了借助考古研究,关于先祖的探求只能从这些古代传说中看到零星线索。一个被载入了正史的传说,可能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些关于他们源流的东西:《晋书·载记第十二》中提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我们可以先把它当作真事,分析一下。有扈在今天户县的位置,苻家作为氐族大姓,起源于有扈,也就是说,氐族的一部分先族来源于关中。而有扈是典型的华夏部落,与夏部落是不同分支。而“世为西戎酋长”,则进一步说明了从诸夏到氐族之间的传承。退一万步讲,这些都是苻洪瞎编来玩的,被史家所采,苻洪并非有扈苗裔,依然不能否认氐族先与华夏有很深的渊源,然后又被区分为西戎这个传承过程。因为,从有巨大影响力的氐人酋长苻洪和极有判断力的史官都承认这种说法,即使细节存疑,在传承这样的大问题上是不会有疑的。
华夏—西戎—氐,这个传承顺序,当为他们的共同观念和起源记忆。
二、上古灾难的侵袭
氐人作为上古时代的方国,第一次出现是在甲骨文和诗经中。他们形象不那么高大光彩:“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和西方名著《戒指王》里的咕噜先生一样,在书中一登场就是非常可怜的受气包形象,是不敢不服、定时上贡的的商朝附庸。
西周的气候本是温暖的。中原和关中气候宜人,有大象,也有犀牛,一切都很和谐。但是从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800年左右,气候突然发生了恶化。周孝王在位时,长江支流汉水,发生了两次结冰,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异常。而在冰冷侵袭之后,很快又发生了持久的大干旱。这次干旱从公元前九世纪初,延续到八世纪中叶,历经共和、宣王、幽王和平王。在《竹书纪年》和《诗经》上都有大量记载。“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强大的自然灾害侵袭中原和关陇,部族生活极其困苦。作为氐人的临族羌族,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向西北方的青藏高原收缩以追求猎物和牧场的。
在这持久的寒冷和干旱下,狩猎民族想继续留在原地,就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或者北上或者南下继续追逐猎物,或者就地开始农耕。寺洼文化的遗民正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开始向南进一步发展,尝试并适应畜牧、耕作和纺织,以缓和环境的恶化对自身带来的影响。
他们眼看着身边的草木枯萎,猎物也越来越稀少,一些村落可能面临着断绝食物的绝境。打猎这种收益不稳定的事情只好放在一边了,想吃饱的话,就得有新办法。持续的干旱使本不擅长耕种的他们无法在本地迅速开展农业。而往南不远的山区则富有水源,虽然土层不深,也算不上肥沃,因为高大山脉遮蔽阳光的缘故光照也不太好,但是总好过在平原等死。前面说过,寺洼文化分布地区的南面正是群山耸立的秦巴山区。这里冬天和中原气候相仿,夏天则非常凉爽。岷江、嘉陵江、汉江都从这里发源,它们的支流如毛细纤维血管遍布群山之间,春天积雪融化时,还有雪水从山颠流下,这些高山峻岭无疑比平原更能够储藏水分。与渭河平原相比,这里水源无疑非常充足,几乎不用担心干旱的影响。于是一个个部落离开家园,开始逐步向南迁徙。他们最终定居在关陇之间的丘陵和秦巴山区的山地之间,修筑起板屋土墙的房子,开始新生活,而他们与关中的联系则自然而然地大大减少。
迁徙,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很讨厌的事。在远古时代,这些原始部族,数以千计的部落或者村庄,在食物供给日益匮乏的情况下,要从他们熟悉的平原,举家迁徙到布满荆棘、到处都是陡峭悬崖的深山的密林中居住。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这场被迫的迁徙中,多少个部族完全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原始部族有多少会在迁徙与不迁徙的争端中崩溃,有多少人因为不适应环境而死掉,有多少因为饥饿而死掉,山川之间是否曾有原住民,有多少在和原住民的战争中死掉,史书都没有给我们答案。而之前“立眼人”的传说,据推断,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流传的。定居深山中的后裔,把先人想象成已经消亡的立眼人,而“立眼人”则正好是“离年人”的发音。“立眼人”作为一种先族崇拜的异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总之,环境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此过上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当这种生活形态渐渐稳定下来之后,他们演变成为了氐族。在那时候,他们还被中原称做西戎,氐人这个称呼是秦人叫开来的,意思就是“山坡上的人”,而氐人自己,则自称“盍稚”,应当是一种氐语的称谓。氐人通常都会使用两种语言:氐人之间用氐语交流,与汉人交往时他们使用汉语。
他们不知道,在今后,还有更多迁徙,而那些迁徙都和这次不同,许多人为的灾难,伴随着杀戮和强制,比自然更加严酷。
三、氐人所生活的山地
很多时候历史书满篇都是人与人的事情,背景仿佛是空空荡荡的,也并不怎么重要。我们会凭空想象一个王府,或者一个行军帐篷,除此之外,恐怕是一片茫茫虚空。但是对于氐人来说,“氐”就是坡地、山地的意思,氐人,顾名思义,也就是山地居住的山民。故此介绍一下氐人所生活的地方还是有必要的。
氐人所生活的地方,在如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以及四川西北和西部。向西,延伸向古羌族聚集的河湟地区,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甘肃水草丰富,非现在可比。向南则延伸到西南嘉戎一带的少数民族诸国。向东则与汉文明的中心关中平原相连,氐人和汉人之间的交往非常之多,氐人最初的聚集区是以今甘肃南部和陕西西南为中心,向西南和西北延伸的狭长通道,可以看作是夹在汉与羌之间的“夹心”。
如果打开GoogleEarth,我们可以看到,氐人最初所居住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山地。这些山地通常由河水冲刷成各种山沟,如树根一般分布。这里水源充沛,汉江、嘉陵江、白龙江、岷江等都从此发源,而山谷中和山峰的相对高度有时会很高。一般来说,高处约有海拔3000米左右,而一般地区则在海拔1000米左右。这些崇山峻岭之间就是氐人生活的中心,甘肃东南以及陕西西南的地貌。这里山谷间长满了当地人称为“狼牙刺”的带刺灌木,梧桐、杨树、柳树都比较常见。随着海拔的提升,则会有红桦树等高大的木本植物,松柏之类也很常见,到了春天,满山的狼牙刺和地上的草本植物都会开花,氐人产蜜也有史记载。
今天,当地人蓄养动物主要包括山羊、黄牛。前者能爬上人所不至的悬崖峭壁,安全地寻找食物,既耐旱,又耐寒;后者则一般放养在河滩,很好蓄养。氐人在那里经营,到汉代,已经是“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在这样难以通行、荆棘覆盖的地区,行走跋涉都很困难。想游牧恐怕行不通。李白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这地方。谁要是在这种地方搞游牧,那准是要挑战人类和畜类体能极限。氐人以农耕为主,善织布,既畜养牲口,又打猎。这更像汉人,与“以射猎为事”,“以产牧为业”的游牧羌族很不一样。
这些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也就是说他们居住在一种四周筑土墙,竖有支撑柱,再在上面架上松木板的建筑内。现在我们在川西北,依然能见到这种建筑。虽然氐人很早就有王,但是他们的王,也不例外地和平民一样,住在这种房子里。明小说里常有“谁人顶着房子走哩”,这种建筑形式更说明了氐人还做不成游牧民族。
从山区往北,是黄土高原和渭河平原。这里和南面崇山峻岭之间的气候、气温都相差甚大。没有了这些山岭,这些地方在夏天会更炎热。以我的经验,这些地方的少女穿上撩人的短裙的时候,南面山区可能还在穿长衫,甚至一些山顶还有未化的积雪。而在冬天,这里的温度和山区差别不大。
四、定居山中的生活
到达密林之后,氐人会发现这里的猎物甚至比平原还多,并且山脉之间,还不用担心狼群的侵袭,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狼群,仅有的野生动物威胁来自蛇和那些喜怒无常的庞然大物——熊。这里有得是鹿、兔子、野鸡、锦鸡、金丝猴,还有大熊猫。一些氐族部落就以熊猫来进行图腾崇拜。有了大灾难的经验和熊猫们的保佑,氐人大概明白了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经营策略,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多元化经营:从农耕到麻布纺织,从狩猎到畜牧,从加工漆到收集蜂蜜,他们均有产出。
这些特产很快在果腹之外,产生了赢余。氐人又与关中、成都平原的居民进行商贸往来。他们大都在部落中说氐语,而外出则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和汉人交流着财富和资源的同时,也交流着文化。
氐人一部分依附于秦,另一部分在深山的森林之间,“各自有王,由来久矣”。我们从文献中基本看不到关于氐人政体的介绍,只知道氐人自有王侯,各自独立。各种氐族部落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别,现代民族史学家王明珂在对当代羌族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群之间,文化和认同感都相差很大。一个民族不是典范历史上描述的那样,严丝合缝地遵循着书上所描述的那些特点来生活,而是各有不同,像光谱一样分布在山的褶皱之间,有些时候甚至只隔一条河的两个村落,都会彼此认为是不同的民族,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好理解,即使是沟通频繁的现代社会,在一起生活了数千年的汉族,紧紧相邻的两地:北京和天津,它们之间的语言、习俗和心理差别也是很大的。更何况交流闭塞、被夹在汉藏两大强势文化之间的羌族村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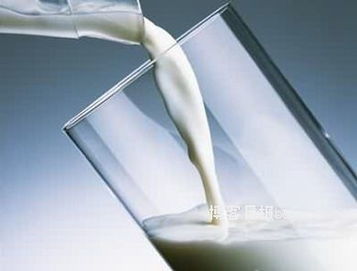
王明珂把它的原因和羌族在汉藏之间的这个境况关联起来,这固然是没错。而实际上地理环境也对这种民族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山和水系把部落隔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同的群体。
秦国受限制于中原争霸,他们只对较少的氐人部落产生了影响。大部分的氐人还是在高山密林之间建立着无数的原始袖珍王国,各自为政。他们中间的酋长和中原一样被称做“王”、“侯”,还有被称做“大”的,即所谓“酋大”。小一些的被叫做“小帅”。这种叫法十分超前,现在网络上一般管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就称做X大,可见网络还是充满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情调啊。
氐人王侯和平民不分贵贱,都住在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板屋土墙的传统房子里,这种房子分三层,上面存东西,下面蓄养牲口,中间住人。而他们的邻居羌人则用毛毡架成毡庐供人居住。氐人在穿着上主张青色和红色,衽露和汉人一样,几百年后,苻坚大举南下的时候,桓冲说:“恐怕我们以后要左衽了。”按说桓冲在桓温北伐的时候,是参加了战斗的,对氐族的了解不可能无知到了这种地步,这话很有可能是写史的人为了营造恐怖气氛自己编出来的。虽然样式上和汉人相同,但是氐人在衣服上还绣有和羌族相仿的各种边纹图案。氐人生产的麻布在汉人中间很有名气,属于当地土特产。
同时,在这片山区里除了氐族部落,还有羌族部落,更多的是汉人的村庄。同时在一些氐人的部落中亦有汉人存在。氐人的姓氏与汉人几乎完全重合,无一复姓,这也证明了氐人与汉人之间的紧密亲缘关系。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先秦与汉人广泛结为联盟的羌族,在姓氏和习俗方面和汉人的差别也非常大。
五、平静的新生
当中原进入东周,列国征战不休的时代,秦人对西境的少数民族领土进行了扩张,羌族在这种形势下猛烈收缩到青藏高原的河湟一带。这时有三个氐人国被秦征服,由此闯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街戎(上邽)、獂戎和翼戎。氐人被称为戎人,羌人被称做戎人,甚至秦人也常被人当作戎人。戎人这种称呼实在说明了古代中原对周边民族缺乏观察。但就这种观念而言,秦人被称做戎人,楚人被称做南蛮,说明了中原诸侯和这些戎蛮之间,虽然有一定的排斥,倒也不是走得太远。
无论是王侯还是酋大,他们的实力都不足以和东方的王国中的任何一个抗衡。高山和它们之间的沟壑,构成了闭塞的环境,它限制了氐人建立广阔疆域的王国和庞大的组织。而东方诸侯基本都建立在广阔的平原上,对他们来说,这些由氐人建立的“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候,他们正在忙着相互征战兼并。最终距离氐人最近的秦国,统一了东方诸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王朝,又在刹那间崩溃,混乱再度侵袭着东方大地。
项羽将刘邦封到了汉中,这里离氐人的居住区就更近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穿越这片山区的古代栈道。它穿越了数个氐人王国,最终到达关中平原。新的王朝建立之后数十年内,国家力量着重在对内部诸侯的压制和对匈奴的战争中。广阔天地之间发生着大的动荡,中原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真正统一,追求集权的中央和想要延续分裂的贵族之间时不时会发生一些零星的战争;在遥远的北方,匈奴人从草原众多民族中崛起,成为了一方霸主;西北方的乌孙人在匈奴人的扶植下蠢蠢欲动,它的野心是摆脱匈奴,成为和匈奴并列的草原强国;月氏人在匈奴人的打击下西迁,赶走了大夏人,建立新的国家;大夏人也被迫西迁,他们征服了亚历山大大帝在亚洲所遗留的的巴克特里亚;而氐人则在整个东方的民族纷扰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但这不过是风暴前的寂静罢了。不久,随着汉朝的日渐强大,汉武帝的拓边政策席卷了许多周边民族,汉帝国象一只东方巨兽,以无可阻挡的强大力量,碾碎它视野内的一切小政权,夜郎们无不争先恐后献出贡品以示臣服,他们诚惶诚恐,生怕得罪天朝,降下天兵。同时,汉人学者的视野,同样深入到了这些渺小的族群中间,其中就包括有这些在深山中星罗棋布的氐人部落国。
六、天朝子民
西汉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夜郎,作为西南最大国的夜郎拜倒在天朝的脚下,西南夷全部被这场政治风暴所震撼。不久,汉帝国作为奖赏,将夜郎侯封为夜郎王,四方部落感受到了汉朝的雷霆之力,又看到了依附天朝的巨大好处,于是争相内附。汉武帝将这些土地划分了新的行政区域,在蛮夷的聚集地设置“道”为其行政单位。
混杂在这些部落中,绝大多数氐族人选择了内附。大部分的氐人被划分到了武都郡,而实际上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郡县制和酋长制的双重制度让氐人很难受,平民受到双重统治,而酋长们则失去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于是,大批的氐人脱离了郡县统治,逃往更远更深的山区。
元朔四年至六年,汉武帝命张骞派人以四路西行,寻找大夏。大夏即吐火罗,在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它是西域以西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如果找到了大夏并建立起合作的关系,那大概就能对匈奴人形成包围之势。
但是没想到不知什么原因,四路人马全都受到了土著人的围攻。其中北路就是受氐人所阻。天朝对这种情况十分震怒,派郭昌、卫广出兵征服氐人,设立武都郡。关于这次战斗,史书上基本没有什么记载。但是过了不久,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再次暴动。弱小的抵抗很快就被征讨镇压下去,为了分化他们,武帝命令将一些部落远徙至酒泉郡。
昭帝时,氐人又发生了几次暴动,这些没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暴动被轻易粉碎。整个西汉时期,氐人处于不断的小规模暴动中。
与此同时,一些氐人在武都郡设立时受到了排挤,迁徙到了略阳郡,回到了渭河平原。这一支氐人在日后随着与汉人的广泛接触,表现得不像他们的同胞那样自闭,而是更有计谋和想法,他们在几百年后将大放异彩,他们的佼佼者将在中原称帝,昙花一现地统治着整个中国北方。
东汉初年,氐人摇摆于益州和凉州的军阀之间。马援制止了即将面对氐人豪强们的强力统治,并且在光武帝刘秀的支持下提出了一笔政治交易。汉政权将以册封的形式承认氐人酋长们的地方权力,而氐人部族则转而支持刘秀政权,并纳入它。这一交易的直接结果是凉州军阀的平息,也就是隗嚣的倒台。氐人酋长齐钟留甚至与天朝联手,剿灭隗嚣的残余势力。在安帝永初三年,氐人还曾代表帝国讨伐李贵。
氐人,作为紧邻关中的部族,与华夏血缘、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天朝上国的能量,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这样和天朝子民保持着大面积的错杂相居。帝国的一举一动,都会投射到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民族与汉族的中央那么近,他们花几天的时间,就能到达汉族的中心——关中地区。他们和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不同,有丰富的特产,有富足的粮食产量,有吃苦耐劳的山地战士。氐人在两汉时期所有的暴动都是针对一些地方事件的暴乱,与其他匈奴、羌人不同,他们很容易平抚。只要帝国承认他们的地位,他们甚至愿为帝国前驱,扫除边患。他们与天朝关系紧密,从土特产的销路到部落之间的关系,无不受到汉朝的影响。这使得日后他们将成为第一个在帝国内部获得和汉人一样政治地位的民族,而与汉族的紧密关系,也使得在日后的大混乱中,他们常常做出与其他边缘民族所不同的抉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