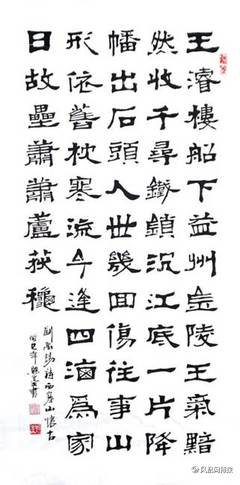我和王朔,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可以无限延长,但是永远不会相交。
——金庸
一
金庸与王朔,【一】都用汉字汉语写小说,【二】是当世最具幽默感的两位小说家。
此外,二人再无相似处。
更多情况下是截然相反、天然敌对的。
金庸视王朔《我看金庸》为“对自己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明显表露出几分困惑迷茫:自己与王朔既无“个人恩怨”,还曾对王朔做出过正面评价。王朔这厮为何欺上门来,偏要跟自己过不去?
金、王之争,自然与“个人恩怨”无关。然而,他金庸所珍重珍视的一切,正是人王朔反感反对的。
王朔在祖父一代,还生活在辽宁,满族。金庸家族几百年生活在浙江海宁,汉族。东北与江南不协调,满、汉现在“全席”,当年也不是没有对立。
50-80年代,王朔长养于北京城军队大院中,金庸则食息于香港渣甸山自己的豪华别墅。把军队大院与大资本家的别墅联想到一起,是否已足以给人以紧张感?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既是拥有几千亩耕地的大地主,又是(尽管金庸认为他对人太厚道做生意不精明)资本家,在王朔的大院父辈们眼中,正是双料的反动,查枢卿土改殒命,正为此故。
遥想燕京当年,分明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本部和策源地。香港呢?纯然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前哨站;
北京曾经是“计划经济”的总规划地,香港则是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大都会,十几年来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王朔自称“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只不知:他的祖父一代呢?王朔父母参加的,那可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啊!
王朔爹妈考第一名,这样“优秀人种配的”王朔本人谅必成绩优异,谦虚不说罢了。1983年,金庸在台湾参加一次访谈,说:“我从小看武侠小说成绩还是很好,初中高中大学甚至毕业都是考第一名。”(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29页)太不谦虚了!
在一堆小知识分子中,王朔的父母,也算鹤立鸡群了。然而,他们的人文素养,怕是不能与真正文化世家的子弟相比罢。
海宁查氏,即被康熙称作“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一时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1924年生于海宁查氏老宅,触手皆是文化,张目即见传统。他的祖父文清公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加同知衔,编过一部《海宁查氏诗钞》,竟有数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竟成为金庸和堂兄弟们的玩具。童年的记忆太深刻,直到1966年,金庸在满世界“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创办《明报月刊》,还是希望“构筑一堵墙壁,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
王朔1958年出生,到1966年,是8岁,进入“懂事年龄”。到1976年,那场乱子结束,王朔正好18岁,成年了。这一年,王朔高中毕业,从此再没踏入校门。这十年间,王朔满目所见,皆是“反传统”“反文化”。10年间,无数古籍、古画、古墓、古寺、古钱、古玉、古陶瓷、古城墙、古建筑……被一一毁灭,“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阴霾了整个华夏的天空。
今日台湾当局在文化上大搞“去中国化”,居然把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由原来的60%降到50%。记得我在上中学时,文言比例大约25%吧?在王朔的时代,这个比例只有更低,王朔对传统文化接触既少,而在“破四旧”的时代氛围下,对传统缺乏最起码的敬意与温情。
1997年,王朔到美国的博物馆参观,方始见识到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在这之前,王朔直道:“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
王朔是现代、后现代、伪现代。金庸是传统、古典、冬烘;
王朔是新鲜人,金庸是老古董;
王朔的确身染“痞子气”,金庸则难免臭“贵族气”。
二
王朔与金庸之争,表面看,是王朔处于下风,毕竟帮金庸辩护者众,而为王朔助拳者寡。论到二人的单打独斗,处于劣势的反是金庸。王朔放出一把“小王飞刀”后,好整以暇,静观金庸的反应。当金庸一开口回应王朔的搦战(张五常的说法是“金庸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就已经输了。谈什么“八风不动”?做得到?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最佳的应对之道不外:晾着王朔,根本不答复不辩解不搭理,有记者问,答以“今天天气哈哈哈”即可。即此,同时体现了自己的大度和对小王的蔑视,王朔就难免由主动陷于被动,他会四处赶着人强调“我就是那谁谁谁的敌人”!
周作人晚年持“不辩解主义”,是因为“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在知堂看来,就算能说得清的事,辩解起来,“总难说得好看”。
毕竟经济学家更精于计算,张五常就认为:“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或许,老张也是心知肚明:金庸实际处于下风,这才出面帮老友找回场子。金庸也很承他的情,张五常后来对记者谈到金庸的反应:“七年多前王朔发表《我看金庸》,痛骂‘老金’,我写《我也看金庸》回应。老查当时在欧洲,传来的消息是很高兴。后来在杭州遇上,他要求转载我那篇文章在他的一本结集中。”
然则,以金庸的老滑头,为何偏要上赶着去理会小王的骂战呢?他那句“我曾对王朔的小说给予过好评王朔与我不会有个人恩怨”实在没劲透了!文学评价又不是做交易,说李白、拜伦的诗篇好的人多了去了,总不成李、拜就应该回馈他们不错的评语?
我只感觉:当王朔的板斧抡过来的那一刻,金庸确实有些发懵。他要真的不在意,也不会让自己去想“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了。何以致此?因为金庸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与未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很在意了,却无十足的信心、把握。面对“纯文学作家”——即便是王朔这样不咋“纯”的“纯文学作家”,仍有自卑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金庸亲见环珠楼主武侠写得那么好,在文坛与社会上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金庸当然希望己作走向经典化,又将信将疑、患得患失……
张五常认为“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我对金庸的认识则是“唐宋以来世家子,雪芹而后第一人”,所以都不认为金庸有必要对王朔作回应。
三
20世纪中期,神州故国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金庸与王朔,一个站在断裂带的此岸,一个在彼岸。
王朔近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他自许为“五四”的精神传人,而“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无知者无畏》43页)。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论调,他自己做不到,王朔却做到了。
《我看金庸》被王朔收入《无知者无畏》一书,王朔当然并不“无知”,他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甚至堪称“深刻”。在文学本行,王朔对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其阅读量与鉴赏力都足以惊人,唯独对于古典文化真正接近“无知”,——也许,他压根儿也不想“有知”。
好歹王朔也读过一些旧小说,此外的诸子百家、诗经楚辞、汉赋骈文、魏晋文章、唐诗宋词、昆曲京戏……等等,王朔既没有兴趣,也就缺乏讲求。
王朔的小说语言,采自北京方言、日常口语,文字几乎无懈可击,只有当他的杂文中冒出几个文言词汇或是先哲名言时,“硬伤”就很多了。随便以《无知者无畏》所收第一篇文章《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为例,王朔说:“都是叫那帮正人君子害的,天天说钱是万恶之源,君子晓于义,小人晓于利。”《论语·里仁》说的是:“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朔不像是成心要给孔夫子改作文啊。
金庸的理路则与陈寅恪先生为近,不反对吸收西洋文明,但更要保存、继承传统文化。用陈先生的话说来,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否定金庸的文学成就,王朔决不是第一个。但指称金庸的文字“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王朔才是第一人。
当年胡适先生首倡“白话文学”,确为功德无量的伟业。然而,白话的表现力毕竟有限,知堂老人乃为适之先生继作补充修正:
“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决不够用了,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与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
此后,从梁实秋到余光中,无不自觉地“援文言入白话”,到了金庸手上,功德圆满。
王朔只读了《天龙八部》第一册,如果他看到第二部中阿碧与阿朱那段清沥爽脆的吴侬软语的对话,或许能明白:金庸对于地方方言以及口语的捕捉能力决不在他王朔以下。
半文半白,是古代题材小说的客观需要,也是金庸的自觉追求,绝非王朔想当然的“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金庸回应道: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來的风格。”
还是要拉张五常的大旗来做成俺的虎皮:“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四
金庸对古典中国向来充满温情,他晚年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他!”
鲁迅这种对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姿态,事实上为王朔所继承。至于说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东西真的全被“踏倒”,打碎了太多的坛坛罐罐,似乎连“温饱”也没解决完满,何谈“发展”?就差没被开除“球籍”了,对民族“生存”无益有损。这个,也许王朔暂时还没想。
金庸(尤其晚年),很有几分民族主义情绪,而王朔在那个大肥皂泡破灭后,感到一种更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
王朔非常有悟性,其实也不缺乏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当。他从80年代开始,对自己曾接受的社会教育同样有着深入的反思,说王朔仅是“痞子作家”,这点我不认同。在王朔的成长历程中,大陆的时代氛围一是反西方,二是反传统。“反西方”的论调,王朔经过反思,彻底放弃,他既不反西方,更不反美,王朔终于没有成长为一代“愤青”。
至于“反传统”,王朔不仅没有放弃,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毕竟时代不同了,“反西方”比当年的义和拳大师兄的“灭洋”,难度大出许多。在“器物”层面,抛弃所有西方的科技发明,我们今天的生活还剩有什么?
至于“破四旧”,暂时来看对我们的现实生存关系不大,甚至拆了北京老城墙,可以多盖几处猪圈,来年还能多分得几片肥猪肉。毁了宋版元版古籍,化作纸浆,可以印更多的宝书。
更重要的是:当国门被重新打开,我们发现那个“一天天坏下去”的西方世界,并没有让我们骂倒,反而老神在在,精神矍铄。王朔只得承认:“中国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学。”(《无知者无畏》)
“古典中国”则与此迥异,它已经不存在了,并且我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中国今日的一切不如意的屎盆子全扣到“传统”头上,“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无知者无畏》)。
在中西体用之辨上,我更认同王朔。感觉那些个“十博士”“廿教授”搞的种种“文化宣言”好玩极了,也无聊极了。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足以救中国,拿它来拯救世界,更属梦呓。
时至今日,王朔那样彻底反传统的做法,同样无益有损:
【一】在科技器物、公民意识以及体制建设上,自然要学习西方,至于艺文之事,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必需的。
【二】在传统文化势力太过强大的时代,如“五四”时期,矫枉过正,彻底反传统还有其合理性,而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久已花果飘零,仅剩一息残喘。连、宋来访,我们第一流学人的表现已尽够我们自豪了,清华校长不识字,厦大校长不识不知“黉宫”就是古代的学校,给读成“皇宫”,清华文科教授中冒出一个“当代仓颉”,靠嘴皮子就发明了一种新书体,叫作“小隶”!
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再去反传统,怎么看都像“打死老虎”,既不足以言勇,反而迹近无聊。
【三】古典中国当然不是“新儒”所夸称的“用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儒家的忠恕教化、佛道的来生信仰,也确实使古人具有一种“人情之美”,不排除其中夹杂有虚假的成分,而实具安定社会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现在那么多危及国人生命的假货,我们的祖先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他们造不出来。有了技术,他们也未必会做,因为他们太“迷信”,做这等缺德事,会有报应的。
美利坚是最前卫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保守的国家。90%以上的人对宗教仍然比较虔诚。抽掉了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山姆大叔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与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现代化”为号召,时至今日,真正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除了欧洲国家、欧洲人后裔建立的国家以及米兰·昆德拉所说“欧洲体外的心脏”以色列之外,只见“儒家文化圈”的东亚数个国家、地区,足证:中国传统文化比其他非欧洲民族的固有文化,更不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受幼年社会影响,也与王朔本人的个性、阅历相关,他对于传统带有一种过敏式的反感与排斥:“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一定要站在它的对面。”
具有浓厚传统特色的金庸小说从80年代进入大陆,影响力惊人。
1999年11月,王朔出列。
站到了金庸的对面。
五
冯其庸读金庸,王蒙说王朔,两相对照,比较好玩。
冯其庸《读金庸》:
“笔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具有一种豪气干云、一往无前的气概,给人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并且他笔下的人物,也使人感到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人们可以怀疑其真赝,有一点还是确定无疑的:金庸在他的作品中表达、摹写了这个民族一些“崇高”的品质与气象。
王蒙评论王朔的文章就叫做《躲避崇高》:
“王朔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开了玩笑……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
对于从小就接触、被灌输的那些“崇高”的字眼,王朔具有条件反射式的敏感与反感。金庸的作品他没有胃口细看,本能地认定金庸笔下的侠客与他打小从书籍、电影看到的英雄人物是一路货色。
某些“崇高”背后有着伟大的力量保驾护航,对这样的“崇高”,王朔不能反抗,只能“躲避”。这个大家很能理解。王朔可“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像自己一样的一介文人而已,何须躲避,怕他何来?直是鸣鼓而攻之可也!此时的王朔,大智大勇,转为凌厉无前的攻击:
“(金庸笔下的人物)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爱国主义大帽子……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王朔《我看金庸》令人最恶心的地方,不是对金庸的攻击,而是他为了贬低“四大俗”而正面提出的“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前三项没什么问题,至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就让人搞不懂了。这根支柱,用的是什么名贵木料?《渴望》?《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都什么玩艺儿?!当年的王朔也知道也说过室内剧就是“肥皂剧”,没有价值的。《北京人在纽约》获奖,主演姜文没去参加以此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与王朔对谈的“老侠”先生表扬道:“拍个煽情的电视剧,本身就是跌份儿的事,再去领什么奖就更让明眼人瞧不起了”(老侠、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也没见王朔挺身而出捍卫他自己的以及这个国家的文化支柱。
一个庞大的国家,居然寒碜到只能把电视剧作为支撑文化屋檐的四根顶梁柱之一,实不知王朔此文是要贬低港台文化还是有着恶搞大陆文化的更加隐蔽也就更加险恶的用心。
弘扬大陆“四大支柱”,抵制港台“四大俗”,可你拿960万跟3.7万平方公里、拿13亿跟3000万人口比量,就算大获全胜,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不摆明了以大欺小吗?不嫌跌份儿吗?
公道点说,王朔实无意以大欺小,无奈放眼现实世界,在文化上,大不能欺小,小的反而咄咄逼人,对大陆展开文化反攻。
我想,这才是王朔所切齿于金庸与整体港台文化的真正原因。
2007、2
补记:
王朔攻击金庸,是为了炒作自己?只是有可能,决不是全部。
王朔说:“以你(金庸)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那么,苍茫人世间,到底有无值得扯上“千秋大义家国之恨”的不“恶心”不“扯蛋”的争斗呢?
就不要四处瞧了!典型不远,便是眼下、当前、此公。
“大家把金庸捧得这么高,只能说大家是‘睁眼瞎’,别人糊涂,我可不傻。”
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无论对错,确是在捍卫某些他心中以为神圣的东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