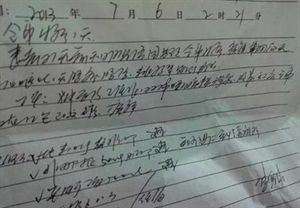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首歌绝对是最流行的歌曲之一。那时候,台湾校园歌曲以其简单清新的旋律、清纯抒情的曲调、欢快上口的歌词风靡大学校园。我的同桌是班里的文娱委员,每周都要拿几个傍晚来教歌,《踏浪》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故乡地处鲁北沿海,离大海仅有五十几里路,可我没有见过大海;故乡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所以在读大学之前我没见过山,至于山上的山花是啥模样就更无从知晓了。
母校在千佛山北麓,依山势而建,进学校实际上就相当于爬山了;而校园的花开也就是山花开了——可心里总觉得不是一个事儿。或许,那浅陋的见识里总在期待山上该有另外一种风光吧。
第一次登山就是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对我来说,登山是个十分重要的事儿,原想郑重其事地选个时间,然后郑重其事地去爬山。跟同桌出去买东西回到宿舍,有些累,正躺在床上休息;一位学兄敲门,问“想去爬山吗?”我腾地坐起来,拉上同桌就跟着去了。学兄领着我们从一条小路上的山,目的倒不是为了逃票——那时候山门是没有售票处的,只在千佛山寺的大门口有卖票的;我们纯粹是为了过爬山的“瘾”:学兄很是知道我们这些第一次爬山的人心里想啥!山下的层层梯田还种着玉米、大豆等庄稼,跟我们老家没什么两样;田边地头的狗尾巴草、苦苦菜花也没有什么特殊。走过一个小村,开始进入林区。千佛山北麓的松柏非常茂盛,这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穿行在茂密的林间,不时拨开拦路的灌木——而这些灌木几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其中一种不起眼的灌木,开着洁白的花絮,浓香四溢,问学兄是什么花,学兄摇摇头,不知道。后来我多次在山上见到这种花,却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今年春天,我从影友的摄影里知道,它有着一个极有诗意的名字:“珍珠梅”!
在泉城求学的日子,登山几乎成了一门“必修课”。四年时间里,我每周都要跑几次千佛山,算是健身。至于冬日的周末、夏季的黄昏,几位同学一起散步到千佛山也是常事。第二年春天,一种瘦瘦弱弱的黄花在凛冽的寒风里盛开了,同桌告诉我是迎春花;登山的时候,看到千佛山脚下一棵开得金灿灿的树,问一位大爷,大爷说:“迎春啊!”我直觉感到跟迎春不一样,后来才知道那是连翘。小时候读白居易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老师怎么解释也只能是想当然尔;如今登山,看山寺的桃花真的姗姗来迟,才不得不敬畏古人的博学多识、用词的洗练。

在艰难的求学生涯中,登山不仅仅是为了锻炼,也不仅是为了赏玩,有时候还是一种宣泄,一种排遣。
一个仲春的雨后,我曾独自一人钻进密林,看山花烂漫,听百鸟齐鸣,而情不自禁地大喊:“大——山,我——来——了——!”
一个盛夏的黄昏,我在半山腰找到一块铁皮方板,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闻着山花的芳香,任山风吹拂,任思绪飞扬。
在一个中秋的月下,我们组的同胞聚餐后相携登山,一路欢歌,一路海侃,直至醉卧山巅……
“……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
熟悉的旋律久已不闻,再次响起,禁不住眼眶发酸。山上山花尚开否?若是山花依然开,朋友,你能否再陪我上山看花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