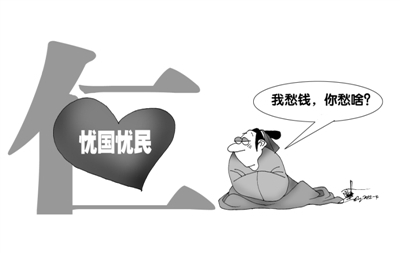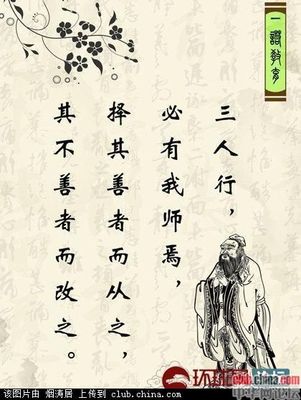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凿[集解]对曰:“然,非与?”孔曰:“然,谓多学而识之。非与,问今不然。”
何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时人见孔子多识,并谓孔子多学世事而识之,故孔子问子贡而释之也。然,如此也。子贡答曰,赐亦谓孔子多学故如此多识之也。子贡又嫌孔子非多学而识,故更问定云非与。与,不定之辞也。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学而识之也。贯,犹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学而识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识者,我以一善之理贯穿万事,而万事自然可识,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贯之也。
[朱子集注]子贡之学,多而能识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问以发之。方信而忽疑,盖其积学功至,而亦将有得也。说见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谢氏曰:“圣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观而尽识,宜其以为多学而识之也。然圣人岂务博者哉?如天之于众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贯之。’‘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愚按: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
顾炎武《日知录》:
予一以贯之,“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按:顾炎武之说,乃是就知识而言,是“一贯”而不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是立脚点、是根基。
阮元《擘经室集》“一贯”说:
贯,行也。此夫子恐子贡但以多学而识学圣人,而不于行事学圣人也。夫子于曾子则直告之,于子贡则略加问难而出之,卒之告子贡曰“予一以贯之”,亦谓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
焦循《论语补疏》:
《系辞传》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韩康伯注云:“少则得,多则惑。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与何晏说同。《易传》言“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何氏倒其文,为“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则失乎圣人之指。《庄子》引《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此何韩之说也。夫通于一而万事毕,是执一之谓也,非一以贯之也。孔子以一贯语曾子,曾子即发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舜于天下之善,无不从之,是真一以贯之。以一心而同万善,所以大也。一贯则为圣人,执一则为异端。董子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四气者,天与人所同也。天与人一贯,人与己一贯,故一贯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学?无常师,无可无不可。异端反是。孟子以杨朱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由于不忠恕,杨子惟知为己而不知兼爱,墨子惟知兼爱而不知为我,子莫但知执中而不知有当为我当兼爱之时也。为杨者必斥墨,为墨者必斥杨。杨已不能贯墨,墨已不能贯杨。使杨子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一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执中者也。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摒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之不知,人其舍诸”,举贤之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学之基也。善与人同,则人之所知所能者皆我之所知所能,而无有异。惟事事欲出乎己,则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则不与人同而与人异。执两端而一贯者,圣人也。执一端而无权者,异端也。《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各有所当,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记礼书》云:“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惟孔子无所不贯,似恃乎多学而识之。乃多学而识,仍自致其功,而未尝通于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学而识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后知至,故无不知。由身以达乎家国天下,是一以贯之也。一以贯之,则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执其多,仍执一矣。
光辉按:焦循此说著于皮相,“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学而识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后知至,故无不知。”,讲的还是技能知识问题。
刘宝楠《论语正义》:
夫子言“君子博学于文”,又自言“默而识之”,是孔子以多学而识为贵,故子贡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犹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圣门之教,行尤为要。《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多学而识之也。笃行,一以贯之也。《荀子·劝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则徒博学而不能行,如诵诗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与诏曾子语相发也。
程树德氏引此四者系于考证,曰:“按以上为汉学家所说之一贯,虽不尽然,而语不离宗。至宋儒乃各以所树立之主义为一贯,而论始歧,当于下详之。”(程树德《论语集释》)
朱熹《论语或问》:
夫子以一贯告子贡,使知夫学者虽不可以不多学,然亦有所谓一以贯之,然后为至耳。盖子贡之学固博矣,然意其特于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当然,而未能知乎万理之为一,而廓然无所不通也。若是者虽有以知乎众理之所在,而泛然莫为之统,其处事接物之间,有以处其所尝学者,而于其所未尝学者,则不能有以通也。故其闻一则止能知二,非以亿而言则亦不能以屡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圣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谓众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贯通之,则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无不通矣。
朱熹《朱子语类》:
孔子告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予一以贯之。”盖恐子贡只以己为多学,而不知一以贯之之理。后人不会其意,遂以为孔子只是一贯,元不用多学。若不是多学,却贯个甚底!且如钱贯谓之贯,须是有钱,方贯得;若无钱,却贯个甚!孔子实是多学,无一事不理会过。若不是许大精神,亦吞不得许多。只是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耳。
吕枏《四书因问》:
予一以贯之,此一字非泛然之一,如《书》“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尝不自多学中来。但其多识前言往行,便要蓄德;多闻多见,便要寡尤寡悔,所以扩充是一而至于纯,故足以泛应万事。若祗泛泛说一,则或贰以二,或参以三,元自不纯,理与我不相属,又何以贯通天下之事。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1)“吾道一以贯之”,“之”字所指,包括周遍。“予一以贯之”,“之”字所指,则子贡所疑为“多学而识之”者也。于此有别,故集注曰“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若云“一”云“贯”,则未尝有异,故集注云“说见第四篇”。以实求之,此所云“贯”,以言知,而未该夫行;若“吾道一以贯之”,则言行,而岂遗夫知哉?使遗夫知,则所知者亦夫子之道也,而彼所云“一”,“一”外更有“一”;彼所云“贯”,有所“贯”而有所不“贯”矣。
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且知行二义,有时相为对待,有时不相为对待。如“明明德”者,行之极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为先焉。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故“吾道一以贯之”者,并子贡所疑为“多学而识之”者而亦贯也。
然则“予一以贯之”者,亦可受贯于忠恕乎?此读书者之所必疑也。虽然,恶在其非忠恕耶?谢氏曰:“‘予一以贯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所谓“上天之载”者:其于天,则诚也,“其为物不贰,而生物不测”者也,是即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者也;其于人,则诚之者也,“笃恭而天下平”也,是即所谓“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者也。乃于行见此易,而于知见此则难,故疑一以贯乎所知之理者,不可以忠恕言也。呜呼!苟非知圣学之津涘者,固不足以知之。然唯不知此,则不得不疑为“多学而识之”矣。藉令不此之疑,则又以为神灵天纵,而智睿不繇心思,则其荒唐迂诞,率天下以废学圣之功,其愈为邪说淫词之归矣!
(2)“予一以贯之”,亦非不可以曾子“忠恕”之旨通之。此非知德者不足以与于斯,先儒之所重言,而愚何敢言。虽然,其无已言之。忠,尽己也;恕,推己也。尽己之理而忠,则以贯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则以贯天下之情。推其所尽之己而忠恕,则天下之情理无不贯也。斯“一以贯之”矣。
夫圣人之所知者,岂果有如俗儒所传“萍实”、“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亦物之理无不明、物之情无不得之谓也,得理以达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谓也。如是而古今之远,四海之大,伦常礼法之赜,人官物曲之繁,无不皆备于我矣。
所以“皆备”者何也?理在心,而心尽则理尽也;情沿性,而知性则知情也;理之不爽,情之不远,于己取之而皆备矣。己之理尽,则可以达天下之情;己之情推,则遂以通天下之理。故尽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学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学者之忠恕也。理尽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圣人之所以穷神知化也,圣人之忠恕也。
天下之事,无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无不如情而生。诚有其理,故诚有其事;诚有其情,故诚有其物。事物万有者,干道之变化;理情一致者,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生物不测”,皆示人以易知者也,天道之忠恕也。
故乌吾知其黑,鹄吾知其白,茧吾知其可丝,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恒而无不忠,以充满发见于两闲,推之无吝、如之不妄而无不恕。圣人以此贯事物之情理,学焉而即知,识焉而不忘,非所学、非所识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祖述、宪章,以大本生达道,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一诚而已矣。诚者天之道也,物之终始也,大明终始而无不知也。呜呼!过此以往,则固不可以言传矣。
(3)或问中“语子贡一贯之理”一段,中闲驳杂特甚。朱子曰“此说亦善”,取其“不躐等”数语,为学有津涘耳。乃其曰“一体该摄乎万殊”,则固然矣;抑曰“万殊还归乎一原”,则圣贤之道,从无此颠倒也。周易及太极图说、西铭等篇,一件大界限,正在此分别。此语一倒,纵复尽心力而为之,愈陷异端。愚于此辨之详矣。
又曰“圣人生知,固不待多学而识”,则愚所谓荒唐迂诞之邪说也。
又曰“学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及夫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则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此虽与大学补传相似,而揆之圣言,则既背戾;且其言亦有自相剌谬而不知者。朱门诸子,用一死印板,摹朱子语作生活,其于朱子之微言且不得达,况圣人之旨耶!

子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又曰“予一以贯之”,凡两言“以”。“以”者用也,谓圣功之所自成,而非以言乎圣功之已成也。然则夫子自志学以来,即从事于“一以贯之”,而非其用功在多,得悟在一也。若云“向之多学而得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则夫子之能“一以贯”者,其得力正在“多学而识”,子贡之所曰“然”者,正有以见圣功之本原,而何以云“非也”?则揆之圣言,岂不为背戾耶?
其云“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固与夫子博文、约礼之训相为符合,乃既云“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又云“积累既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则敬既为主矣,于此之外而别有一本以待他日之知,是始之一本,而既之又一本也。此所谓自相剌谬者也。
繇此问者初不知有何者为一,妄亿他日且有□力地光明、芥子纳须弥、粒粟藏世界之境,而姑从繁重以求之。子贡之疑,初不如是,子且急斥之曰“非也”,况其以学识为敲门砖子者哉?
天地之道,所性之德,即凡可学可识者,皆一也。故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一而物备焉,岂一物一理,打破方通也哉?
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入处,则学识徒为玩物。古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是颜子早年不应有“亦足以发”之几,而夫子在志学之年,且应不察本原,贸贸然求之,而未知所归也。
无已,则曰,彼所言者,乃为初学言耳。然学者之始事,固无能贯之力,而要不可昧于一之理。“明则诚”者,圣人之德也。“诚则明”者,君子之功也。故彼所谓“主敬力行以反于约”者,即初学入德之“一以贯之”也。子固曰“予一以贯之”,而不曰“予既已能贯之于一”也,则圣固以为功焉,而非豁然贯通之速效矣。
故博文、约礼,并致为功。方博而即方约,方文而即方礼;于文见礼,而以礼征文。礼者,天理自然之则也。约而反身求之,以尽己之理,而推己之情,则天理自然之则着焉。故大学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初不以前日为之之谓先,后日为之之谓后,而必以明德为本,知止为始,非姑从事于末而几弋获其本也。
乃既曰“反诸约”,又曰“然后知其一本而不二”,若反约之日,犹将迷于一本者然。足以知发此问者,不知何者为一,而妄亿有单传末后之句,得之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日,则岂不诬哉!
若其功之浅深,几之生熟,固必有之。其为圣人也,而后笃实光辉,以知则耳顺,以行则从欲。其未至者,多有捍格不合之处。然其不合者,亦非不可必合;积诚于会通之观,典礼之行,而“诚则明”矣。非当其未之能贯,则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且埋头瞎撞,依样循持而不求其故。然则为朱、陆之辨者,始终原自异致,正不前半修考亭之功,后半期鹅湖之效,遂可傲陆氏而自立门户。必如此说,则鹅湖且得以格物穷理为敲门砖子傲人矣。
子夏“先传后倦”之说,其失正在此。自非圣人,固不能有始而即有卒,而方其始不知所卒,则亦适越而北辕,又奚可哉!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其云“将以”者,言将此以说约也,非今之姑为博且详,以为他日说约之资也。约者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故将以反说夫约,于是乎博学而详说之,凡其为博且详者,皆为约致其功也。若不以说约故博学而详说之,则其博其详,假道谬涂而深劳反复,果何为哉!此优孟衣冠与说铃、书厨之士,与圣贤同其学识,而无理以为之则,无情以为之准,所以祗成其俗儒,而以希顿悟之一旦,几何而不为裴休、杨亿之归哉!圣学隐,大义乖,亦可闵已!
王肇晋《论语经正录》:
朱子文集方宾王问一贯谓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与《或问》说同,故朱子善之。陆稼书亦谓一贯是功夫熟后自然见得学者不可预求一贯。而王船山则谓予一以贯之,谓圣功之所自成,非言乎圣功之已成。杨宾实则谓一以贯之非贯而为一之谓。夫子教人为学,功夫原从一上做起,说有不同何也?盖一贯有已成之极诣,则所难在实。论学而至之之功,则所学无非致一。朱子、稼书以已成之极诣言,谓子贡之多学而识,积累功致,夫子以一贯指示之而翼其悟也,故有豁然贯通之说,而戒学者之预求。王氏、杨氏以学而至之之功言,谓夫子告子贡多学而识,当知一以贯之之道,而不可徒役志于学识,故谓主敬存诚即致一之要。是其所指而言者虽不同而理则无二。故朱子又云:“夫子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一者,性之理也,诚也,其功夫则存诚也。圣人不待存而无不诚,诚则明矣,一以贯之之谓也。”
陆陇其《松阳讲义》:
当日夫子告曾子、子贡绝不是含糊说个一,自然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即应之速,而子贡不再问。门人所以有何谓之而问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见夫子平日论工夫体用俱分作两截,至此则偏重在体上,似另有一个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谓圣人之心一如学者之心,未熟则忠自忠恕自恕,熟了则忠即恕而恕即忠,虽谓道只有一个忠可也,并非另有个直截法门。曾子此二句塞了许多弊窦,不然,门人这一疑,便要走到虚无寂灭去了。子贡后来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天道虽另有一番指点,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后自能见得。
孔广森《经学巵言》:
告子贡之一贯与告曾子之一贯语意不同,彼以道之成体言,此以学之用功言也。子之问子贡,非以学为非,以其多学而识为非。子贡正专事于识者,故始而然之,但见夫子发问之意似为不然,故有非与之请,此亦质疑常理,必以为积久功深,言下顿悟,便涉禅解。予一以贯之,言予之多学,乃执一理以贯通所闻,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证故,必如是然后学可多也。若一一识之,则其识既难,其忘亦易,非所以为多学之道矣。盖一贯者为从事于多学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能一旦贯通,得无与此义相左乎?
程树德按:程朱派以主敬穷理为一贯,无有是处。格物穷理之不能一贯,孔氏广森之说是也。至主敬之不能一贯,则王阳明《传习录》已言之矣:“人若矜持太过,总是有弊。曰矜持太过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数语切中主敬之弊。
焦竑《焦氏笔乘》:
李嘉谋曰:“多学之为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则仁义不相反,忠孝不相违,刚柔不相背,曲直不相害,动静不相乱,语默不相反,如是则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异道,道不异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于一,万事毕。”又曰:“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为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自知其即为道,舍无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夫门人疑一贯之说,如系风捕影之难,而曾子断断然以忠恕尽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谁乎?”杨敬仲曰:“夜半爨火灭,饥者索食对灯而坐,不知烛之即火也,则终于饥而已。忠恕之论,烛喻也。”又曰:“老子曰:道生一。当其为道,一尚无有也,然一非所以为道,而犹近于本;多学虽非离于道,而已涉于末,二者则大有间矣。虽然,此为未悟者辨也。学者真悟,多即一,一即多也,斯庶几孔子之一贯者已。”
李颙《四书反身录》:
子贡聪明博识,而学昧本原,故夫子借己开发,使之反博归约,务敦本原。本原诚虚灵纯粹,终始无间,自然四端万善,溥博渊泉而时出,肆应无穷,无往不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贞乎一,斯贯矣。问一,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则常一,常一则事有万变。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聪明博识,足以穷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不足以体道。若欲心与理融,打成片段,事与道凝,左右逢源,须黜聪堕明,将平日种种闻见种种记忆尽情舍却,尽情瞥脱,令中心空空洞洞了无一翳,斯干干净净方有入机,否则憧憧往来,障道不浅。
程树德按:陆王派以良知为一贯,虽未必尽合孔氏之旨,然尚有办法,较之空言穷理而毫无所得者似差胜一筹也。
李塨《论语传注》:
文武之道在人,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夫子焉不学,是多学而识也。然在十五志学则然,迨至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一以贯之,无事多学而识矣。圣门除颜子而外,首推曾子,达者首推子贡,故以上语之。
光辉按:然则孔子“不知老之将至”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又是何境界?
程树德按:宋学中颜李一派,其见解与程朱、陆王两派均异,兹于列举诸家之后列此一说,以备后之研究此章者,得观览焉。
李颙《四书反身录》:
博识以养心,犹饮食以养身,多饮多食物而不化,养身者反有以害身;多闻多识物而不化,养心者反有以害心。饮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识能化,愈博愈妙。盖并包无遗,方有以贯,苟所识弗博,虽欲贯,无由贯。刘文靖谓邱文庄博而寡要,常言邱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贤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斯言固戏,切中学人徒博而不约,及空疏而不博之弊。
吕留良《四书讲义》:
谢显道博举史书,程子谓其玩物丧志,谢闻悚然。及看明道读史,却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初不服,后来省悟,却将此事做话头接引博学之士。须知夫子此个话头,正从实地接引耳。如以学识为敲门之砖,以一贯为密室之帕,皆狐禅矣。若问曰:一以贯之如何?应对曰:多学而识之可也。
光辉按:若庄周所谓“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庄子·逍遥游》)者,可谓之一贯乎?
程树德按:阳明之良知说,陆稼书讥为野狐禅。伊川之穷理说,阳明亦斥为洪水猛兽。然其一贯须从多学而识入手,则同。此章为孔门传授心法,诸家所说均未满意,尚待后人之发明也。
以上,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外,尽录程树德先生关于此章的引文。
而《论语》当中与此章相关之章节有: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7-28)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
这一章的解释,成为不同家法的法门,因此人言人殊。但是我认为,这一章并4-15章其实包含了天道与人道的问题,孔子认为天道是永恒的必然,是存在本身,而人道则有通塞、有穷达、有治乱。所以一以贯之者,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在这个化生的世界当中,天的意志是可与人道相通的,因此人的一生是可能崇高的一生,是证成其崇高的可能的一生,因此此一贯即是所是、应是、当是的界定中,证成人生可能的高度,而不仅是闻见而已,不然大盗窃国亦可以是可以多学而识,这也是曾子应之以忠恕的意思。
度这中间涉及知识与智慧、目的与手段问题。
语曾参时说“吾道”,此呼子贡而言者“学”,以子贡之善言辞而不更辩难者,以为当无疑义也;曾子以为忠恕者,示门人也。孔子反复强调学的重要性,但是其所谓“学”,不是简单的知识性学习,而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根本的人生信条则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6)、“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29),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博闻强记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慧问题,是手段而不是道路。同时,从孔子强调的“学”来看,不是我们今日所谓学知识、学文化的意思,而是学立身行事的准则和应世济民的手段,所谓“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是也,因此与吾道一以贯之并不矛盾。
将孔子的问题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当中,则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因为孔子的问题,与人的自我问题密不可分。
关于人的自我问题,未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人类祖先不存在自我问题,他们的存在是未被自我定义的存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就是透过人与自然的异质化,开始照亮了一条道路。当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异质关系,开始建构自己的来路去途时,就开始踏上了“陌生化”的道路,当然也是文明化的道路。在这陌生化的道路上,不同群体的神裔性想象是驯服陌生化的有效尝试,这一步是通过想象建构起某一神的后裔这一统一族群来实现的,而不同族群作为不同的神的后代,他们之间的差别,与牛和鱼的差别一样大,而这就是文明之源。当更群体的规模突破了单一的族群时,族群之间的交往打破了封闭的神裔族群主体,怎样超越神裔想象来定义异质化的其它族群,就成为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一次汹涌的陌生化浪潮,印度、古希腊等古代文明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文明/野蛮的分野是这一时期的核心观念,并进而出现了普世性的关于人的想象。而华夏世界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面临着这一问题,孔子的思考就是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试图在天人图景当中建立人的图景,在化生世界模式中设定人的社会特点——从属于人际网络当中,而其关于人的定义则是通过他者来定义自我,每一个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境况中得到认定,同时建立起华夷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而在这当中,个体是已然的。第三次陌生化则正是由于个体的已然出现危机,完全陌生化的个人是最大的问题,在完全流动化的全新世界图景中,马机雅维利关于生存的争辩(超越德性)、霍布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成了预言之声,而卢梭的契约论可以看作是领悟了这一次陌生化浪潮展开的定义自我之尝试,而其标志性的言辞则是“上帝死了”;而当我们在上世纪初宣布孔子死了之时,我们也就剧烈地跨入了这一语境……。
而卡尔·巴特的陈述具有它山之石的意谓——
对于我们的一切所是、所有、所为而言,上帝是纯粹的界限和纯粹的开端。他与人类、与一切人性的东西之间存在着质上的云泥之别,他永远不是我们称呼、体验、感觉和祈求的所谓“上帝”。对人的一切不安,他是无条件的“止步!”吼声;对人的一切安宁,它是无条件的“前进!”号令。他是我们的“不!”中的“是!”,是我们的“是!”中的“不!”;他是最先者和最终者,作为这样的未识者,永远不在我们熟悉的“始终之间”与万物并列;他是主,是创世主和救世主——这样的他是活生生的上帝。[1]
恩典是服从。复活的概念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的一种所是、所有、所为,这种所是、所有、所为与人迄今为止的、与一切可能的所是、所有、所为的关系犹如生与死的关系。我们的存在开始处于黑白分明的、不可更改的“非此即彼”的局面!我们的存在进入了它最终可能性的领域,不,进入了它不可能的可能性的领域,恩典是这样一位上帝与人的关系:他刚披挂上阵,就已大获全胜;他不允许我们走中间道路,不允许我们对他冷言冷语;他是吞噬万有的烈火,没有义务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他高呼“是!”,高呼“阿们!”,而我们却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似乎”,模棱两可地说什么“是又不是”。[2]
孔子的“天”有这个绝对性(如上帝)的意味。孔子乃至整个子学时代的话语背景,即天道之基本预设,这是绝对的存在,而人道本身则是通过天降圣人实现天的意志,“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人谱系,则是天的意志在时间中的呈现。
冯友兰先生认为,天有五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3]但是在孔子的语境中,“天”是绝对的他者,更像是卡尔·巴特语境中的“上帝”(这也是秦汉儒士、方士合流形成天命式宗教形态之源,参考顾颉刚先生《汉代学术史略》),而孔子将视域限定在“生死之间”正是因为此。当然,在现世的视域中,孔子认为人之所是、所有、所为是必然以天的意志为依据,而天人之间不是对立的,不过只有天命之“圣人”才能体现天的意志,处于天人之间的枢纽位置,而士君子则通过时间中的证成和呈现实现其主体性,普通平名百姓则是未被定义者——“民者,冥也”。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对于士君子等之存在问题,是在承认现实的价值基础上进行言说,而好货、好色等之作为存在的基本色彩,并没有被孔子打上绝对的道德烙印,因此并不存在“存天理灭人欲”一大关节(这是宋儒在“天”被消解之后,重新建立的语境)。同时,在孔子接受的语境当中,“天道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观念有一点卡尔·巴特氏所说的“他是最先者和最终者,作为这样的未识者,永远不在我们熟悉的‘始终之间’与万物并列;他是主,是创世主和救世主——这样的他是活生生的上帝”的意思),这样的绝对性,又在“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的指称当中转化为现世德行的动力。从此,“天”已经蕴含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族群的定义已经开始模糊,地域化的群体整合正在消融神裔传统中的异质化因素,
孔子坚信:自己就是天命的承负者,承续了圣人谱系当中“神圣使命”,担当着重塑礼乐制度的伟大使命。孔子以绝对的圣王律令统系天下,以人伦血缘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奠定人世的基本,从肯定人的自然(血缘关系、生存需要等)出发,消融周公“尊尊亲亲”之制的族群内核。
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对士君子(统治者及潜在的统治者)发言,坚定地肯定士君子的人伦主体资格(诛独夫的说法就是孟子对于孔子言辞的发挥,这最能体现士君子之主体特征)。在此层面,孔子建立起了圣王的谱系、仁者的谱系、君子的谱系,并进而建立相应的德性谱系,树立起人世的旗帜,在对弟子的训诲中,反复强调士君子的伦理主体资格,此之所谓“一贯”。伦理主体资格即是以人生为可以崇高的可能,并能实现可能的高度,具体的人伦主体之证成、提升、呈现,就是在“躬行”、“为仁在己”,其“无所不与二三子”者亦以此,而“一贯”之旨亦在乎此。在孔子的言说中,坚守的东西是什么?此乃其一贯,学也,以此一贯;道也,以此一贯。
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其所是而言,则是“忠”;就其当是而言,则是“思无邪”;自其应是而言,则是“宁俭”;自其必是而言,则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而其大本,则在“克己复礼”,于立己当中明其所是、应是、当是、必是,所以一以贯之。
而在汉儒眼中,伦理主体的不同层位,则将孔子的话语转化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单向性律令,君王(天之子)具有人世唯一的绝对性主体资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转而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父而外,均处于帝王的标尺之下,成为孔子的圣人理想遭遇帝制现实的政治性意识形态。
宋儒的津梁,是在至高无上的“天”的终极意义被“空”与“无”(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彻底消解的情况下[4],提出“天理”问题,建立自己的根本,而大倡天理人欲之辨,成为主敬穷理的流派;陆王则以良知良能为自家根本,树立起一面旗帜;颜李“实学”则又自成一路,试图在放弃超越性追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路。
正如葛兆光氏所说:隋唐而后的南宗禅“只能解决个人心灵的宁静和适意,甚至只能在纯粹心理层面上抚慰自己。作为人生的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它也许不可替代,但是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种人生手段,它也许会使人流于平庸或流于放纵。……在中国思想大转型的中唐,儒佛道全面融合建立一个新型思想体系时,以儒家思想定位并吸取道释思想的那一批人,表面上看来是从南宗禅那里得到思想资源,但在汇入新思想时那些资源都剥落一层还原为近乎北宗禅的理路。”[5]“宋儒所说的‘不睹不闻是主体,戒慎恐惧是工夫’,即佛氏所谓‘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也。”[6]然宋儒之所是,其标尺仍然处于帝王的标尺之下。人世的所是、应是、当是莫不以圣王的标尺作为度量的依据,亿兆臣妾之民自然低了半截(奴才是不配享有德性的)。“天”之绝对存在的消融,在宋儒是以释道渡将来的“心”、“理”命题进行充实,此是朱子之天理,陆王之良知。不过化生世界模式仍是其骨架,并且是所谓“和”的世界所依托者。
离开了“天的意志”,在尘世当中肯定尘世,必要以尘世的物量为依据,在君王为最高权威的现世组织,君王及其统系的组织,控制了域内的物质性资源,君王的所有臣民只因为君王的恩赐、而不加剥夺才能拥有某物,其所为则以帝王允准为据,垄断和控制了物性资源的君王,同时也就垄断了命名的权力,所谓“惟器与名不可假人”是也,从而也就为臣民的精神定下高度。在肯定尘世的意义上,只有建立了个人温暖的物性家园,方有可能建立起个人的绝对伦理主体地位(近日读一文曰当首先建立“私民社会”,其意近之)。
正是由于尘世的个人存在是在人伦关系中得以定义,并且在尘世的生活中完成自我,那么依据人伦原则通过他者定义自我就成为必然,而尘世生活正是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的个体就是既勤劳又知足的个体,人伦中的他者的界定作用既为个人安置了家园,也为个人配置了相应的目标和理想,即使在死亡的边界之外,死者作为家族的亡灵仍然参与着人伦的工作。
孔子的“一贯”指向着人的自我问题。在孔子的定义中,个体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皆在人伦血缘中建立,以此解决了族群离散后政治的组织和社会的组织(族群间的“陌生化”,以周天子的族群征服了殷人后,以其整个族群建立政权,组织起姻亲诸侯封建的辽阔国家,我周与尔殷之间有一大分别在。春秋之世,地域化的整合运动,已经背离了“尊尊亲亲”体系,僖公三十三年弦高之犒师,鲁人赎奴的故事,显示出礼崩乐坏后新的地域化整合趋向,古老的族群开始离散,新的活跃力量正在聚集),以人伦血缘组织社会取代族群对社会的组织,以圣王范型政治,以选拔人才代替世官制度,从而建立起超越族群的、以文明野蛮华夷之辨的标尺,建立起超越族群的以人伦血缘为核心的社会认同,从而构建起稳定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封闭的社会架构,实现社会基层的单一化和邻里化,进而消解陌生化问题。
[1] 卡尔巴特着,魏育青译《罗马书释义》,第30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同上, 第211页。
[3] 冯友兰着《中国哲学史》,第55页。
[4] 葛兆光着《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葛兆光着《中国禅思想史》,第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同上,页,219。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