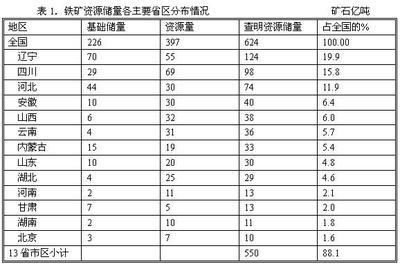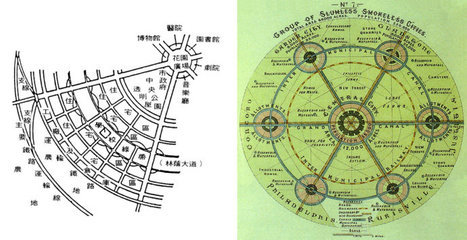以电影《天下无贼》和《甲方乙方》编剧的身份在百姓中一窜而红的王刚,在数年前就写了小说《英格力士》。2009年夏天,美国的企鹅集团所属的维京出版社发表了此书的英译本,将「洋泾滨」的英语书名转回到正宗的原汁原味,English。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入英语世界者,一向不多。English一书本是给美国读者看的,却意外地给了海外华文读者一个新的机会。「英格力士」一词,所蕴含的文字和人文意义,在中文的语境和英语的本土,毕竟是不同的。流落在母语之外的华人,包括华人写作者,尤其是从上世纪60年代活过来的人,读「英格力士」版《英格力士》,感受因此而加倍地放大。
英语:灵
当代散文名家张宗子先生说,对中文的失望,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这个话宗子是在海外说的。以此推想,在以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并和欧美敌对的时候,对于英语的盼望,是否可以说,是对于自己的希望?王刚的「英格力士」的故事,正好诠释了这个一种语言文字和人性的关系。
事情发生在60年代的新疆乌鲁木齐。迁居边疆的建筑师夫妇的儿子刘爱(英语就翻译为LoveLiu)和一班小朋友们停了俄语,连维吾尔语也学不下去了,因为老师阿吉泰要调走了。阿吉泰是个漂亮的混血儿,是乌鲁木齐人的骄傲,让班上男孩们脸红、发愣的人。「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她的头发像阳光一样灿烂,她的大腿像是玉石雕刻的,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从博格达峰上融化的雪水」。但班上的女同学没有这样的沉重,「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很快就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何以新疆的小学生居然要在连庙宇都拆了的年代突然学英语了,已无可考。英语老师是王亚军(SecondPrize Wang),一个穿着讲究、干干净净,充满绅士气的上海人。进出课堂,他夹着一本英语字典,乌鲁木齐唯一的一本英语字典。这本神秘的书吸引了刘爱的眼球。起初是和英语课代表黄旭升(SunriseHuang)争宠,因为王老师为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开小灶补课,教她国际音标,念出每一个英文字。当刘爱也有了进入老师宿舍的机会,他发现,这本英文字典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比新鲜的刺激;每个字组合在一起,就编制出了沉闷单调的都市所没有的世界。刘爱和黄旭升住一个筒子楼里长大,刘爱便去她那里学音标。这是一种快乐的经历,浸透着青春时期默默的忧郁,但无疑散发出英语的吸引力:
「在母亲和父亲怀疑的眼光里,黄旭升开始给我教音标。在她给我教音标的时候,那种香甜的气息就从窗外飘然而入,使我的内心充满快乐。这种快乐也许是春天带给我的,也许是黄旭升带给我的。但快乐的确在充满我的内心,在那种时候,我忘了离我而去的阿吉泰,也许,这种快乐真的是英语带给我的。」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就和黄旭升念英语时一样。大家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默默地呼吸,孩子们的呼吸。我在这种氛围中从容地念着,英语的单词滋润着我的口滑,我的声音渐渐变大,我就像吉里在唱意大利歌剧一样地高声诵读着关于伟人的赞美诗。」
事实上,王刚除了写一种语言和它暗示的人性,他也直接写男女,从小孩到大人的性和情。他也没有把后者作为第二主题。这是后话。
刘爱从英语字典里学到的词有moon,house,bird,也有soul,grace,love,gentleman,change。还有一些和青春期有关他闻所未闻的词。就是在这样的学习里,当其他孩子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刘爱和他的年龄不相称地独自忧郁着。刘爱因为爱上了英语,和王亚军老师成了忘年交。书中并没有交代王老师为何而来到新疆,虽然,我们知道他的从小听祖父讲正宗的英语,他还喝咖啡,洒一点香水。英语代表了什么?刘爱并不十分清楚。英国和美国离的太远,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全中国一样,在挖着防备帝修反的原子弹和氢弹的防空洞,而且还是刘爱的母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设计的。英语的词汇和中国的字所传达的更是相差万里。就在和王老师的交往中,在新疆土生土长的刘爱窥见了不一样的世界,对英语的词也有了切身的理解。王刚的这本书,是一本小说。但他时不时地插入写作时的自己,隐约地说那是一部自传。当然,书的一部分是他的经历的叙述。王刚后来从新疆到了北京,天山外「口里人」的生活让他不习惯。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外省人」(一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人和外省人之区别)。王刚对于文明的落差有其敏感和认识,那是边疆和内地的差别。但他的独到之处是,他学过「英格力士」,而且感受过正宗「灵格风」英格力士的异域风情。他是这么记录改变了他的一生的王老师的:「王亚军没有留胡子。他一生都没有让胡子长出来,他总是干□、典雅,就像是一首巴洛克时代的乐曲,平衡而中性,他的谦和以及含蓄的微笑让我今天想来都伤心不已。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虽然有一点俗世关于上海人的痕迹,但毕竟不是全部。这说来复杂,也有点离题。我甚至为此还去翻阅了易中天先生的「读城记」,其中的「上海滩」一章,想看透其中的现代二字。于是,仍去读王亚军身在乌鲁木齐却向往着英语和英国绅士生活的心境,以及他对于刘爱的教导。我甚至有点庆幸,这些话是出自王刚,一个边疆人和北京人,而非我辈语言的伪军的身份,否则,说服力肯定一泻千里。书中是这么写的:
我的目光停留在靠着北墙的一个小书架,那上边有些英语课本,但是有一本很厚的,硬壳,墨蓝色的精装书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到跟前,想仔细看看。
他似乎意识到了我的目光,说:
「认识这个单词吗?字典。」我说:「英文字典?」
他点头。
我说:「是大字典?」他说:「这里面的单词如果你都会了,那你就可以像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那样,在那儿生活。你甚至可以超过他们那儿一般的人,因为你水平很高。」
文字,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是语言的记录和传承的工具。稍微进入深处,则知文字(言)是人类思想(意)的表达,而且有自己的生命和建构。日前读到《八方风来》(中华书局2008年)中,张隆溪教授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他在谈到其著作《道和逻各斯》时,讲述了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观念、思维和思维上的异同。语言(口语和文字)除了自身的魅力,就是探寻人类思维和认识的一道门径。中国人讲言义之辩和「文心」,从《庄子》轮扁和桓公的对话,到对于文字的讲究谓之「文心雕龙」,一直为文字和思维的关系着迷。西方语言的世界,古希腊有柏拉图的《哲学书简》(第七篇)谈语言的局限,近代有哲学和语言学的阐释学,乃至在流行文化里产生了奇幻小说如《墨心》(Inkheart),阅读出书页文字中的生命,穿越时空。因此,王刚从「英格力士」语言的角度入手,写一个时代的悲剧和人性的挣扎和向往,是充满睿智的一种思考,绝不是以写出一个异域的故事为满足。一个围绕对于一种语言的思考和追求的故事,表征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思想,则其起手之高,入笔之妙,称其及于文化探究的深处,似乎不是溢美之词。在刘爱渴求知识的年代,学校里传授的中文的表述是「毛主席万岁」,是「中南海的灯光哟,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底下写文章」。在简单的教室里,王亚军教的英语,暗示了有一个世界超越了蒙昧,人的行为、思想遵守不一样的规范。英格力士就如天山博格达峰溶化的雪水,淌到刘爱的心灵,在他心里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在此,故事是实实在在的,但其抽象的高度也超越了具体的情境。英语读书界的评论虽然无不看到了文字开启的人性,但把眼界仍然落到故事上,所以,作者在地域、汉族维族关系,以及文革背景上的省略,被视为一种遗憾。但是,当我们在言与义、言与道的关系上洞察语言的巨大张力的时候,就会觉得,用一个故事的标准看这部小说(虽然王刚还是把故事讲得颇为「折腾」的),实在是落到了第二义上面。
作者毫无阻隔地出入、转换于当时行动中的「我」(少年刘爱)的自述和现在回忆和写作的「我」(成年刘爱,其实即使作者自己的叙述)之间,乃至于我们难以分辨下面一段被称为「在那时的孩子几乎很难听见的充满古典情怀的话语」,到底是前者的自述还是后者的旁白。
英语老师王亚军的智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吗?不,不是,是从那本英语字典中来的(引者按:这里是模仿毛主席某段语录的口吻)。每个人说的话都是由词构成的,而英语词典里拥有无限的词汇,任何伟大的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这本词典里得来的,因为他们把这本词典里的词汇重新排列组合,所以词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跟圣经一样重要。
这话是谁说的?
英语老师王亚军。
这些「充满古典情怀的话语」,告诉我们,文字和词汇、伟人和思想,都源于词典。当然,这里指一本60年代流落在新疆的英语词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