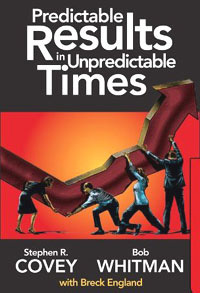敬爱的朋友们:
无数次,人们要求我讨论多杰雄登护法一事。在经过多番考量,以及获得我的上师们及护法的指示后,我认为这是谈谈这件事的时候了。然而,当我谈及关于多杰雄登护法的时候,我必须将多个阵营及不同的人们纳入考量之中:
于是不管我如何谈论这件事,总会有一些阵营高兴,另一些阵营不高兴,要两全其美实在不易。然而,我认为如果我发自内心、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述说我的看法,这是我尽我所能做好的事。我希望我能为这件事解开一些疑惑。
在这分成四个部分的视频中,我谈到了我如何接触多杰雄登,为什么修持和坚持下去,寺院、至尊嘉瓦尊者、我们的传承上师、我的上师、至尊赤江仁波切,以及我们如何能解决禁令问题。你也许会认同我的看法,也许不会。然而,我已经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能做的就是坦诚地表达自己、我的感受和我的修持。再怎么说,这是我的选择,然而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选择会在各方面影响许多人。因此我向来的做法就是根据知识、观察、历史和结果来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感谢参与这项制作、编辑、渲染输出、听写、翻译和筹资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许多人付出资源、资金、时间和真心在这个项目上,他们都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你们都秉承良好的发心完成了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感谢你们的努力、付出、慈悲和关怀。我深深地珍惜大家。
对于观看这些视频的朋友,感谢你投入时间、关注和想法。我希望我在视频上的分享能能协助解决多杰雄登禁令的争议。我真诚希望更多人对这个情况能有更好的了解,给每个关注此事的人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詹杜固仁波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视频文字本请往下看
![[转载]《多杰雄登:我这方面的说法》(上)](http://img.aihuau.com/images/02111102/02021346t01d80ef4cbc7f50a1a.jpg)
看点:遇见首个上师——堪殊洛桑塔庆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Fd3dRo35Tw/
看点:遇见第二个上师——格西簇亲格而辛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iofecyl0qM/看点:遇见第三个上师——嘉杰宋仁波切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cFhKRccHKI/看点:嘉杰宋仁波切赐予多杰雄登之修持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Rb0DJzLNQY/
完整视频(一): http://bit.ly/1GQOxVD
内容摘要
看点:绝不可能违背对上师的承诺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_0OJst3oqM/
看点:宋仁波切毕生都修多杰雄登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UyZm7N7Pzw/
看点:因修雄登,前世的嘉杰赤江金刚持甚至不是僧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GVe3Z_zzNs/
看点:无有极限的证悟之心相续——文殊菩萨与多杰雄登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AqKCVpbLv0/
完整视频(二):http://bit.ly/1APLo6E
内容摘要
看点:为何詹杜固活佛要谈论多杰雄登护法一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QPHpt4rCis
看点:多杰雄登的修持无有宗派主义色彩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0yXy0PhnM4
看点:詹杜固活佛的一生为佛法而存在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TEVZo4W3p8
完整视频(三):http://bit.ly/1KyQida
内容摘要
看点:何不直接“降伏”多杰雄登?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4ch4f-axvA/
看点:多杰雄登是文殊菩萨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nAOJbNVdC4/
看点:高僧无法降伏邪灵?不可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MTVT0GVs_k/
看点:给世界其他多杰雄登修持者的话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rCTnAN8cJk/
完整视频(四):http://bit.ly/1E0ZIJw
内容摘要
———————————————————————————————————————————
视频文字本(第一部分)
大家好
今天我在这里,想跟我全球各地的好友、支持者、僧众、我的上师们和那些想了解更多的中立人士谈谈世界和平护法嘉钦多杰雄登。我想跟大家解释我跟这位护法的关系。我跟大家讲解这位护法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改变你的信仰,也不是要你跟我站在同一阵线或企图以任何方式去让你想个中的好坏。在过去的10年、15年、20年,我收到成千上万关于多杰雄登护法的询问。我收到的问题,有些来自多杰雄登修持者,有些来自不修持多杰雄登的人,而有些人甚至不喜欢多杰雄登。这些问题越堆积越多,我想我必须针对某些问题做些解释。我今晚无法针对所有问题一一作答,但我会尽量回答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是克切拉佛教中心的精神导师,也是创始人。我跟几位很亲近和努力的弟子——佛法弟子,内在旅程的弟子——共同创办的克切拉佛教中心,今天已经发展成稍具规模和成功的中心(若可以那么说),那是克切拉每一个人努力的成果。那种凝聚力与和谐,基本上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内在世界,若可以也包括外在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居处。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
我首先要谈的是我跟多杰雄登的关系,它如何开始和我跟祂的缘分。现在,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的背景。我想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但我会为新人稍作讲解。我的生父是西藏哲蚌洛色林寺的前僧人。我的生母则是新疆皇室的后裔,属于当地主要的蒙古部族——土尔扈特族皇室。她的母亲,即我的外祖母,以及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曾经是当地许多代的统治者家族。我的父亲则从西藏前去台湾。我母亲离开新疆后到西藏,再辗转来到台湾。我父亲刚到台湾时,并没带上自己的妻子和三名孩子。他在那儿的时候,遇上了我的母亲。她当时还是少女,敏感脆弱,且因皇室公主身份而饱受周围族人评头论足。在监视下,她的一举一动,无论是走路、谈话、衣着打扮都必须符合她的身份。
她在台湾遇见了我的父亲,我猜他们堕入爱河,而她怀孕了。在她怀孕时,我父亲告诉她自己在西藏已有妻室。这给她们的社区带来了很大困扰、问题和难题,因为在台北的蒙古和西藏社区相当庞大。在我外祖母和母亲那方家庭的建议下,一切都低调进行。我母亲在台北综合医院静静地生下了我。她生下我之后,从不曾接纳或承认我,我也不曾成为她家中的一份子。她联络了一些台湾当地人,每个月付费让他们看顾我。她并没真的抛弃我,但她不能把我留在她身边,因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单身女人未婚先孕并不是一件能被人接受的事。我生于1965年。
我并不是要批评我母亲或父亲的对与错。我并不是要批判任何人的做法。我只是如实说明当时的情况。话说回来,我被当地一个家庭看顾,我也记得外祖母偶尔会前来探望我。我现在知道她是我外祖母,但那时的我当然不知道。我母亲后来相隔很久之后才告诉我,当我7个月大,未满一周岁时,有一群喇嘛、僧人和上师前往她家里,告诉她说我已被正式认证为一位西藏喇嘛的转世。当我向母亲询问关于这名转世者的身份,当时的谈话内容,搜寻队的名字时,她说事隔太久,她记不起了。然而,她却告诉我,他们的确在我7个月大时前来认证我,我估计他们是想把我带回寺院参加坐床仪式。我母亲不允许这件事发生,原因是若你在寺院参加坐床典礼,你就必须说出母亲和父亲的名字,而在当时说出这孩子家人的名字,对这个家庭而言并不是个愉快的经历。因此,她把我留在那里,认证工作也无法完成。最后大约在我6岁多7岁时,我就从台湾被带到美国去。
我记得外祖母带我乘坐泛美航空班机,这航空公司目前已不存在,但当时依然存在。我抵达纽约时,跟外祖母一起被带到母亲家里过一夜。第二天一对土尔扈特族的蒙古夫妇开车从新泽西上来,把我带上了一辆白色福特大轿车。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她从不曾告诉我她是我母亲,但她告诉我那就是我的父母,我必须跟他们一起离开。6岁的我只能答应,我曾以为自己的父母在台湾,但遇上了这些人,我也只好跟他们一起走。我被美国的一对蒙古卡尔梅克族夫妇领养,住在新泽西州豪威尔市。那时我大约六七岁。
我的养父母布尔查和妲娜布珈雅。
当地的卡尔梅克社群很有趣。卡尔梅克族源自新疆,他们曾经征服欧洲和俄罗斯等。你也知道,蒙古人曾占领许多地区。部分人回到新疆、蒙古,部分继续留在卡尔梅克地区。我的家庭有一部分源自位于俄罗斯西部的卡尔梅克地区,现在那里已经是共和国。一部分来自新疆。事实上,我在这两个地方,依然还有血缘亲戚。二战时期,俄罗斯爆发革命,卡尔梅克举国动荡不安,发生很多问题和困难,人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国家。卡尔梅克人离开卡尔梅克共和国,前往美国。这些勤奋、美丽的卡尔梅克人原是蒙古人。卡尔梅克族其实就像中国人可分成广东人、福建人等一样,分别来自不同省份。卡尔梅克人只是蒙古族的其中一个支系。蒙古族可分为75个支系。他们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前往美国,努力工作,把本身的文化、宗教(西藏佛教)、食物、传统等也一拼带过去。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纽约和新泽西三州地区定居。领养我的卡尔梅克人居住在新泽西。新泽西共有三所卡尔梅克佛教寺院,分别是尼赞寺、拉昔甘巴林寺和扎什伦布寺。这三间卡尔梅克寺院都有自己的蒙古-卡尔梅克族的僧人和格西。有者在伟大的西藏哲蚌寺接受教育。另外,在新泽西北部还有一所美丽庄严的蒙古卡尔梅克寺院,由格西旺杰管理。
我住在新泽西州的豪威尔市,这是一个 难以形容的美丽小城。我住在那里的卡尔梅克社区,一直到十五六岁。你要记得,我有一半的血缘是蒙古人,具体一些就是卡尔梅克人。另一半血缘是西藏人。我父亲是西藏人,母亲是蒙古人。然而,这两个文化都修持西藏佛教。所以,在我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宗教冲突。我住在西三街养父母的家。他们的名字是布尔查•布珈雅和妲娜•布珈雅。他们尽量给我一切最好的,用他们所知道的方式来爱我,给我他们所能给的。重点是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要我成为他们希望我成为的人,就像多数父母一样。
在新泽西豪威尔市成长。
我于1972年抵达美国。住家附近的拉昔甘巴林是我父母祈祷供佛的地方,那儿充满了卡尔梅克人。1971年,那儿迎来了西藏佛教界最伟大的上师之一,他同时也是至尊帕绷喀金刚持的心子。那是因为当地的蒙古社群想要一位伟大的上师和僧人,于是写信要求,结果就请来了这位伟大的上师。这位伟大的上师后来成了色拉昧寺的住持。他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作者和上师,在新泽西州豪威尔市平静地生活,安详地圆寂。嘉瓦尊者很喜欢他。
这位伟大的上师就是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 藏名一般很长,为了方便起见,我会直接称呼堪殊洛桑达庆。他是一位高级学者,也是显、密大师。不仅如此,他还是少数能将自己从西藏色拉寺所学的一切付诸实践的人。
卡尔梅克社群邀请、请求并确定了这位大师即将成为新泽西州豪威尔市拉昔甘巴林的驻寺上师。你能想象吗,他在1971年抵达,我在1972年抵达,当时我大约6到7岁。更巧的是,我住在西三街,寺院好像在东六街,大约只是两三道街的距离。我骑单车到寺院耗时约七八分钟。我骑得很快,寺院也很近。慢速骑单车大约需时10分钟,而步行则是15到20分钟时间。在10分钟单车路程之外,就住着本世纪最伟大的上师之一,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他授课、讲解,他带领禅定闭关,授予灌顶、口传……你必须明白,他是那种能够制造许多学者的学者。可说是其中一位最高级的学者。他也是至尊赤江仁波切、至尊宋仁波切、至尊帕绷喀仁波切的直接弟子。在西藏时,他服侍这些上师,从他们那里接受教诲和传承。他是一位十分纯净的僧人,非常仁慈、乐于助人,他透过不停地教授佛法,将一生奉献于服务他人。
我就住在离这位大师10分钟之外的地方,说是好运嘛,这已不单纯能用好运来形容了。我觉得自己前世一定许了很好的愿,才能如此近距离接触那么伟大的上师,基本上就只是隔一条街而已。年幼的我一看到这位大师,立刻就着迷了。即便只是6、7、8、9岁,我清楚记得自己对他充满敬畏。没有人告诉我他有多伟大,谁会告诉一个小孩他有多伟大呢?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多么伟大的学者,多么伟大的大师,多么了不起的禅修老师,没有人这么说,没有人会对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说这些。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与众不同,我想跟随他。我小小的心灵这么告诉自己,我想要跟随他。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开始参加他的课,参加他的开示,参与他的闭关,参与他的禅修。我变得越来越参与和投入。
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是我的第一位上师。
格西拉教了我们些什么呢?对不起,是堪殊仁波切。当时我们都称他为格西拉,因为他还没当上住持。堪殊仁波切那时教了我们一些什么呢?他专注于讲授《朗讲》修心法门。他要我们学习法称大师的教诲和辩论。他要我们学习《菩提道次第》。他专注传授胜乐金刚和金刚瑜伽母密续法门。他着重守戒。他专注于正确的禅定和仪式。他并没教授什么魔术、戏法,所教授的都是直截了当,清晰易懂的佛法教诲,我参与这些课程好几年。约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经跟随这位大师学习了好几年。这令我父母感到惊愕……因为他们领养我作为他们的独子,让我长大后继承他们的名字,然后结婚,生下许多孩子。这是蒙古父母对孩子们的期望,而我的心愿却是出家为僧。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家。他们一点儿都不高兴,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我十二三岁时,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邀请了他的侄儿前来帮忙打理寺院。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邀请的这位侄儿,若我没记错,他的名字是洛塔。仁波切邀请他从色拉寺前来。他抵达后住在我们的寺院内。我刚记起洛塔曾经在那里。洛塔不会说英语,但他常常笑,常常微笑,是个很平易近人、很快乐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僧人,他的任务是照顾堪殊仁波切,他的叔父和大师,以及看顾寺院。洛塔在那里待了好几年。
我曾到寺院去,因为我不能时常见到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而且洛桑达庆仁波切总是很严肃、坚定,我有点怕他,但我曾常去那里修剪草坪、施肥、洗碗碟、扫地、打扫寺院,能做的我都做,因为你必须明白,我真的很喜欢寺院。我真的很喜欢堪殊仁波切,我真的很想接近他、服侍他,我其实想搬到寺院住,但我不敢把这种想法告诉我父母。
我真正想要的是搬进寺院,穿上僧袍,住在那里服侍堪殊仁波切和学习。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作为替代,我只好尽可能常到那里去服侍。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到寺院服务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有机会看堪殊仁波切一眼,或被他叫过去传授我一些特别教诲。通常他会叫我吃了馍馍就回家。我的秘密心愿,就是跟堪殊仁波切偶遇,并得到他的特殊教诲。那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特别,而是我真的很爱他,至今依然。一对一的特别教诲从来都不曾发生,我还曾经被他严厉地瞪过。他曾经严厉地瞪着我,而我则这样回望。
我是个早熟,有点顽皮的孩子,也许这就是他瞪我的原因。无论如何,洛塔和我成了朋友,他是堪殊仁波切的侄儿。洛塔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到寺院去,尤其是在夏天。我只是在那里逗留,在那里祈愿,帮助他们打扫,跟他们开玩笑等。洛塔要我教他英语。我教了他简单的英语,如ABC之类的。
一天,洛塔在楼下清理厨房,我很早熟,对什么都感兴趣,还好管闲事。我是那种你越是叫我不要碰什么,我就越会确保自己非得连碰两次不可的人。所以,当洛塔在楼下清理厨房时,他叫我在那里等着,我当然没听。他叫我别到他房里,或别上楼去,因为堪殊仁波切的房间就在那儿,而他的房间则在隔壁等之类的话。当然,我不敢到堪殊仁波切的房里去,我就是不敢。我潜到楼上他房里,想知道僧人的房间长什么样子,僧人拥有些什么,抽屉里会放些什么,衣柜里放什么,床上放什么,床底有什么,他用什么样的床等,因为我真的很想当僧人。我对僧人的生活作息很感兴趣。
所以我潜到他房里。洛塔在楼下哼着歌曲,洗着碗碟,我听不到他的动静。猜我做了什么?我打开所有东西,看看有些什么。那里有他的僧袍、念珠、僧人物品、床等。我打开衣柜。美国人有一种开放式衣柜,当我打开衣柜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那里头是空的,上面有个小架子,上面放着一幅黑白照。黑白照前有一杯茶。而黑白照上有个像这样的东西。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正当我伸出手去拿照片,想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并记得它,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但正当我刚拿到照片时,洛塔走了进来,从我手中夺回照片,连声说“不,不,不……这不是给你的!”。我问:“为什么不行?这是什么照片?”他说:“那不是给你的。”我问:“你能告诉我祂的名字吗?”“不是给你的!”“那是谁?”“不是给你的!”“为什么把祂单独放在衣柜里,还放了一杯茶?”“不是给你的!”那是他的答案。我想那是他唯一能说的,因为他的英语不好。“不是给你的!他把照片和茶杯都放回原处。我把茶溅出了一些。他把衣柜关了起来。我打开,他又关起来。我说:“我想看。”他说:“不行!”几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多杰雄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多杰雄登。我的第一个邂逅。
后来家里变得不安宁。我父母对于我想要出家,待在寺院,参与更多佛法这件事极度不满。他们非常不高兴。他们开始给我的上师制造很多问题。事实上,他们尝试把他遣走。我不知道他们怎会变成这样,但他们真的是如此。所幸他们并没成功,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让他从我生命中消失。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跟父母之间面对很多问题。他们要我读书,他们会处罚我,有时候打我,有时惩罚我,有时对我吼叫。有时候,父亲会在我正在寺院聆听开示时突然走进来,让我尴尬。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年,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里,沿路搭便车从新泽西州的豪威尔到纽约,从纽约市,我再搭便车横跨美国大陆到洛杉矶。我的原意是到夏威夷,但我没有钱买船票,更别说是飞机票了,所以我最后留在洛杉矶。抵达洛杉矶之后,我在一个表亲家里住了几个月,同时也在找寻一家佛教中心。后来我到一家从事东方研究的大学,在那里遇见了善心的利奥•普鲁登教授。你必须明白,我在洛杉矶到处走着,在黄页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或谷歌)我找到了东方研究大学。我心想:东方、佛陀、西藏,三者之间必然有关系。我年少的心叫我到那儿去。我那时15岁,快进入16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找到那地方,我找到了地址,问了方向,就走到东方研究大学。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抵达那里。我抵达时就直接找利奥•普鲁登教授,告诉他我是一个蒙古男孩,我想找一个有佛像的佛坛,我只想坐在佛坛前祈愿、禅修和念诵心咒。
他说“孩子,你找错地方了。这是所大学,这里没有佛坛,但我可以带你到一个有佛坛的地方。”我说:“真的吗?”于是利奥•普鲁登教授出于好意,用车子把我载到约20分钟车程外,地址为洛杉矶市St.Andrew’sPlace 135号的地方。那是一栋难以形容的别墅。外表看起来只是一间别墅,但当我跟利奥•普鲁登教授走进去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什么?整个起居室都被改成一所佛教中心了。每一面墙上都挂着唐卡。地毯有点……呃……如果我没记错……西藏地毯被铺在木板上。到处都整齐地叠着供人禅坐的垫子。还有一个佛坛和嘉瓦尊者的法座。佛坛上有宗喀巴大师、佛陀和度母像等。在佛坛下方的地上,阳光透过黄色的窗帘,照射在格西拉身上。那是来自甘丹萨济寺的格西簇亲格而辛。
格西拉是甘丹寺的伟大学者和伟大修持者。他是至尊宋仁波切和至尊赤江仁波切的弟子。我走了进去,你能想象吗?我当时15岁,一个小时前遇见了利奥•普鲁登教授,他把我载到St.Andrew’sPlace135号。我走进去,角落有一位西藏喇嘛正在禅坐,旁边有宗喀巴大师像,还有一道光照射在他身上。我走了进去,利奥•普鲁登教授把我介绍给格西拉。我告诉格西拉我的历史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告诉他我如何到洛杉矶来和为何而来,格西拉对我说:“噢,那很好。”他说:“今天是荟供日,藏历是这个月份的第十天,我们晚上将举办荟供。”我的反应是“哗!”“你不如今晚过来吧!”我答应了。我十分兴奋。我在洛杉矶独自一个人,15岁快跨入16岁;我享有自由,找到了佛法大师,父母再也不能约束我。我一个人了。我刚走进来遇见了这位大师。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况且他还是赤江仁波切和宋仁波切的弟子。
这所房子曾是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的所在地,他们后来搬迁到更宽阔的地点。
我在市内到处走,身上没钱,只能用走的,偶尔在车站逗留。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车站,因为那是免费的。我喝了一些饮料,准备参加荟供。然后,我走回佛教中心参加荟供。在新泽西,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进行这些仪式,譬如如何使用金刚杵、金刚铃,如何结手印和念诵经文。格西拉要我坐在前排,那地方挤满了约六七十名弟子。我们一起进行上师荟供。后来他们就很好奇地问:“哗,你才15岁,你从哪里学会做这些?你怎么学会念诵?你怎么会做法会和荟供等?”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事,因为在新泽西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是。无论如何,后来格西拉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告诉每个人我的情况等。那儿一些善心的委员。
其中一位委员同情我,说服其他委员会成员降低别墅楼下那间房的房租。你能想象160美元一个月的房租吗?在西方国家的佛教中心,你必须付费。你不会领取薪水,也没有生活津贴。你不会有免费住房,不会有礼物等任何东西。每个人都很穷。你要到中心去就必须付钱,要参加课程也必须付钱。这是那里惯常的做法,因为人们必须付账单。她成功把房租降到160美元。听好,这里有四间楼上的房间,有一个图书馆、一个起居室,一个厨房,楼下接近冲凉房入口,还有一间小工人房。那间楼下靠近冲凉房的小房,大约有8尺乘10尺大小,我得到的就是这间房。他们跟委员会讨论,允许我住在那儿。他们让我住那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搬到佛教中心,只带了两个袋子。我的家当不多。我搬到佛教中心去,住在楼下。墙的后方就是我们祈祷的大殿。大殿内有宗喀巴大师像和法座。每个星期天,格西簇亲格而辛就在这里讲课。我只需起床,梳头,走进去,就能参加《菩提道次第》课了!你相信吗?我参加《菩提道次第》课程啊!
每一天,我都有幸能清理格西拉的房间,为他送茶10至12次,格西拉很喜欢喝茶;我为他洗衣,打扫大殿;我有幸为格西拉煮饭,帮他买东西,打理整所房子,因为跟格西拉同住在楼上的一两名弟子都需要出外工作。我也有工作,但我只是兼职工作。我在这所位于St. Andrews Place,135号名为图登达杰林的佛教中心,跟一位伟大的活佛格西簇亲格而辛同住,你能相信吗?
但我有点小障碍。在《事师五十颂》里提到,若你已经有了一位上师,就无需找寻另一位上师,跟另一位上师学习或跟另一位上师一起。忠心跟随一位上师就好了。
因此,我不能从他那儿接受教诲,因为我在新泽西已经有了一位我敬爱和珍惜的上师,我们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换新上师的唯一情况,就是当你的上师叫你去跟某位上师学习的时候,或者当你所学的已经足够,已经可以在上师的允许下离开了。于是我打了电话。当时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我致电给新泽西的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告诉他我为什么离家出走(他知道),目前身在何处。我告诉他我在洛杉矶格西簇亲格而辛的住处,并请求他让我跟格西拉学习。如果新泽西的堪殊仁波切反对,我会立刻搬出来。他是我的上师,我必须听从他。我需要他的同意,因为在西藏佛教里,如果你没得到上师的同意,就不能跟随另一位上师学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视频文字本(第二部分)
马鸣大师所著的《事师五十颂》里说得很清楚,没有上师的同意,你不该向另一位上师寻求教诲、灌顶,甚至加持。为什么?当你找寻另一位上师,或从一位上师换到另一位上师的时候,你就是在告诉全世界,你的上师不够好,你上师的加持并不足够,你上师的学识不足,你上师不够好,所以你必须另外再找个上师。你们当中也许有人会说:“哦,我只不过想得到另一位上师的加持。”既然你的上师已经赐予你加持,你为什么还需要另一位上师的加持呢?所以根据《事师五十颂》,基于几个原因,你不能随意更换上师。一是当你已经跟上师建立关系,向他学习之后,你上师所拥有的,就是其中一个证悟之道,这对你而言应该已经足够。
若你想要从2位、3位、4位,甚至5、6位上师那儿接受教诲,你怎能修持每一位上师给予你的教诲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其一。其二,当你接受了一位上师,你就把他们视为证悟能量、证悟知识和证悟心识的体现。所以,那位上师教导你的,只要你加以实践,就能取得成就。当你获得成就时,你其实跟那些向其他上师学习而取得成就的任何一个人是一样的。因此,你无需跟随许多上师。我对上师依止修持的要求十分严格。我一直都十分严格。所以,我抵达洛杉矶时,我知道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我并没得到第一位上师的允许。为什么我会从第一位上师换到第二位上师?因为我父母不允许我学习。他们不允许我到寺院去,所以我必须离开。他们要我结婚、考取学位、拥有孩子、参加派对、喝酒、取乐。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我父母甚至挑选了一位蒙古卡尔梅克女孩,作为我日后结婚的对象。双方家长已经讨论过了。这是他们做事情的方式,所以我只能离开。我想出家为僧。
我的第二位上师,伟大的格西簇亲格而辛。
我在洛杉矶格西拉的家里,在格西拉的允许下致电给新泽西的堪殊仁波切,向他解释整个情况。当然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能够谅解。他听说我离家出走。他很高兴听到我安全无恙。我告诉他:“我短期内都不能回到新泽西,因此没机会跟您学习,尽管我很想那么做。我目前住在格西簇亲格而辛那儿,我能否征求你的同意向他学习,又或者我该怎么做?” 堪殊仁波切在线的另一端。如果他叫我离开,我肯定会马上收拾离开。我绝不会质疑我的上师。我没有对上师表现不敬的习惯。然而,堪殊仁波切对我这么说:“你非常幸运,格西簇亲格而辛是一位伟大的大师和学者。你必须如同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你必须服侍他,向他学习,成为一位好弟子”。
哗!当时我头脑立刻浮现几个想法。第一,佛法大师们真的没有妒忌心。佛教大师们真的不在乎你如何取得证悟,或在那一位大师的指导下取得证悟,他们只要你取得证悟。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我的上师们有多么的伟大。你也许会问,我怎么可以说是第一次呢?我现在说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他正式同意了让我跟格西簇亲格而辛学习。所以,我即使跟格西簇亲格而辛学习,也不会引来因为换上师、换中心所引起的业果。.第三,他告诉我格西簇亲格而辛是个伟大的上师。若我的上师告诉我,他是一位伟大的上师,我就无需再检查,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师。他也要我像在新泽西服侍他那样来侍候新的上师。我当时悲喜交集,悲是因为我爱我在新泽西的上师。喜则是因为我虽然不能在那里,却可以继续学习。更巧的是,他们属于同一传承、同一上师、同一传统。他们都属于宗喀巴大师传承,都是赤江仁波切和宋仁波切的弟子,而且他们俩都是备受敬重的格西。
于是我将电话放下,并向着电话顶礼,因为我的上师刚在电话上跟我说话。为了表示尊敬,我对上师顶礼。接着,我跑上楼去向格西拉转述堪殊仁波切的话。格西拉只是说:“好,帮我弄杯酥油茶。”我答应了,心想为什么没有人为我感到开心,但我意识到格西拉的另一项特质,他并没有我执。当我告诉他堪殊仁波切对他的评语时,他没有我执,并没有进一步谈论此事,只是说:“好,帮我弄杯酥油茶。”我很惊讶,这位上师并没有我执。我刚转告他另一位上师称赞他的话,他却不为所动,也没问细节。所以,当我为他准备茶的时候,我思考着这两位上师的特质,没有我执。
所以,我透过两种方式成为格西簇亲格而辛的弟子。第一,我取得了第一位上师的同意,因为我已不能再向他学习。第二,格西簇亲格而辛接受了我。
在纯然的喜悦中,我已经生活了16年,我已经16岁了。从15岁到16岁、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我跟格西拉住在一起,直到我接近23岁,动身前往印度之前。其中有一年,我曾为了体验生命而搬到好莱坞西部,随后又搬回来。所以,在洛杉矶的七八年间的其中一年,我曾经搬到洛杉矶西部接近日落大道的地方居住,体会了一年的娑婆生活,然后再搬回去。当我在佛教中心居住时,我每周都从格西拉那儿接受教诲。我许多时候有幸能为他煮食,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还为他洗衣,因为洗衣间就在我房间隔壁。我打扫、吸尘、清洗、购物,我什么都做。我并没获取任何酬劳,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服侍我的上师。
于我而言,服侍上师是不该领取酬劳的,而且对上师有诚信是十分重要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只要我答应了上师的事,就无需他来提醒我、催促我或向我提起这件事。我一旦对上师许下了承诺,我就会坚守至死亡为止。这是我自小被灌输的观念,这是我相信的事,这是来自佛法书籍的教诲。
如果你对上师——这位教授你佛法以取得证悟的崇高生命——都没有诚信,那就表示你对任何人都不会有诚信。若你能丢弃一颗钻石,你必然也能丢弃玻璃和水晶。有什么人会抛弃钻石,把水晶和玻璃留在家里,还不断保养照顾,并将玻璃镶成戒指呢?你怎会丢弃钻石而保留玻璃呢?由此可见,若你不照顾一颗钻石,你就不会照顾一块玻璃。于我而言,上师就是钻石,我会好好照顾它。
我年少时答应过上师的一切,我都会一直坚守着:保持诚信,不让上师催促你、提醒你,不把问题丢给上师和不扰乱上师的心,这是上师给予我的教诲。绝不对上师大声吼叫,打断他的话,做让他不喜欢的事,不跟他说话或表示任何不敬。因为你的上师是教授你佛法的人,你的上师是指导你证悟之道的人,因为你无法亲见佛陀。我无法遇见佛陀,无法遇见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或度母。我无法从祂们那儿接受教诲,但祂们必然存在且已经证悟。
既然祂们存在,且已经证悟,祂们从祂们的上师那儿接受教诲,但我无法从祂们那儿接受教诲,因为我没有在这时候看见祂们的福报。既然我没有在这时候亲见祂们的福报,我只能依赖神圣的上师们来给予我教诲。
既然上师们给予我教诲,他们就是佛陀的替身,或是正在行动中的佛。如果我对行动中的佛或我的上师们不敬,如果我欺骗,不守承诺,如果我对他们吼叫或待他们无礼,或我时常想要得到他们的关注、金钱或其他东西,他们就不是我的上师。我对待他们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对待富有的父母一样。这对我的修行怎会有帮助呢?
我们跟上师之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驯服我们的心识。我们跟上师之间的每一种关系,上师教授我们的每一件事,上师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一位具格上师,他的用意是训练我们的心识,让我们具备想要修行有成所应拥有的特质。如果我们无法对上师拥有诚信,无法对上师信受承诺,在学习和实践上无法跟上上师的进度,那就表示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对什么人都会持有同样的态度,因为我们不珍惜任何东西。
我很高兴自己能向格西簇亲格而辛学习。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开心。人生中第一次,在16岁那年,我是自由的,没有父母,我兼职工作养活自己。我住在佛教中心。我住在底层,而楼上则是一位来自拥有纯正传承和修持的甘丹萨济寺的伟大上师。我参加《菩提道次第》课程、密续课程和朵玛课程。我能够服侍我的上师,就像密勒日巴一样。我为上师煮饭、洗衣、打扫、购物;当他外出时,我有时还有幸能伴随他、护送他,甚至为他提袋。我喜欢跟他外出,帮他提袋子,因为我会想象自己是他的助手,看我!我知道这有点自我。我很骄傲,我对自己能够跟着格西拉到处走感到很骄傲。我爱跟他逛街购物。有时候我们会到处逛,因为我喜欢看他如何跟他人互动。我看到他如何跟中心的弟子们互动,我看到他如何跟巴士上、商店里、柜台前、餐馆内的人互动。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善。我很喜欢这样,因为我并不期待其他的。
我曾在这家洗衣店兼职。这只是我在洛杉矶工作过的许多地方之一。
他有许多弟子,一天当我正要去参加荟供时,我遇到了格西拉的其中一位弟子,他给我看一张至尊宋仁波切的照片。哗,我难以置信!我不曾在任何地方见过或听过这位喇嘛,我怎可能见过呢?我看到宋仁波切的一张照片,其中一名弟子告诉我说,他们都相信他是胜乐金刚的化身。我看了那张照片,就恳求那个人送给我,他给了。我把照片放在我的佛坛上,自己也难以置信。我全身仿佛有股电流通过。我很兴奋、很感动,我无法形容自己看到宋仁波切照片时的心情。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格西拉的上师,格西簇亲格而辛的上师。我不禁“哇”了一声。你猜怎么着?我得到那张照片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宣布至尊宋仁波切即将访问我们的中心长达6个月的消息。你无法相信我的感觉!你无法相信我有多么喜悦和兴奋。
我想要跟这位上师结缘,我想要跟他结下很深的缘,所以我跟年少的自己说,我想做大礼拜供养。我将至尊宋仁波切的照片供在佛坛上,每天对着他行一百个大跪拜。连续几个月,直至他到来为止。我的目的是以身、语、意作顶礼,因为我没有钱,于是就供养身、语、意。我每天都供香给宋仁波切并祈愿:“愿我能跟您建立很深的缘分,愿我能从您身上接受教诲,愿我证得如您的成就,愿我接受您的传承。”我曾经每天都这么祈愿,并向他顶礼。
几个月后,这个大日子终于到来了。然而,我必须上班,这让我感到很沮丧,因为至尊宋仁波切抵达的时刻,我正在上班。我想在门口迎接他。我一面工作一面感到兴奋。下班后——我做的是兼职工作——我跑回中心,发现到处都是行李袋和新鞋子。我知道他到了。
我听到楼上传来陌生的声音,不是让人不舒服的那种,但就是陌生的声音,我说:“哦,天,那肯定是他。”我在颤抖。我在楼下的厨房假装显得忙碌。我哀求他们带我上楼。我一面等待、希望和祈祷,一面感到害怕。最后,格西拉说:“好,你可以上楼见宋仁波切了。”我“噢”了一声,很紧张地上楼去,心里很害怕。我走向他,他坐在那儿,身体挺直,哇,我知道那长着白山羊胡子,眼神锐利,没有笑容的人就是他。他由始至终没对我微笑。
我走了进去,不敢看他,不敢直视他的脸。我很紧张、害怕、兴奋、敬畏、恍惚。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但我知道我正面对一位佛。我向他行了三个大礼拜,这样看着他,往上往下看……我好奇心旺盛,会打开别人的衣柜,发现一位护法……我就是那种孩子。我很害怕,但我还是要看。
接着,我开始禁不住哭了起来,自己也不明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我只是不断地哭泣,而宋仁波切坐在那儿看着我……不为所动,没有情绪。他要格西拉告诉我:“我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你无需哭泣。”“现在你可以叫他出去了。”于是我就被请了出去。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离开他的房间。我告诉格西拉,我的表现并不好。他说:“不,你没做错什么。”于是我到楼下开始准备晚餐和茶等,因为跟随宋仁波切前来的随从很多。
所以,我每天都为宋仁波切、其助手、格西簇亲格而辛、两名功德主、翻译员、翻译员的叔父共7个人准备食物,长达6个月。我负责煮早餐和晚餐,午餐由另一个人负责。
日子久了,宋仁波切开始喜欢我。我给他送上食物后,就立刻离开房间,因为我不希望被他赶出去,我很害怕。所以我会走进去,敲门,把食物放在前面,等半个小时,然后上楼取回托盘并祈祷。我很狡猾,我会多准备一些食物,以确保有一些剩余的,那我就可以在把它端下去之后,吃他吃剩的食物。因为我读过,吃上师吃剩的食物是个很好的加持。我曾经为他准备多一些食物,就是想确保有剩下的食物。我听到有人埋怨说你煮太多了,所以有剩余的食物,我说我知道。有时候,若没有剩余的食物,我就会吃残余的食物屑。我把它放在头上,然后吃了它,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位佛。
我开始跟他变得很亲近,我甚至可以走入他房间,坐在地上,为他按摩脚部,有时是头部、手部;或者在他禅修时,坐在他身边;有时当宋仁波切小睡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我就这样看着他,因为我无法想象他竟是一位那么伟大的喇嘛。格西拉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他说:“你把我的上师服侍得很好。”
我有幸在宋仁波切访问洛杉矶期间侍候他。
那时候,我一般都持诵文殊、观自在菩萨心咒和做一些简单的修持,以及格西拉教授我的《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我也持诵吉祥天母心咒。我很喜欢吉祥天母:“JO RAMO JO RAMO JO JO RAMO TUNJO KALA RACHENMO RAMO AJADAJA TUNJO RULU RULU HUNG JO HUNG”。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就不断持诵祂的心咒,且时时刻刻都那么做。
我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必须有一个护法神。有一天,我跟至尊宋仁波切和他的助手在他楼上的房里时,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透过助手问宋仁波切:“我该修什么?”意思是,我该如何修持?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让我先提一提更早前的事。
吉祥天母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位佛教护法。
宋仁波切到来之前,格西簇亲格而辛每个月都会在图登达杰林举办一场多杰雄登酬供和金甲衣护法酬供。.格西簇亲格而辛每个月都会跟五六十名弟子一起进行金甲衣护法和多杰雄登酬供。为什么会这样?金甲衣护法是甘丹萨济寺的护法,多杰雄登护法则是其中一个守护格鲁修持的护法,也是格西拉的个人护法。格西拉从他的上师那儿接受了多杰雄登托命灌顶,他每个月都进行法会。接受托命灌顶的其中一项承诺就是每个月必须进行多杰雄登法会。格西拉传授我们多杰雄登修持,他讲解多杰雄登法门,鼓励我们参与多杰雄登修持,他详细解释关于多杰雄登的一切。
事实上,格西拉给予我们的教诲,乃取自赤江仁波切编撰的《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这本由赤江仁波切撰写的书,包含了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传承、背景、仪式、禅修、心咒、火供等。这册书由至尊赤江仁波切编撰,格西拉拥有一份,并把它当成给我们上课的教材。格西拉为我们讲述多杰雄登的历史、来源,祂如何崛起,祂的修持和好处等。格西拉教授我们这一切,并鼓励我们修持。每一个月,格西拉都会举办多杰雄登和金甲衣护法法会。七八年来,我每个月都会在那里,不曾缺席。
当宋仁波切到来时,我已经透过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的助手和侄儿洛塔接触了多杰雄登,后来我发现新泽西的堪殊仁波切每个月也都会修持多杰雄登。在新泽西的拉昔甘巴林,我接触了这位护法。后来在加州洛杉矶,我在格西簇亲格而辛的影响下,再度接触这位护法。他给予我们教诲,鼓励这项修持,在他的佛教中心举办法会。他是我的上师,所以我跟着做。你就只是跟着做。如果你的上师说祂已经证悟,祂就是证悟的。所以,当宋仁波切到来时,我已经做着多杰雄登修持,不算大量,只是少量修持;我也在持诵吉祥天母心咒,但我并不想拥有太多护法,因为我想那只会令我将来忙碌的时候感到混淆。我的主要动机是保留一个,不要很多。所以我问至尊宋仁波切:“我目前修持两位护法,您是否能给我建议,告诉我应该选择哪一位护法作为终生的修持,以协助我消除学佛的障碍?”这是我当时问宋仁波切的话。宋仁波切只是这样回应我:“如果你想要,我会给你我的护法。”我双手合十、顶礼,对宋仁波切说:“请赐予我您的护法。如果祂对您而言已经足够,也是您一生的修持,而您又是佛,那祂对我而言肯定是足够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
在一个月内,宋仁波切在加州洛杉矶的图登达杰林授予多杰雄登灌顶。什么是托命灌顶?托命灌顶指当上师向你介绍多杰雄登时,以象征性的方式,跟多杰雄登携手。多杰雄登把祂的心交了给你,给予你祂的加持,并承诺给你庇佑。你回馈多杰雄登的,是你将视祂为你主要的护法,直至你证得菩提心为止。因为当你一旦证得菩提心,你就不再需要护法,你本身已经高度觉悟。这是我们的承诺。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当你接受托命灌顶时,上师将给予你多杰雄登心水晶,象征多杰雄登将庇佑你直至你证得菩提心。
宋仁波切一次只能同时授予三个人托命灌顶,所以六七八十个人,需要用上一整天的时间。你只能三个人同时接受灌顶,当时没有集体的托命灌顶。我跟另外两个人同时接受灌顶,接受护轮和代表多杰雄登之心的水晶。就这样,我从宋仁波切那儿接受了托命灌顶。
在这之后,我每个月都跟格西拉和其他同修一起进行多杰雄登修持,学习仪式、手印、祈愿、吟诵等。事实上,我从格西拉那儿学习如何制作多杰雄登朵玛。我制作的朵玛虽然有点歪,但总算还能食用。我在佛教中心制作朵玛。我是负责做朵玛的男孩。有时候,格西拉每个月会循众要求进行两次金甲衣护法和多杰雄登法会,有时则是3次,所以我每个月也会制造2到3次的朵玛,同时也参与法会。我负责击鼓。也就是说格西拉敲钹,我击鼓。有时候他敲钹时,我搞砸了。格西拉就会看我一眼。我则有点心虚。我们跟宋仁波切共同进行了多场法会,当他在那儿的时候,每个月都如此。你能够想象吗,我在一个室内,跟宋仁波切、格西簇亲格而辛这两位佛,以及我所有的佛法兄弟姐妹们,约八九十人在一起,共同进行多杰雄登法会?一切都很好。
让我重申,我在新泽西时透过洛塔第一次接触了多杰雄登。随后当我离开新泽西到加州时,格西簇亲格而辛把多杰雄登介绍了给我们,他鼓励我们修持,要我们修持,也使用赤江仁波切著的《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为教材来教授我们这项修持。我曾经出席这些开示。格西拉会用英语讲解,我们则会进行修持。没有关于多杰雄登的恶言,没有禁令,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中心没有遭遇任何不幸,没有人遭遇任何不幸。没有人说多杰雄登的坏话。
我们没听过关于多杰雄登的任何负面言论,而我要清楚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在洛杉矶的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修持多杰雄登,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主要修持.。我们的主要修持是《朗讲》、《修心八颂》、《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度母修持,我们大量学习《菩提道次第》,还有辩经,我们还学习《十二因缘》、《三主要道》。这些都是格西拉教授我们的主要修持。我们平日很少进行多杰雄登修持,一个月只修持一次,但我们都有祂的图片、祈愿文等。没有政治色彩。格西拉从他上师至尊赤江仁波切和宋仁波切那儿接受这项修持。我从宋仁波切那儿接受这项修持。宋仁波切从他的上师赤江仁波切那里接受修持,而赤江仁波切从他的上师帕绷喀仁波切那里接受修持。帕绷喀仁波切则是从他的上师那儿接受修持,如此类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们开始修持多杰雄登时,那时我18岁,所以是1983年。我在1983年18岁的时候,从至尊宋仁波切那里接受多杰雄登修持。我们从不曾为了伤害其他传承而向多杰雄登祈愿。我们从来不曾为了伤害敌人或想象中的敌人而向多杰雄登祈愿。我们修持多杰雄登是为了能很好地了解《菩提道次第》、《朗讲》,为了能获得成就,能够了解在《菩提道次第》中的佛陀教诲,以便能转化心识,成为一个宽容、善良、慈悲的人。换句话说,为了取得证悟。我们从来都不曾主动或被告知要为了任何其他的原因而向多杰雄登祈愿。中国不涉及这个修持。没有任何议程,也没有政治,什么都没有。
我那时18岁,跟格西簇亲格而辛住在洛杉矶的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他的上师宋仁波切拜访我们6个月,并成了我的根本上师。我们从宋仁波切那里接受教诲。我们接受灌顶,发誓一生会守住这项修持。我们也接受大威德金刚、金刚瑜伽母、如意摩尼度母、胜乐金刚、普渡三恶趣观自在菩萨、马头明王、白度母等等。我们也从宋仁波切那儿接受这些修持和释义。我们必须修持这些法门。所以,根据宋仁波切的忠告,我每天除了修持多杰雄登,还要修持这些法门。宋仁波切传授我们如意摩尼度母、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金刚瑜伽母和普渡三恶趣观自在菩萨法门等。我们每天都要做这些修持。我每天的功课包括这么多的多杰雄登修持和那么多宋仁波切给予我们的其他修持。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并不因为跟中国政府有关系而去修持多杰雄登,我不因为想跟达兰萨拉或至尊嘉瓦尊者对立而修持多杰雄登。你知道吗?嘉瓦尊者曾多次探访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中心到处都是多杰雄登图像,嘉瓦尊者一句话都没说。由此可见,重点是当我们从至尊宋仁波切那儿接受多杰雄登修持时,百分百是为了佛法修持。宋仁波切是我的上师,也是我上师的上师。当他传授我们这个修持时,我们承诺了就去做,这就是诚信。我不在乎别的上师对我说什么。我不在乎别的传承对我说什么。我不在乎别人对我说什么。我只在乎我的上师对我说什么。我并不是不尊敬其他上师。我不是不尊重其他人,但我只想清楚说明,当我们接受这项修持时,那纯然只是为了佛法的目的。多杰雄登祈愿文中,没有任何一处教你去毁灭敌人或伤害人们,它只教我们培养慈悲、出离心,培养龙树菩萨讲授的空性正见,以及培养能让我们证得菩提心的心念。这就是我们的祈愿。事实上,格西拉从不允许我们为了一些小事去祈求多杰雄登。
让我再回溯。在我们从宋仁波切、格西拉那儿接受任何教诲之前,我第一次从格西拉那儿接触多杰雄登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在找寻一份工作,我需要靠这份工作来支付账单,但当时只有16岁的我,不太符合工作的条件。我申请了一份工作,他们表示会考虑。如果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就会离中心很近,对我很方便,而我又可以缴付账单。我到楼上找格西拉,告诉他整个情况。格西簇亲格而辛正在他楼上的房里坐着。他房里的佛坛上有大威德金刚唐卡和多杰雄登唐卡这就是我在18岁那年跟多杰雄登护法结缘的经过。我再次重申,那并不是因为任何政治因素,纯粹是为了佛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视频文字本(第三部分)
至尊宋仁波切供茶给上师至尊赤江仁波切。
所以,当我们修持或接受多杰雄登的修持法门时,必须了解我们并非从一般的人,或一般的学者,一般的老师或一般的僧人那里获得修持法门。我并不是说一般人有什么不好,而是强调传授我们修持法门的是当今世上其中一位最伟大的辩论大师,甘丹寺前住持,有学识、有经验的密续修行者,显密学识渊博的大师,一位以神通能力著称的人,高成就者,一位上师中的上师,一位负责教导格鲁派三大寺院: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格西和僧侣的上师。至尊宋仁波切并非一位平凡的人,也不是一位平凡的僧人,不只是我,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三大寺的僧侣也都这么认为。宋仁波切对显密知识的精通为三大寺所共知。他在西藏,其出身地康区和甘丹寺也极负盛名;甘丹寺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尊重宋仁波切,他是他们的上师。当宋仁波切在甘丹寺授课时,来自哲蚌寺的人,哲蚌寺的僧侣,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学者、格西、住持们都会涌来听闻开示。
宋仁波切并非一位平凡的人、僧人或平凡的学者。他是上世纪其中一位备受尊重的格鲁派上师。
他博学的程度几乎无人可比,而这并非我对自己上师的赞美,而是我进入寺院时,格鲁派里每个人都公认的事实。我跟上世纪其中一位从西藏逃出来的最伟大和最博学的上师生活在一起,侍奉他,从他那里接受教诲与誓约。宋仁波切在格鲁派里赫赫有名,这并不因为他是一位电影明星,而是因为他的所学、他的修持、他的能力、他掌握显密教法的能力无可比拟。至尊嘉瓦尊者非常喜欢宋仁波切,他常会扯宋仁波切的胡子,再开玩笑地拽一下。宋仁波切对上师至尊赤江仁波切非常谦卑又忠诚。赤江仁波切跟宋仁波切是完全一样的。他是第十四世嘉瓦尊者的经师、最高等级的格西拉然巴、甘丹赤巴的转世,他的转世甚至可以追溯到佛陀时代那位佛陀的私人马夫。
我们从博学多才的上师和修行人那里获得教义,他们的资格完全毋庸置疑。我有幸跟随新泽西的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学法。我有幸接受甘丹萨济寺的格西簇亲格而辛仁波切的教诲和修持,还跟他一起居住了近8年的时间。我有幸跟随至尊宋仁波切学习,生活在一起并从他那里接受传承和教诲。我对这些上师承诺,我对宋仁波切承诺,不管他赐予我什么教诲,我都会修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不需要任何其他解释,我不需要其他说法或企图说服我的话。我对嘉杰宋仁波切以及他的两位弟子格西簇亲格而辛仁波切和堪殊洛桑达庆仁波切许下了承诺。我对宋仁波切许诺,我对他发誓,不管他赐予我什么修持法门,包括多杰雄登法门,我都会继续修持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要我违背对根本上师的承诺,那是不可能的。
1986年我抵达达兰萨拉,当时我前去等待嘉瓦尊者授我出家戒,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针对多杰雄登的禁令的一些暗示。你要明白,当时我只有22、23岁,年纪还很轻,又远从加尼佛尼亚州的图登达杰林佛教中心来。我每一位上师都修多杰雄登,每一个月我们都进行雄登法会,道场每一位同修都这么做。当时什么问题都没有。当时的我非常年少无知,对什么都抱有美好的期待,你甚至可说当时的我理想化一切,我认为大多的年轻人都怀有过于理想的想法,他们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看清事物的真相,然后学习去面对,而他们会怎样去面对,就决定了他们有多成熟,也造就了他们日后人生的思维和行为。
当时我一直都想找人画一张嘉杰宋仁波切的唐卡。唐卡中央是宋仁波切,从宋仁波切的心间发出一道光,这道光化现为金刚瑜伽母,另外一道光则化现为多杰雄登。会想这样画,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名上师,他也可以化现成本尊及护法。话说回来,嘉瓦尊者的私人助理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些年来我跟他已经失去联络了,但他曾跟我非常要好,他来自尊胜寺。是他把我带到唐卡画师那里,这位画师是嘉瓦尊者的私人唐卡画师。随后我告诉这位画师我想画怎样的唐卡。这位画师非常友善,他对我说“好的,我会画宋仁波切,我会画金刚瑜伽母,但我不会画多杰雄登。”当下我就吃惊并问为什么。他说:“哦,因为我们不画这位护法。”当时是1986年,也是我第一次听闻关于护法禁令的事。然后我跟另一位住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朋友说起此事,他也是一位转世喇嘛,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位翻译员,也是一位学者。他对我说,基本上当时流传多杰雄登法门应被限制,一些人说这个法门没有带来助益,或许大家都应该放弃修持。未来嘉瓦尊者或许会针对此事发表看法。.
我的个人唐卡上画着至尊宋仁波切化现为金刚瑜伽母和多杰雄登。
我真是大吃一惊,不夸张地说,我是震惊了。对我来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必须从嘉瓦尊者和我的上师之间选其一,因为如果嘉瓦尊者是对的,那么我的上师就是错的;如果我的上师是错的,那么我从上师那里接受的每一个修持都是错的。
如果我选择跟从上师,我就没办法跟嘉瓦尊者保持法缘。这也深深地困扰着我,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尊敬嘉瓦尊者,他也是我的其中一位上师。
于是我独自一人在达兰萨拉的房间里做熏烟供,我在冬绸上连续三天燃烧了大量的杜松粉,事实上我也烧了那段冬绸。我向多杰雄登祈愿,我哭了很多次,当时我有少许的忧郁。我深受困扰,也感到非常的迷惘,因为我被告知要在嘉瓦尊者和我的上师宋仁波切之间做抉择。要在两位上师之间选一位,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如果我选择宋仁波切而放弃嘉瓦尊者,我违背了我对嘉瓦尊者的戒誓,我也因此会堕入三恶趣。如果我选择嘉瓦尊者而放弃宋仁波切,我也违背了戒誓、上师依止心的戒誓,更会堕入三恶趣。
无论我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要堕入三恶趣。或许你们没有这样的两难或如此的窘境,因为你们没有同时向两位上师学法,一位雄登上师及一位非雄登上师。或许你没有这样的难处。但是你们要对我的处境有同理心,其实也不只是我,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上千名僧人,以及西藏的千千万万人,对嘉瓦尊者、赤江仁波切、宋仁波切及多杰雄登有无比信念的人,都身陷这种处境。400年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被逼做出这样的抉择。当时我哭了3天。我非常忧郁,我不知所措。那段时间是我人生其中一段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当中最低潮、最悲伤的经历是当嘉杰宋仁波切圆寂的时候,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煎熬的时候。第二煎熬的经历就是,我必须在宋仁波切和嘉瓦尊者之间做抉择。
有些人反对嘉瓦尊者,说我应该站出来表明对尊者的不认同。他们给尊者取不同的名字,贬低他,批评他,但我做不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的承诺。我曾向尊者求法,我不能这么做。也有另一些支持尊者的人告诉我:“嘿,你应该放弃多杰雄登,你的上师是错了,你应该跟随嘉瓦尊者。”我也不能这么做,因为不管我做什么选择都是错的。人们要理解这一点,你们不在这个困境里,但我身陷其中。你想想,你死的时候,你不会经历我的死亡,我的中阴身、我的来世、我的业果和业报,以及我违背了与上师的三昧耶的后果。你不会经历我需要面对的结果,我会自己面对,你不需要跟我说该选择尊者、多杰雄登或宋仁波切,因为我需要面对我做抉择后的结果,你不需要。
所以关键是,在第三天结束之前,我跟我的朋友说起这事,他是一位藏族仁波切,基本上他出于好意责骂我。他说:“你别傻了,你不必做什么抉择,两位上师你都尊重,继续你的修持不就好了吗?你不需要多说什么。”我想那是唯一的办法。那是唯一的办法。但这件事让我非常痛苦,做这个决定非常艰难。之后我出席嘉瓦尊者的多个开示,我非常喜欢,也从尊者的开示中学习不少的知识,期间我也出席我其他上师的开示。我告诉过你,我有16位上师,15、16位上师,我也出席我其他上师的开示。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当中的13位都修多杰雄登法门,也推广此这个法门。于是我选择不在上师当中做抉择。如果嘉瓦尊者说我不能出席他的开示,那么我就会遵循他殊胜的愿望,我不会出席。不是我不要出席,我也不是在发出声明,我更不是在做无声的抗议或是在传达什么秘密的讯息,表示自己的不高兴,不是的。如果尊者说我不能出席,我便不会出席。当尊者批准我出席,那么我会高兴地出席,这是我的感受,因为佛法开示就是佛法开示。
我修持多杰雄登并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破坏任何人,不是为了表达政治声明,或让自己跟某些政府或一些政治运动结盟。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因为我是一名佛教僧人。我剃度、披上僧袍、学习、修行、禅修和学习控制本身的负面思维,转化自己以便成为一位成就者。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众生。我成为僧人和修行,以及跟随这些大师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修行。
我修持多杰雄登,不管是以什么形式,都跟任何政治没有任何关联。所谓的禁令,无论我们要称之为禁令或不是禁令,或者是训谕或敕令,又或者是禁止雄登修持的讨论,都在1996年激烈地展开,但我却是在1983年获得这个法门,这中间有着13年的差距。如宋仁波切如此的大师断不可能会犯错,去修持一个会带来破坏、伤害,充满敌意及有意伤害嘉瓦尊者性命的邪恶法门。像宋仁波切这么一位大师,一位精通显密的大师、西藏甘丹萨济寺的前住持,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亲近嘉瓦尊者;而且像他这么一位连圆寂和荼毗的日期都纪录在日历上,以提示他转世日期的人,这位大师甚至有能力控制自己何时圆寂,将转世在何处,并且把它纪录在日历上--这些全都清楚地纪录在他的传记里。传记我看了。宋仁波切有可能如此愚昧、错误、不聪明,整81年来都看不出来?就说他修持多杰雄登法门的50~60年好了,他怎可能完全没有察觉雄登是邪恶的?唯有等到1996年我们听说了多杰雄登是邪恶的,宋仁波切这才错了,赤江仁波切才错了,以及所有的传承祖师都错了?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如果宋仁波切是错误的,他修持雄登法门,并破了本身的皈依戒;他因为修雄登法门而沦落。嘉杰宋仁波切至离世为止都在修雄登法门。他修雄登至去世为止,意即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持续修持雄登法门。即便在他准备离开自己肉身的最后时刻,他还进行了雄登法会,告诉多杰雄登:“我这一生人中,你给了我很大的协助,我的许多佛法事业有了你的帮助才可能成就,我没有其他请求了,这是我献给你的荟供。”两周后嘉杰宋仁波切进入禅定,并在禅定中圆寂。
嘉杰赤江仁波切--嘉瓦尊者的根本上师,有可能一辈子都在修持一个邪魔、邪灵、一个邪恶的法门吗?如果赤江仁波切修持一个邪灵和恶魔的法门,如果他一辈子都修持一些邪恶的法门,这也意味着他已经破了皈依戒。如果他破了皈依戒,也就等于破了他的三律仪戒的基础。他也破了别解脱戒,也就是出家戒,那么他就等于还俗了,甚至不算是一名僧人……他的菩萨戒、皈依戒,还有他的密续戒。那么,他的三律仪戒都失去了。他的别解脱戒,也就是出家戒,对不对?与此同时,还有作为出家戒基础的皈依戒。如果他修持雄登法门,赤江仁波切就破了皈依戒,破了出家戒,因为出家戒建立在皈依戒的基础上。如果破了皈依戒,你就无法成为一名僧人。譬如说,我是一名佛教僧人,我突然不再是佛教徒,不再要修持佛法了,我还可以成为佛教僧人吗?那肯定不能。如果我不再是一名佛教僧人,那么很自然的,我就失去了我的密续戒和菩萨戒。要接受文殊菩萨、度母、事部密续、行部密续的灌顶,你需要皈依。要接受喜金刚、金刚瑜伽母、大威德金刚、时轮金刚、密集金刚和如意摩尼度母等更高阶密续法门的灌顶,你需要坚守菩萨戒,坚守你的皈依戒。因此,赤江仁波切有没有可能因为修持雄登法门至生命最后一刻,就因为修持雄登法门,导致他失去了本身的皈依戒;而因为失去了皈依戒,他失去了出家戒;由于他失去了出家戒,其他所有戒律也失去了?其他戒誓并不依靠出家戒,因为即便你没有持守出家戒,仍可以持守那些戒誓。不过,由于他失去了本身的皈依戒,也就失去了菩萨戒,同时也失去了密续戒;因此他所传授给他人的任何法,他所赐予的任何灌顶和修持法门,也变得无效。这有可能吗?
这是不是意味着赤江仁波切赐予西藏和印度寺院内千万名多杰雄登僧侣的所有佛法,都没有任何加持力?这有可能吗?那将导致我们相信,所有传授给嘉瓦尊者,现任嘉瓦尊者的教义、灌顶、修持法门、释义和口传,全都是无效、失效的和没有加持力的。这有可能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几千名至今还在世的格西、上师和大师,以及我的上一代人,这些从赤江仁波切及宋仁波切那里接受教诲和整个传承的人,其实都是在向一位失去皈依戒、供奉多杰雄登的上师祈愿吗?这意味着每个格鲁派道场、格鲁派寺院,都必须将赤江仁波切和宋仁波切的照片从寺院移走。这意味着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的祈祷大殿,都必须将这些上师的法座、照片,以及来自他们的任何教诲和经典都移走。这也意味着嘉瓦尊者不应该传授任何他从赤江仁波切或赤江仁波切的传承那里获得的教诲。一样也不行。为什么?赤江仁波切直到圆寂的那一天,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修持多杰雄登法门。他不曾放弃。嘉杰宋仁波切修持多杰雄登法门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他圆寂为止,他都不曾放弃。这两位都是多杰雄登上师。既然是多杰雄登上师,他们也就失去了本身持守的戒律,失去了本身的修行,他们理应没有任何成就才是。因此,我们从他们那里接受的任何教诲,包括一切的密续、显续教诲,所有的灌顶、修持法门皆是无效的。事实上,你完全从膝关节把格鲁传承切断了,那个人再也无法站立。因此,这有可能吗?
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告诉我们多杰雄登是魔,是邪灵,他会伤害嘉瓦尊者。他会伤害藏人的利益,他会伤害任何一个修持其法门的人。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应该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这会招引邪恶的能量。这有可能吗?这么说来,宋仁波切是走动的负能量?赤江仁波切是走动的负能量?这怎么可能? 当我在1988年1月抵达甘丹寺,抵达甘丹萨济寺布康康村的时候,我顶礼后走入寺院。他们带我去见了住持,我从此成为甘丹萨济寺正式的一员。在这之前的两个月,嘉瓦尊者在达兰萨拉授予我出家戒。早在1987年,嘉瓦尊者就授予我出家戒。因此,我的法名是丹增索巴(Tenzin Zopa),根据嘉瓦尊者丹增嘉措的名字而取。因此他是我的授戒上师。我的皈依上师是修持雄登法门的堪殊洛桑达庆。我的密续上师是修持雄登法门的至尊宋仁波切。我的显续上师是修持雄登法门的格西簇亲格而辛。因此,堪殊仁波切、宋仁波切和格西簇亲格而辛都修持多杰雄登法门,而嘉瓦尊者则没有修持多杰雄登。
因此,当我在1988年抵达甘丹萨济寺时,当时大概是23岁、22岁或23岁大概那个年龄,我很兴奋,因为那是我计划度过余生的地方,是我计划住下来的地方。那里有泽美仁波切、嘉杰拉谛仁波切,有来自甘丹江孜寺的甘丹赤巴杰尊江白群佩,嘉杰登马洛确仁波切则在不远处的哲蚌寺。还有嘉杰扎貢仁波切、 察雅多登仁波切,伟大的堪殊强巴耶喜仁波切,以及伟大的格西干竹泽令等。我们身边全是大师。走出甘丹寺,无论是转左还是转右,总会遇见博学的格西,多才的大师,伟大的仁波切,伟大的杜固,他们全都在我们身边。几年后,至尊嘉杰赤江仁波切的转世来到了甘丹寺。我的住所詹拉章,跟赤江拉章毗邻。我经常看见年幼的赤江仁波切在玩耍,他会跟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当然,我们彼此双手合十。所以,赤江仁波切就住在我隔壁,接下去则是泽美仁波切的住所,沿途走下去是宋仁波切的住所,接下来是神谕媒的住所,那里住满了博学的大师。
现任转世,至尊赤江卓图仁波切。
拉谛仁波切就住在附近。我们都在那里,都住在那里。每个月,当我们到甘丹萨济寺进行护法法会时,我们进行五护法法会(Goncho Nga):吉祥天母、大黑天、嘎拉路巴、财宝天王和白玛哈嘎啦(贡嘎)。金甲衣和多杰雄登法会也被纳入其中。所以,每个月,甘丹萨济寺的僧人都进行多杰雄登法会。甘丹萨济寺也有一个护法殿,叫Goenkhang。在护法殿内,有金甲衣护法,有Shidak Gyenye也就是跟宗喀巴大师有关联的特别护法,有嘎拉路巴、多杰雄登。在甘丹萨济寺,僧人每天都会给多杰雄登护法献上金酒。在甘丹萨济寺,我们也有多杰雄登佛像和多杰雄登的圣相。
隔壁就住着由赤江仁波切和宋仁波切负责训练的神谕媒,而降神于他的是多杰雄登寂静相、多杰雄登忿怒相、金甲衣护法、喀切玛波,以及其他几位护法神。就在那个地方。宋仁波切、赤江仁波切、泽美仁波切、拉谛仁波切、堪殊强巴耶喜仁波切等所有大师,全都向护法提出咨询。
事实上,每年的藏历新年,我们都会进行每年一次的特别降神仪式。在甘丹萨济寺,他们会准备一个法座,所有的住持、高僧、杜固、格西和整座寺院的僧侣,都会聚集在甘丹萨济寺。多杰雄登神谕媒将受邀到甘丹萨济寺,坐在法座上。多杰雄登的忿怒相将会降神,而住持、前住持、上师、杜固、格西,甚至我都会出席。我们会趋前给多杰雄登献哈达,多杰雄登则会向众人撒米,加持所有的僧侣然后离开。
接下来,降临的是金甲衣护法,同样的情况,同样的程序。第三位是多杰雄登寂静相来到甘丹萨济寺。当多杰雄登寂静相到来时——他被称为度津——他头戴宗喀巴大师的法帽和僧袍,坐在法座上。我们所有人包括住持、上师和大师,每个人都会趋前给他做供养。接着我们坐下来,聆听多杰雄登给我们佛法开示。然后,寺院方面会向多杰雄登提出问题,而祂会预言未来。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正如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当我抵达闻名遐迩的甘丹萨济寺——甘丹萨济寺建立于600多年前,由伟大的瑜伽大师、伟大上师、大成就者、导师、圆满证悟的圣者宗喀巴大师所建立。而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也建立了哲蚌寺和色拉寺。西藏在1959年之前,哲蚌寺就有1万名僧侣,色拉寺有将近6600到6800名僧侣。甘丹寺则有3000到3300名僧侣。这数据还不包括安多省扎西奇(拉卜楞寺)寺的上千名僧侣。这数据也不包括历代班禅喇嘛驻锡寺院——位于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不包括几百所其他分布在西藏、卡尔梅克和蒙古的重要寺院。甘丹寺是所有这些寺院的起源,因为那是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居住的地方。大师的弟子为上师了建造这所寺院,大师居住、弘法和将佛陀教诲完整保留在甘丹寺,直到他圆寂为止。
邦拉康村僧人全都修持多杰雄登,后来从色拉寺分割出来,成立了色邦寺。
譬如说,在甘丹寺,有一部分的僧人完全专注于度母修持,有一些僧人完全专注于胜乐金刚或大威德金刚的修持。某位僧人可能主要修持大威德金刚法门,但他也可将其他法门作为日常的修持。譬如,他们可以少量修持度母、文殊菩萨、宗喀巴大师、密集金刚、金刚瑜伽母的法门,不过主要的修持法门是大威德金刚。同样的,寺院里有些僧人主要修持度母或大威德金刚,但他们专注于大威德金刚法门,并不意味着度母法门不好。他们专注于度母法门,也不表示大威德金刚的法门不好。因此在寺院里,你可以选择你个人想要修持的法门、禅修,完全没有问题。
在寺院里你经常会听闻一位名叫格西丹达的大师,我在寺院那段时期,他会在甘丹寺赐予多杰雄登托命灌顶。在哲蚌寺,札贡仁波切也赐予多杰雄登托命灌顶。嘉杰札贡仁波切也是一位博学、温和、纯净的僧人、学者、大师、拉然巴格西。他是哲蚌寺一位很伟大的大师。我也具备了足够的功德从达貢仁波切那里接受很多教诲。他已经圆寂了,然而在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每个角落,都有人在修多杰雄登,也有特别为多杰雄登而设的护法殿,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祂的法会,这完全不是问题。
注:视频文字本待续……请点击查看中半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7edf5f0102vw8v.html
视频文字本下半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7edf5f0102vw8z.html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