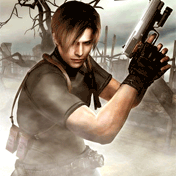9月17日晚7点半,看话剧《公民》,到人艺剧场才知道,明天——9月18日才是正式的公演。整个晚上,我坐在剧场的一个角落里寻找着“公民”。但我的结论是:人艺话剧《公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公民”。
说什么都有了,是说林兆华有了,冯远征也有了;人物与灵魂的对话有了,对时空眼花缭乱的打乱、切碎、组合、缝缀也有了;色彩灰暗的鬼魂版大清官员有了,出出入入略显多余的捡场人也有了;皮影戏式的日本天皇有了,傀儡戏里的宣统皇上也有了;后宫的情欲与挣扎有了,满大街追着末代皇帝磕头的小脚奶奶也有了;末代皇帝撒尿也有了,末代皇帝阳痿也有了……但是,就是没有“公民”。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处于极度纠结焦虑的“身份认定”之中——他做儿童的时候是最不真实的儿童;做“宣统皇帝”的时候是最没权的皇帝;被赶到天津做寓公的时候是最不老实的寓公;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是最“儿皇帝”的皇帝;他是天下最有条件纵欲的男人,却没做过一晚真正的男人;当他在抚顺监狱中逐渐认同自己的“战犯”身份时,却以“前皇帝”的身份蒙恩获释;出狱后他试图当个“一品平头大百姓”,却继续被人当成政治怪物展览示众;他极力想讨好上边儿,“想做点事”,写过《我的前半生》,也在香山植物园研究过树叶子,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之所以得以苟全,不过是为了证明那如天似海的“宽仁”……他死于文革开始之际,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爱新觉罗·溥仪确实不只一次地表示过:自己在新社会过上了真正的“人”的日子。这一方面,是切割掉前半生噩梦般无力控制的险恶命运后,心理上的“大撒把”式的解脱;另一方面,就是讨好,他明白自己应该扮什么角色、说什么话、表什么态、谢什么恩,他并不傻,他知道剧本,了解导演的脾气,他听话地扮演了一个“被指定”的“特殊社会角色”。当然,以他心性的懦弱卑微和无知,他可能很快就习惯了这般角色与如是演出,并很可能甘之如饴,游刃有余。这才是真实的溥仪,而现在那些关于“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只可作“故事”观,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编的;有的,是别人愣给他编的。
幸亏溥仪死于文革开始不久,否则这个故事将难以结尾,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溥仪,和“公民”这个概念有什么关系?
我的结论是:毫无关系。溥仪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他的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舞台上,成为政治清明的“喘气儿的注脚”——一个连“自我”都不是的人,哪里谈得上什么“公民”?
更何况,在一个“非公民”的社会形态下,所有的人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他一个被释放的战犯,怎么可能超乎时代之外,得天独厚地独自成为一个公民?话剧《公民》的结尾,居然还让他来了一大段现身说法,侈谈到什么“民主”、“自由”、“博爱”,我看到那里极度“出戏”,好像不是在看戏,而是在听一场蹩脚的、充满悖谬的虚伪报告。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戏的主题圈定在“公民”上,事实上,好好讲述溥仪这个时代大风暴中心的小人物,已足以令人唏嘘感叹。生硬地塞进一个“公民”的内涵,让溥仪像“白毛女”一样,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神话,这既不符合对溥仪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解读,也让戏剧本身捉襟见肘,处处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能明显感觉到编导者为了完成对“公民”这一概念的“塞入”,几乎费尽了心力。但是,任何努力都无法回答观众的一些最朴素、最“二”的问题:溥仪怎么就变成一个公民了?不当皇帝不再犯罪、有60元工资、有资格投票选人民代表、有个女人甘心和他组成无性婚姻,他就“公民”了?那些跪地叩拜他的庸众是公民吗?那些官员真把他当成公民吗?他真的懂“公民”二字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事实上,本来挺“有戏”的一个“戏”,被“公民”这个概念的强行植入,弄得超级拧巴——相信以人艺编导演员的水平,应该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过这种拧巴,只是,没人、或者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改变它。由此观之,戏剧,没有坚实的逻辑作为骨骼支撑,再华丽也是一滩烂泥,再努力也是南辕北辙,再“现代”也是虚弱陈腐,再装饰也是一个空壳。人艺的这出戏,让我看到了当代中国顶级艺术团队理性思维和历史认知的严重缺失。
溥仪去世已经多年,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依旧浮荡着对皇帝、皇家、皇宫、皇室、皇族的向往和仰慕。今年春节,据说去故宫博物院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多少多少万。我对此的解读是:如果一个社会没人去逛博物馆,最多就是缺教养;而如果一个社会流行集体仰慕皇上,则基本上是没睡醒。我们这个社会,要真正完成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转型,还有很漫长曲折的路要走。
回过头来挖掘溥仪自身经历中的“戏剧性”,我以为,他仅仅是一条大时代中的可怜虫,而其“可怜”之处,不仅在于他前半生经历了那么多纠结的“身份认定”,也在于他后半生依旧延续着这种“身份认定”的纠结。如果人艺这出戏一定要讲“公民”,也许就该讲溥仪后半生想做“公民”而不得、而不会、而无从做起。
那些扎堆儿看溥仪喝豆汁儿的老街坊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给溥仪叩头请安的皇子皇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没有出场、但被选为人民代表的也不一定是“公民”,而溥仪本人,无论前半生还是后半生,也从来就不是“公民”。作为“任何人都可以被改造”的神话玩偶,他尽力了;作为“公民”,他想也别想、想也没想过!一言以蔽之,他从过去的“鬼”,试图变成“人”,却有复杂的社会力量使他变成了非人非鬼的“符号”。而这,才是他最“结实”的戏剧内在结构、最“完整”的悲剧性之所在。
可惜,我在人艺的《公民》中,既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也没有看到一个人物成为“公民”的努力与不能,更没有看到一个不能产生“公民”的社会的荒诞。在满剧场飞舞的关于“公民”的模糊概念下,我看到了人影幢幢、鬼影幢幢,看到了人鬼对话中不时出现的逻辑错乱,看到了带有活报剧色彩的历史叙事,看到了过分强调的性无能,看到了号称“很现代”的舞台呈现,甚至,我看到了编导和演员们为了自圆其说而付出的努力,但是,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公民”。
没有“公民”的《公民》,注定成不了人艺的经典。当然,它很“经典”——它以很“经典”的方式记录了我们对于“公民”概念的当代认知——虽然这并不是编导者曾经期望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