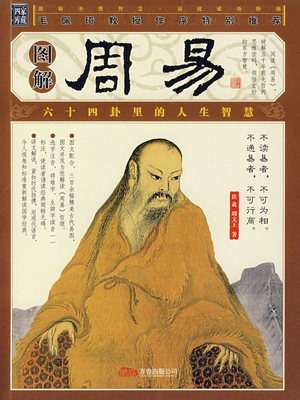///es tmis mem kas yarmrm ma nas
“He gives, of that thereis no measure nor number.”
——“Maitreyasamiti-Nataka”YQ1.29 1/2[recto]3
“吐火罗文”,这门连名字至今都未必可以算是确定了的稀奇古怪的语言,它的发现和解读、研究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位德国的天才学者Sieg和Siegling,根据吐火罗文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从地理位置来看,既然吐火罗文残卷仅在中国西域有所出土,那么,它似乎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表示数字“100”的字,在它的A方言里作kant,B方言里作kante,都等于拉丁语的centum。再加上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特点也都指明,它又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即相对于东支的“satam”语言的西支“centum”语言。这就给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出了一道真正的“世纪难题”。由此还引发出众多的其他难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地的问题。吐火罗文的发现、解读给这个本来就众说纷纭的老问题之火加上了一勺新油: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于亚洲的老说法,似乎得到了某种有力的支持。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对于这门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近,而在语言系属上却又离我们很远的语言,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我国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王国维在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所收《静庵文集续编》)里写道:
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尤夥。其中除梵文、佉卢文、回鹘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旋发见,其一种为粟特文,而他二种则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语即玄奘之所谓窣利,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其东伊兰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诸国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有相关笔记留存,具体可参见先生的《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272—285页)、王国维等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新疆吐火罗文残卷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吐火罗文残卷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已经足以冲击比较语言学、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入华史等等领域中的既有陈说了。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已经处于落后的地位了,所以慨言“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幸运的是,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的季羡林先生终于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或者毋宁说不幸的是,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学者利用相关的吐火罗文解读、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获,但是,从发现吐火罗文至今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将吐火罗文研究视做解决其他相邻问题的手段的同时,而又能够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出发,将吐火罗文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却仍然只有先生一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年来,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文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个事实,不能不令后来者为之汗颜。
一 吐火罗文研究的学术谱系
劫后幸存的“学习本”(见《学海泛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1—26页)不见有关先生研习吐火罗文的记载。实际的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先生的博士导师Waldschmidt教授就被征从军了,原本已经退休了的Sieg教授以垂暮之年,重新出山,代替Waldschmidt教授上课。其时,先生已经基本修完了必需的课程,正在集中精力撰写难度很高的博士论文,本来并没有从事吐火罗文研究的打算(见《学海泛槎》,39—40页)。而Sieg教授却在第一次上课时就对先生郑重宣布,要将自己毕生最擅长的学问,即《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先生(见《留德十年》,《季羡林文集》第二卷“散文”,461页以下)。这也是中国学术的幸运,先生不顾种种困难,还是毅然投身于一个崭新的、难度极高的研究领域了。
Sieg教授所讲的四门绝学,前三种是见于“学习本”的,可见是列入哥廷根大学的正式课程之中的;吐火罗文则不是,是Sieg教授额外开设的。当时从学的只有先生和比利时的赫梯文专家WalterCouvreur。具体的研习情况,见于先生所著《学海泛槎》、《留德十年》的有关章节。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吐火罗文的初步解读成功,是以E.Sieg、W.Siegling于1921年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Sprachreste,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undLeipzig,1921)为标志的;而吐火罗文几乎完全解读成功的标志则是E.Sieg、W.Siegling、W.Schulze合作的巨著《吐火罗文文法》(TochrischeGrammatik,G?觟ttingen,1931)。说“几乎完全”,是因为迄今为止在吐火罗文里还有一些字词的语义无法确定,一些语法形式也有待进一步解释。但是,无论如何,Sieg都是成功解读吐火罗文的首代功臣。因此,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属于直接受业于解读者的第二代。
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庸俗的论资排辈毫无关系。先生曾经回忆道:
我们用的课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Sieg和Siegling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字母转写本。如果有需要也可对一下吐火罗文残卷的原本的影印本。婆罗米字母老师并不教,全由我们自己摸索学习。语法当时只有一本,就是三位德国大师著的那一本厚厚的《吐火罗文文法》。这些就是我们这两个学生的全部“学习资料”。老师对语法只字不讲,一开头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中的前几张。我在这里补充说一个情况。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焚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我后来发现,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真正“残”的残卷,其困难概可想见。Sieg的教法是,先读比较完整的那几张。Sieg屡屡把这几张称之为Prachtstücke(漂亮的几张)。这几张的内容大体是清楚的,个别地方和个别字含义模糊。从一开始,主要是由老师讲。我们即使想备课,也无从备起。当然,我们学生也绝不轻松,我们要翻文法,学习婆罗米字母。这一部文法绝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简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一走进去,立即迷失方向,不辨天日。老师讲过课文以后,我们要跟踪查找文法和词汇表。由于原卷残破,中间空白的地方很多。老师根据上下文或诗歌的韵律加以补充。(《学海泛槎》,40—41页)
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和当时德国一般的教外语的方式,特别是讲授古代语言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比如教梵文就是这样。(见《学海泛槎》,33页)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然而,吐火罗文毕竟不是各方面已经被详细研究过了的、原本没有失传过的、语法已经被用近代西方学术语言再次规律化了的梵文。学习梵文就是学习一门古代语言,而以上述的方式学习吐火罗文就绝不仅仅是学习一门古代语言那么简单了,其实乃是在重复一遍破译解读的过程。可以说学习梵文的人,本身是一个学生;而学习,尤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学习吐火罗文的人,本身还多少必须是一个解读者。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的学术谱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面前还没有很长的研究史可资借鉴,可以直接亲炙破译解读者本人,尽可能地接近吐火罗文被解读前的原始状态,亲身体验在依傍很少的情况下释读残卷的甘苦,从根本上培养起至关重要的独立解读的学术功力。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这一套办法,在我后来解读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时,完全使用上了。这是我从Sieg老师那里学来的本领之一。这一套看来并不稀奇的本领,在实践中却有极大的用处。没有这一套本领,读残卷是有极大困难的。(《学海泛槎》,41页)
上面的夫子自道清楚的说明,在停顿了近四十年、也和相关学界隔离了近四十年之后,已届古稀之年的先生能够迅速承担起释读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艰巨任务,至少在技术上凭借的正是吐火罗文的破译者Sieg教授亲授的方法。
二 两个偶然和三个阶段
我以为,用“两个偶然和三个阶段”的说法可以比较概括地说明先生吐火罗文研究的历程。先说“三个阶段”,这是先生自己的总结。先生认为,自己在将近六十年中学习和研究吐火罗文的历史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在德国哥廷根的学习阶段,这个我在上面已经有所论述了。二,回国后长达三十多年的藕断丝连的阶段。1946年回国后,先生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一点资料,加上大环境的恶化,所以出现了这个尴尬的阶段。三,80年代初接受委托从事在新疆焉耆新发现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缩写为MSN)的解读和翻译工作的阶段,其成果是一部世界上规模首屈一指的吐火罗文作品的研究、考释和英译。(见《学海泛槎》,297页)
“两个偶然”则是我斗胆而为的。我想说的是,假如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Waldschmidt教授没有被征从军,假如接替他的不是Sieg教授,假如早已退休享清福的Sieg教授不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而哪怕有一点点私密或躲懒之心,那么,我想来自吐火罗文残卷出土地的中国学者未必会有机会亲炙解读者,也就未必能学会这门古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掌握了破译法门。这大概不能不说是一个偶然了。第二个偶然是,假如《弥勒会见记剧本》没有在1975年出土,或者没有在我国境内的新疆出土;或者,假如新疆博物馆李遇春馆长像一直就有而眼下更甚的某些人那样,手握珍贵资料,不管自己有无释读的条件,秘而不宣,暗度陈仓为自己谋求出国等等的各种好处,而不是一本学术大公之心;再或者,假如当时(八十年代初)身兼数十要职、杂务猬集、已年过七旬身名俱泰、面前还有大量既定的学术研究课题的先生,不是将学术放在无上的位置慨然接受这个难度奇大的课题的话,先生的吐火罗文研究也只会以遗憾而告终,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欣慰之言:“我六十年来的吐火罗文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也就可以说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了。”(《学海泛槎》,297页)
总之,公认为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里的最佳甚至惟一代表的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里的贡献与地位,不能不讲是个人能力和时代机遇、偶然与必然的巧妙契合的结果。
这些结果就体现为:《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以及由于文章的侧重面或牵涉面等等的关系收入在《季羡林文集》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中的德文论文“Parallelversionen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Punyavanta-Jataka”(《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中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中的《浮屠与佛》,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中的《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等文章。从发表的时间来看,第一、二两阶段甚少,总数不超过五篇,有的还相当短,有的还仅是与吐火罗研究有关;主要的成果集中出现在80年代以后。
三 吐火罗文研究的成名作
德国大学的规定是,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个规定是无法付诸实行的。先生研究混合梵语佛典《大事》的博士论文也只能以打印本形式呈缴哥廷根大学文学院,以及在学术界流通了。四十年以后,才原样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得以正式出版。因此,从发表的时间上看,《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就成了先生第一种正式面世的学术论著了。
关于这篇重要论文的写作背景,先生在晚年有非常翔实的回忆。已经完成博士论文的先生,正在师从Sieg教授研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正是《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这部经有许多其他语言的异本,比如梵文、于阗文、藏文。《大事》里就有这个故事,先生对《大事》当然是烂熟于心的。当时,先生正以翻看汉译《大藏经》为日课,发现其中有几种汉译的异本,有的整个故事相同,有的下属的小故事相同。在Sieg教授的鼓励下,先生选择了混合梵文本《大事》、《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大智度论》、《大方便佛报恩经》、《长阿含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等与吐火罗文本最为接近的几种异本为重点考察的对象,将它们译成德文(参见《季羡林文集》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149页),同时还参照了其他大量的梵文、巴利文、汉文佛典,加上了详细的注释,以与尽管是堪称“Prachtstücke”(Sieg教授用以夸赞完整程度还算差强人意的残卷)实则残缺已然非常严重的吐火罗文本对勘。先生对汉译佛典的熟悉程度,当然不是西方学者可以比肩的。吐火罗文本里一些原来不认识的字,现在有了汉译异本可资参照互勘,就立即可以释读了。
据先生自己的总结(见《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115页以下),比如,利用《大智度论》:TS(《吐火罗文残卷》)No.1a5 samudram kars nemi simpranka,原来不知何意,Gr.(《吐火罗文文法》)§84把prank解释为“矿”;据《大智度论》,知其确切含义是“船去如驼,到众宝渚”。TSNo. 1a6 sartha jambudvipaca peyamuras,原稿残缺,不详何意;据《大智度论》,当是“是时众贾白菩萨言:‘大德!为我咒愿,令得安稳。’于是辞去。”TSNo.1b1 lyom,原来不知字义,据《大智度论》,当即“泥”。(此字先生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五研究要点确定要点的原则》中遗漏,据《季羡林文集》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196页注20补。——文忠案)TS No. 1b3 stwarwakna arslas lo rarkuncas isanas kcak,原来不知其意,Gr.§83释arsal为“毒虫”;据《大智度论》,“有七重堑,堑中皆满毒蛇”,则arsal当是“堑”。TS No. 1b3 stwarwakna spe-下缺,b4 saklumtsasyosopis过残,不知所云;据《大智度论》当是“过是华已,应有一七宝城,纯以黄金而为却敌,白银以为楼橹,以赤珊瑚为其障板,阵渠、玛瑙杂厕间错,真珠罗网而覆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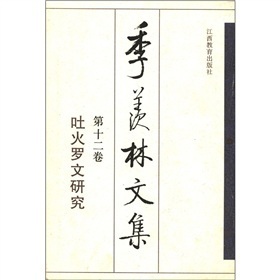
又如利用《长阿含经·小缘经》:TS No.2a3:kyalte neswrasassi sne wawlesu sne psal klu swatsi ses, Gr.§9收入psal,但未做解释。wawlesu的字根是wles(“制造”),wawlesu系过去分词。整句意思不明。据汉译异本,知其对应句为“自然粳米,无有糠糩”。snewawlesu即“自然”,klu即“粳米”,sne psal即“无有糠糩”。
再如利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TS No.8b1:kakela,ela在Gr. §389无解释。先生在这篇论文里将与此相关的一段译成“Dann trat er hinter denTürflugel, verbag sich undwartete”,Sieg后来在《吐火罗文德译之一》(“?譈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I”,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Nr.16,1943)没有注意先生的关键词“verbag sich”,而是译成“ging hinterdenTürflügen”(“走到门扇后面去”。先生以为Sieg翻译此句的时间为1944年,见《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118页,似不确。——文忠案)这个字字义的最后解决,还要等到四十年之后,我在下面再予以介绍。
当时中德两国语文学界的精神都是“发明一个字的字义,等于发现一颗新的行星”(大意,胡适之也曾有此语)。先生的一篇论文,而且还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解决或接近解决了如此之多的字的字义,贡献真可谓大矣!然而,这篇文章的意义还不限于此,在方法论层面上,它首次大规模地将汉译异本引入吐火罗文研究,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举。Sieg教授初步听了先生的发现后,“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见《学海泛槎》,51页)于是,在Sieg教授的推荐之下,1943年,此文发表于在国际东方学界具有崇高威望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eitschrift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第97卷第2册。
这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开端。
四 不仅仅是藕断丝连
随着先生的回国,以及对赴剑桥大学任教机会的放弃,在天翻地覆的巨变之下,先生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当然不可能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这样的条件下,在Sieg教授这样的吐火罗文大师的指导下,再以成名作所呈现出来的已经成熟的方法,继续从事吐火罗文研究了。但是,已经留下了中国人足迹的吐火罗文研究这个奇妙的学术前沿毕竟是难以骤然忘怀的。大概,这就是先生用“藕断丝连”来形容回国后长达三十多年的这个阶段的原因。
然而,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并不那么简单了。从1946年回国,到1978年,在这漫长的三十二年里,先生写了不少文章,假如要和留德期间所发表者相比,先生心中真正感到满意的恐怕不会太多。尽管如此,《浮屠与佛》(1947)、《论梵文t、d的音译》(1948)、《列子与佛典》(1949)、《三国魏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1949)、《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55)以及两篇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论文,无论放在先生的学术史的哪个阶段,也都是佳构杰作。而在这些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吐火罗文研究有关。下面依次加以论述。
促动先生撰写《浮屠与佛》(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的,是胡适和陈垣关于“浮屠”和“佛”字谁先谁后的激烈争论。但是,先生的切入点或者说所凭借的技术手段首先是对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了解。正是由于先生知道,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在中亚各种语言里有不同的形态,特别是,在吐火罗文A作ptankat(pattankat一个更重要的形态),吐火罗文B作pūdnakte(还有pudnikte,pudnakte等形态)。根据吐火罗文构词法,可以将附加部分剥离,剩下的与Buddha对应的字分别是吐火罗文A的pta或pat,吐火罗文B的pūd或pud。这样,先生就有力地指出“浮屠”和“佛”不是一个拉长或缩短的问题,而是来源不同。当时,由于资料有限,没有能够圆满地解释p和“浮”、“佛”古音的对等问题,但是,用传统的常规手段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已经被先生引入的吐火罗文刺开了一个大口子,研究思路得到了绝大的拓展。终于,四十二年以后的1989年,先生根据新获得的大量资料,发表了《再谈“浮屠”与“佛”》(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这个问题。
《列子与佛典》(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照理与吐火罗文研究毫无关系,然而,先生还是在有关《生经》处的注12里引用了自己用德文发表的那篇吐火罗文专论。
《三国魏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英文本则收为该卷倒数第二篇)虽然主要引用的是汉译佛经和不多的梵文、巴利文佛典,但是,在说明“三十二相之次第因佛教宗派之不同而异”时,还是注引了当年的同学W.Couvreur的吐火罗文研究论著(Le caractère sarvastivadin-vaibhasika desfragments tochariens A d’après les marques et épithètes du Bouddha,Muséon, tome LIX 1-4)。这篇文章更是时隔三十三年后的1982年的《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的先声。
关于《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先生自己的评价是:“勉强可以算作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学海泛槎》,99页)这段话说明先生对“学术论文”悬的之高。先生一贯强调,“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同上书,311页)。但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新意的,不仅是“勉强”而已。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它指出,佛教初入中国时,佛典大都以中亚某一种“胡”语为中介,根据资料来看,以吐火罗文为最多。这就将尚未得到重视的吐火罗文的意义凸现了出来。从窄深的意义上说,它用丰富的资料证明,“恒(河)”来自于吐火罗文A的gank、吐火罗文B的gank或gan,“须弥”则来自吐火罗文(A、B同)的sumer。这些都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事实上,先生当时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的论据,上述两字仅仅只是举例。
由上可见,“藕断丝连”如果不是先生的自谦之辞的话,那么,只能说明,先生本人对吐火罗文研究在这三十二年(其实主要是前十年,即1946至1956年)里所占的分量做了过低的估计。
五 完美却未必是句号
1978年是再生的一年,是复苏的一年,是给我将近耄耋之年带来了巨大希望的一年。在这之前,我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的念头。然而,我却像做了一场噩梦突然醒来一般,眼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学海泛槎》,115页)
起初,先生并没有恢复吐火罗文研究的打算,其诱因是李遇春馆长亲自携来的1975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先生就像在当初决定是否要学吐火罗文时那样,没有经过太多的犹豫,接受了释读、研究的艰巨任务。随着对《弥勒会见记剧本》的释读、研究的推进,先生在延续了利用平行异本释读、确定残卷某些字义和语法形式,探索某些汉译字词和吐火罗文的关系等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以外,更将视野扩展到了中外古代戏剧关系等新领域。同时,还发表了多篇堪称“精品”的“副产品”。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副产品”。1981年,先生发表了《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指出新疆是全世界惟一的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因而有着丰富的比较文学的资料。先生在此文中举的惟一一个例子,就是吐火罗文A的“木师与画师的故事”(这个主题先生在1947年就已经关注了,见《学海泛槎》81页。先生曾在1947年5月24日写成,并于1947年5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0期发表《木师与画师的故事》,不知何故《文集》失收),而且,为了说明新疆特有的平行异本多的优势,先生再次展示了使用平行异本确定字义的方法。
次年,先生称之为“重头的论文”(《学海泛槎》,130页)发表。在整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过程中,先生偶尔发现其中多处有关于三十二相的记载。先生的兴趣自然不在于这些“相”,而在于吐火罗文本身。利用新博本的材料,加上既有的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吐火罗文三十二相表,再凭借对汉译佛典、梵文佛典中相关部分的参照,从而有助于确定一些字的含义。先生最为满意的是达到了对ela的确诂。前面曾经提到过,Sieg教授不知何以忽略了先生德译的关键词,在翻译这个字时留下了遗憾。以后,WolfgangKrause和Werner Thomas合著的《吐火罗文基础读本》(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 CarlWinter·Universitatsverlag, Heidelberg, Band I:1960, BandII:1964)将ela译成hinaus(出去)。现在,这个ela又出现在三十二相里,先生彻底证明了它相当于梵文的guhya、巴利文的guyha,确切意思是“隐藏起来”。
同年写成的还有《说出家》(写成于1982年4月20日,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又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不知何故,亦为《文集》失收)。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专业论文,在梵文佛经里,没有“出家”这个词,只有“出走”。但是,吐火罗文里却有“家”字。那么,是吐火罗文影响了汉文,还是汉文影响了吐火罗文?先生证明,后者是正确的说法,由此展现了文化交流丰富多彩的面相。同年还写有介绍性的《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1982年6月24日写就,后发表于《文物》1983年第1期,《文集》亦失收)。
1984年,先生写成了《〈罗摩衍那〉在中国》(和英译文一起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其中专节介绍了《吐火罗文残卷》(10-11)所收《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中木师与画师的一段有关罗摩故事的对话。同年,先生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了“吐火罗语”词条(发表时间为1988年,《文集》失收)。
长文《关于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写成于1988年(原刊于知识分子文丛之一《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文集》失收)。这是一篇在先生的吐火罗文研究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论文,它标志着中外戏剧关系成为先生非常注意的一个课题。先生自己所做的归纳是:“这篇文章颇长,讲了下列几个问题:一、吐火罗文剧本的情况;二、印度戏剧的发展;三、印度戏剧在中国新疆的传播;四、印度戏剧和希腊戏剧的关系;五、中国戏剧发展的情况;六、吐火罗文剧本与中国内地戏剧发展的关系。”先生还比较了中印戏剧的特点:“(1)韵文和散文杂糅,二者同;(2)梵文、俗语杂糅,中国有,但不明显;(3)剧中各幕时间、地点任意变换,二者同;(4)有丑角,二者同;(5)印剧有开场献诗,中国有跳加官;(6)大团圆,二者同;(7)舞台形式不同;(8)歌舞结合,同。”(见《学海泛槎》,218页。)紧接着,先生又撰写了《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这篇论文详尽独特,考察的问题是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如《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的异同,印度戏剧的来源及其和木偶戏的关系,从梵文yavanik?觀(“幕”,原意是“希腊的”)看与希腊的关系,中国戏剧的起源。最后,先生再次对比了中印戏剧的异同,基本和上文相同。
将先生吐火罗文研究的看家本领展示得淋漓尽致的《梅呾利耶与弥勒》(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学海泛槎》230页作“《梅特利耶》”,不确)发表于1990年。在汉译佛典中一直有“弥勒”和“梅呾利耶”两个形式。先生入手的思路一如《浮屠与佛》,但是,处理过程更为复杂精细。与梵文Maitreya、巴利文Metteya对应的字,吐火罗文A作Maitreya,吐火罗文B作Maitreyee,A、B里又有Metrak的形态。一般都认为,后者是从前者变来的。先生提出“Metrak是独立发展成的吗?”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问题,然后根据吐火罗文-ik构词法,判定Metrak、Maitrak与梵文Maitreya无关,是由梵文的Maitri(“慈爱”)加上词尾-ik演变而成的。因此,这才是汉文最早的意译“慈氏”的真正来源。先生排比了大量汉译佛典资料,归纳为:1.“弥勒”和“慈氏”同时出现于最早时期,即后汉、三国时期,“梅呾利耶”等出现较晚;2.在最早时期,同一译者,即使在同一部佛经中,随意使用“弥勒”和“慈氏”;3.历史上,“弥勒”和“慈氏”并行不悖。先生从中得出的正是自己一贯坚持的结论:“最早的汉译佛典的原本不是梵文或巴利文,其中可能有少数的犍陀罗文,而主要是中亚古代语言(包括新疆),吐火罗文恐怕最有可能。”(见《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242页)
同年,先生还写成《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文集》失收),解答了一些重要问题,指出此书是编译;基本上是属于小乘的佛典,但是已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印度戏剧的重要特征乃是朗诵和表演的结合。
上面我们说过,这些还仅仅是“副产品”。下面要评述的,正是两部重头著作。一部是1993年在台湾出版的《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这是一部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全面回顾总结吐火罗文研究的重要论著。内容包括:一、绪论 吐火罗语发现的经过;二、资料概叙;三、资料特色;四、资料价值;五、研究重点确定要点的原则。其中第五部分尤其重要,是先生几十年研究心得的提炼,是度后人的金针。下面分述:(1)确定残卷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单词的含义(举出四类实例,以及研究进程);(2)利用回鹘语《弥勒会见记》来解释吐火罗语本;(3)积累吐火罗语语法形式;(4)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之间的关系;(5)吐火罗语同其他语言的关系;(6)命名问题;(7)吐火罗语第三种方言——跋禄迦语。这是一部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入门书,也是进一步研修的指导书。有心者只要将先生的这部《导论》和WernerThomas的《吐火罗文研究史(1960—1984)》(Die Erforschung desTocharischen(1960—1984),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Stuttgart 1985)对读,就不难看出先生这部导论的全面、深入、重点突出、切实适用了。
另一本更为辉煌的巨著是吐火罗文研究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浩大的,对原典残卷的英译、考释、研究,也是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中树立的惟一一块丰碑。自从80年代初以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生的年龄从七十轻松地迈向九十,但是,先生手中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研究却是沉重的,能够接过这副重担的年轻学者尚未出现。先生用中英文,在国内外连续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的释读、翻译、研究成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在先生的为学术献身的勇气和毅力面前,后辈只有钦佩自叹了。终于,厚厚一大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独自成为了《季羡林文集》的第十一卷,其中包括厚达138页的中文的长篇导论,全面深入地探考了《弥勒会见记》及相关问题。还有厚达390页的英文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所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Museum,China),对《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存全文进行了转写、英译、考释、研究,编制了详尽的索引,影印发表了残卷的照相版。在国际著名的吐火罗文专家WernerWinter和Georges-JeanPinault的协助下,作为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语言学趋势·研究与专著类”第113种(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113),于1998年由著名的Mouton DeGruter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震动了吐火罗文研究以及印欧语言学界。这是一个宝库,对于它的消化远远超过了一篇文章、一部书的任务和能力。不过,这当然应该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年轻一代中国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六 冒号和几句台词
“冒号”云云,很简单,上述两部巨著各自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足迹,它们的合理组合是冒号,而非句号。我想,只要机缘凑合,先生还会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发言的。
“几句台词”云云,更简单:最近风靡一时的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中有一段戏,闲人马大姐想学点尽量古怪的东西,要和就读于老年大学的邻居孟大妈较劲,在学习了《诗经》、逻辑悖论等等而无效之后,终于靠向前楼“顾教授”学来的几句“吐火罗语”,彻底镇住了孟大妈。孟大妈佩服得五体投地,马大姐谦虚地说道:我这点哪行?吐火罗语有A、B两种,前楼的顾教授也只懂一种。“两种都懂的,只有北京大学的季教授。”并且表示,来日还要去北大跟季教授学两手。
先生,虽然那个“前楼的顾教授”一定是乌有先生,虽然至今为止中国还只有您一个人从事吐火罗文研究,可是,您孤独吗?
注:由于电脑原因,文中的字母无法按原文正确打出,特此说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