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花怒放”到“超脱莲花”
——论安妮宝贝作品风格的嬗变
景志萍
摘要:安妮宝贝作为当红女作家,其前期作品坚持黑色主题,“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充满小资式的自恋阴郁、颓废唯美的末世情绪,被人称之为“盛开在网络上绮丽诡异的伤花”。而后期作品《莲花》中,一改过去的阴暗晦涩,风格如作品所隐喻的“超脱莲花”的盛开,空灵清新、笃定明朗。《莲花》是呈现安妮宝贝写作转变意义的力作,我们看到安妮宝贝已走出其作品惯常的壁垒,呈现出大气与从容的开阔气象。
关键词:安妮宝贝小资情调颓废 嬗变
安妮宝贝作为风头正健的网络文学作家,其作品因其另类的书写而备受关注与争议,200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到后来的《八月未央》、《彼岸花》等早期作品集,都充满自恋阴郁、孤独颓废的末世情绪,爱情和死亡、告别和流浪等黑色主题被反复书写,给人一种绝望苍凉、敏锐疼痛的灵魂触觉。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简洁的文字里有伤花怒放,这些是安妮推崇的方式。”①但后期作品,《二三事》,特别是《莲花》中,一改过去的阴暗晦涩,而是空灵清新、笃定明朗。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莲花代表一种诞生,清除尘垢,在黑暗中趋向光。一个超脱幻象的新世界的诞生。”通过《莲花》,我们目睹了作者风格的成熟蜕变,从早期的暴戾与疼痛,到后期的淡定与自控;从早期的在个我的小天地里自伤自悼式的自恋,到后期的对生命、人生的自省与追索;从早期的阴郁颓废,到后期的包容忍耐,我们也目睹了莲花的“超脱盛开”。
一
作为20世纪末在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与安妮宝贝同时成名的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等最终放弃小说创作而投身商海或影视行业,安妮宝贝的文学创作一路坚持走来,在成为一位知名网络作家之后,彻底与网络脱离,创作直接指向纸媒出版,成为一个人气很旺的走红作家。安妮宝贝作品的走俏既有借网络的推动,也与她作品中特有的题材元素和写作风格分不开。
网络文学作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后现代文化的烙印,互联网所特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与文学的自由性相契合,给消解权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文学多元化展示的平台和桥梁。安妮宝贝的前期作品以自我的生存体验作为小说的底本,改变了经典文本的背景设置和叙事方式的审美情趣,将前卫的个人体验与消费社会的物质景观巧妙结合,使作品的书写形成一种和传统的人文主义书写所不同的网络文学书写空间,表现在作品上便是鲜明的小资情调。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在后现代文化空间中,在价值崩溃的荒原上,裸露的只能是人类的日常生活景象,人类通过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审视以获取前此未曾觉识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思想规则。”②“小资情调”正是藉此浮出历史地表,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语之一,“它有一定的社会学的阶层概念,但又不是严格的以经济收入来定义,而是更多地指向了某种“生活”的“文化”品味、情调与氛围。”③
安妮在作品中有非常突出的小资情调及其叙述元素:狭小而封闭的私人空间,耽于内心都市体验的生活,时尚、小资女性的自我沉醉和都市心灵漂泊,温馨的怀旧,网络或酒吧中的邂逅,气质、品位的互相吸引等。不同于同时代的卫慧、棉棉的小资情调中所透露出的对西方后殖民文化的迷醉与顶礼膜拜,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小资情调,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品味和格调,物质更多的是用来修饰人物气质而不同于卫慧、棉棉笔下欲望的狂欢和享乐的盛典,“他们最易受到指责的地方就是与市场机制的合流,这个阿喀琉斯之踵足以把满腔的激情化作撒狗血式的自欺欺人的表演,把晾晒内心的行为化为媚俗的自我拍卖。”④
安妮作品中的小资男人,无一例外地英俊睿智,穿白棉布衬衣,喜欢喝蓝山咖啡,听帕格尼尼的音乐,杂糅中西,商场气息和古典诗意交映、明亮和忧郁兼具。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明眸皓齿,千篇一律地是“黑色蕾丝内衣,一头黑藻般浓密的长发,松松垮垮的很大的牛仔裤。”或穿着“纯白色的棉布裙子,光脚穿白球鞋。”或“光脚穿着细细带子的麻编凉鞋。”尤其巧合的是她们“左眼角下有一颗浅褐色的泪痣。”这些男女主人公,代表着物质时代的某种萎靡而精致、桀骜而脆弱、狂野与低迷、犀利与诡异的精神气质。而作者在作品中也一再地强调主人公们抑或是自己的独特品位及爱好,象爱尔兰音乐、王菲的歌曲、纪梵希香水、梵高的蓝色的鸢尾花、杜拉斯的小说、哈根达斯冰激凌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物质经济的发展推动下,中国社会转向了一个注重生活享受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知识阶层,讲究消费品位、注重物质享受。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在90年代后进入大学的女性阶层,大多有浓郁的小资情调。安妮宝贝作品中的这种小资情调是随时代而生的,安妮宝贝作品的畅销也是与满足了小资们的某些梦想分不开的。“小资情调不排除对物质的享受姿态,但它又试图在物质昌盛到几乎淹没人的时代从物质的缝隙中竭力创造人性气氛的心理趋向,即将物质的存在合理化为人性的构成部分。”⑤安妮宝贝心中理想的物质生活是恬淡、不俗和个性化的。她推崇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一代青年人所共同向往的。安妮宝贝前期的作品中对物质的书写渗透着一种感性的抚摸,并力图在这种抚摸中深入探讨人性的丰富芜杂。
安妮宝贝曾说过:“我写的都是比较阴沉的文字,里面有很多黑暗颓废的东西。同性恋,谋杀,同居,艳舞,离家出走,漂泊,伤感,脆弱的爱情。”⑥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为灵魂的漂泊者。外表冷漠,内心狂野。隐忍着叛逆的激情。有沉沦的放纵。也有挣扎的痛苦。相同的是都受到焦灼和空虚感的驱使。从而一再踏上孤独的探索路途。”⑦正因为其作品中的人物的另类与叛逆,作品中以漂泊、死亡、疼痛、杀戮、变态、绝望为题材,使早期作品充满孤独颓废、阴郁诡异、华丽唯美的情调,不同于同时代卫慧、棉棉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在欲望和享乐中沉沦、粘软糜醉的颓废气息,安妮宝贝作品中的颓废大多来自于工业时代和现代文明喧嚣浮华背后都市人进退失据、真实而隐秘的心态。
戴锦华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曾这样评价安妮宝贝的作品:“在安妮的笔下,那(都市)是永远的漂泊的现代丛林,也是无家可归者的唯一归属。我为安妮笔下颓靡和绮丽所震动,在那里生命如同脆弱的琴弦,个人如同漂流中的落叶……安妮的作品展现了一脉大陆版的世纪末的华丽,一分灰烬间的火光的弥留。”⑧是的,安妮宝贝的前期作品正如网络文学这片园地中的一朵另类而诡异的“伤花”,怒放在网络上。
安妮宝贝的颓废是自我的颓废,颓废源自个体在时代、命运面前的无力,这是一个现代西方文学反复渲染的主题,颓废、绝望、伤感宣泄了一代青年在物质时代的无奈。安妮宝贝对生活的感伤是独特的,她写出了城市边缘人的特有的精神处境,安妮宝贝撕裂、放大了青春忧郁的伤痛,写出了一种残酷的美。严肃作家总是把个体真实的生存处境展示给读者,而通俗作家总是让人做梦,安妮宝贝的作品中饱含着小资情调的物质追求和伤感的情调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一份在急切的时代变化面前,一个边缘群体的尴尬与感伤。
安妮宝贝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因为她创造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安妮宝贝以她唯美华丽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大都市里边缘人的另类生存体验,但正像作者的自况——烟花一样,美则美矣,但是绚丽璀璨的绽放之后,却带给我们烟花不堪剪的寂灭虚无之感。这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主题的单调重复上,“然而另类的人和事不断被重复,相似的场景下的相似情节不断上演,叙述手法毫无新意,过度表达屡见不鲜,对于结构和技巧的无能为力造成叙事基调的庸俗化也是‘70年代作家’无法回避的硬伤。”⑨这一代际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留下烙印。安妮宝贝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有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安妮宝贝所有的作品其实是一部作品,有着大致相同的故事模式和故事氛围,基本相同的意义层面。作家最忌讳重复自己。安妮宝贝的所有的故事只是在讲述“一个名叫安的女子,一个名叫林的男人,他们辗转于不同的情结和结局,在时光和情欲的路上颠沛流离,始终未能逃脱宿命的手心。”而且生活体验的单一和艺术视野的狭窄,想象力的贫乏以及某种偏执本性使着其笔下可供开发的资源几近枯竭。
二
只局限于个我天地里的自伤自悼,沉溺于一己悲欢,与社会现实背景保持一定间距,对自身以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状况很难有完全透彻的认识与理解,对民族的百年忧虑,有巨大的疏离感、陌生感。作者未能从存在的意义上对心灵的伤痛做出某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宿命与破碎的家庭;也未能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对自身生存境遇提出卓有见地的反思与批判,只是个人经验及各种意象的感性呈现,“审美意象并非是普遍性的观念与生动的具象外在的拼凑结合,它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感性与理性、形式与意义相融合的审美化实体观念,也即黑格尔所说的实体性统一体。”⑩安妮宝贝作品中理性的缺失,使其作品所展示的人性缺乏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大悲悯、大关怀。不可避免地苍白与贫血,不可避免地走向阴郁与颓废,只会使其作品的路子越来越狭隘。2006年3月,安妮宝贝的长篇小说《莲花》出版,让我们看到安妮宝贝正在改变这种失血的状态。
《莲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源于一次危险切实的行走。这也即是它优于安妮宝贝以往的任意一部书的原因所在,而安妮宝贝前期的作品取材,正如作者所说:“爱情是我每一篇小说的线索。因为爱情是人性中最空洞美丽的部分。”所以安妮宝贝的前期作品中大部分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爱情,绝望苍凉的、脆弱伤感的、宿命无奈的、甚至暴力血腥的,而后期作品《莲花》中主人公苏内河、纪善生、庆昭之间却不关乎爱情,虽然女主人公苏内河与男主人公纪善生从懵懂少年便相知相依,耳鬓厮磨,同床共枕,长大成人后天各一方却依旧惺惺相惜,心灵相通,但却超脱了凡俗中简单的两性之爱;另一女主人公庆昭与纪善生在拉萨旅馆邂逅,结成生死相依的旅伴,经历种种艰难困苦,共赴传说中莲花的圣地———墨脱,但他们之间也同样无关乎爱情;即使是内河与美术老师之间的畸恋也无关乎爱情,而善生的两次婚姻也无关乎爱情,两任妻子都因他的无爱而离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宝贝已走出前期作品惯常的叙事巢臼。那些前期作品中以爱情为主题的情欲描写,在《莲花》中几乎没有,有的是玲珑少年、豆蔻少女的相知相惜;前期作品中那种颓废阴郁的创痛,从《二三事》已渐趋看淡与平和,到《莲花》中,作者的态度则臻于包容超脱,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作者个人的成长,经历的复杂,会有更宽阔的视野,这种转变是不言而喻的。
安妮宝贝前期的作品,充满个我的小天地中自伤自悼的小资情调与自恋情结,而在后期作品《莲花》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这种情绪的流露。《莲花》中作者已走出前期作品中小资与自恋的渊薮,转向对生命意义、人生真谛的追索与探寻。《莲花》对生命的内在和寓意作出全面的透视和自解,这种潜在而深刻的寓意,其实是一种积极和阳光的精神自觉。
故事分两条主线叙述,一条是庆昭和善生艰辛的路途,一条是内河与善生长达二十三年的相知相惜。那些少年往事在安妮依旧唯美的文字下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如同我们心中绽放的纯洁莲花,当樱花伤逝,青春散场,依旧驻留在我们怀抱珍惜与爱的心中。在内河与善生身上,体现了费洛伊德的“本我”与“超我”的性格结构。善生在内河那里,看到了一个“本我”,内河在善生那里,证实了“超我”的存在,他们长久地将对方作为另一个自己并与之交流、与之对峙。其实内河这个人物,从作品中作者对她出生前她母亲那个唯美的梦境描写,就寓意了某种生命的象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一条晶莹而汹涌的河流,它潜伏在我们心里,我们渴盼我们是她,然而在世事的纷扰中又任由它干涸。作者对内河的描写承袭了前期作品中女主人公残缺的家庭、桀骜不驯的性格,从而走向告别、流浪与死亡。而善生的命运在母亲的意志下打磨,压抑人性中的情感,无疑是一个主流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当繁华落尽,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善生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走上这条寻访内河的心灵之旅,而内河已于两年前去世。内河的葬生我们丝毫不意外,如同观看我们自身的消亡,但是不同于肉身的死亡方式,而是在我们心里留下伤痕。
善生与庆昭,向着传说中莲花的圣地——墨脱进发,历尽种种艰险,暴雨、蚂蟥区、山体滑坡等等,只为到达心灵的胜境。作者在此寓意了一种精神的向度,就象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如果任何一段旅途,都是一条主动选择或被动带领的道路,那么它应该还承担其他的寓意,是时间流转的路途。是生命起伏的路途。是穿越人间俗世的路途。也是一条坚韧静默而隐忍的精神实践的路途。”其实这个圣地就是我们心中的那朵盛开的莲花,那是我们的爱和信仰,我们行走在路程中,一直在追寻它。庆昭和善生、内河最后都殊途同归,庆昭获得新生,内河破茧成蝶,意味着在死亡中重获新生,而善生在庆昭的梦境中自杀身亡。安妮宝贝前期的作品写过很多表现死亡的黑色主题,诡异惨烈,而这一次却是在爱与光中走向涅磐。且作者态度淡然,并上升到对死亡本质意义的拷问。丰富的超越性与形而上意义上的哲学关怀,不是世俗的,而是超验的,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体的,而是站在了代言一代人的精神困境的高度上。
三
《莲花》是呈现安妮宝贝写作转变意义的力作,虽然作品也延续了作者的一贯写法:简单的人物故事,精神上有些残缺的主人公,幼年失父、家庭残缺是他们伤感的症结,在流浪的岁月中抚摸青春的忧伤和苦痛,接受生活的残缺,用在劫难逃来解释人生的波折,在漂泊中获得对生命真义的领悟。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莲花》的转变是精神上的提升,《莲花》让读者看到了人情的温暖和意义的追求,以及接受生命残缺的淡定与从容。《莲花》以另一种姿态书写对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关怀,表明作者力图超越自身的内省与审视。
上文谈到安妮宝贝的作品重复自己的缺陷,《莲花》显然是安妮宝贝不断重复写作的一个提升。从根本上说,重复是一个作家所不可避免的,好的作家就在于能否在重复中超越自己。一个人的精神记忆和个人性情决定了她能写什么样的作品,安妮宝贝习惯在简单的故事中写人物在情感中的纠缠,《莲花》也不例外,但超越了以往的所有作品。《莲花》中的主人公向心中的圣地进发的情节来自作者生活中的真实行走,这种对命运的自觉承担是生活的,也是精神的,作家不仅仅是在编故事,而是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自身切切的生命体验。正是对生命情感的尊重,作者才能将生活给予她的这份追求与梦想融化在作品之中,而避免了无关痛痒的伤感情调的泛滥与复制。当代的女作家铁凝、王安忆、张洁等都是以写纯情的童话世界走向文坛的,但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的积累,她们的作品对人性的审视变得丰富、立体起来。与这一代新时期初期走上文坛的女作家不同,安妮宝贝的起点是宿命与怀疑,是对生命劫难的忧伤,走向明朗和淡定必然是其作品走向多元、成熟、丰富的必经之路。《莲花》在精神残缺的主人公生命中贯穿了一个有目的地的行走:走向墨脱,走向主人公心中的圣地——莲花。这是一个鲜明的隐喻,构成了人物的精神向度,行走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们永不放弃心中的理想。
《莲花》的成功也体现在结构上的成熟完美,《莲花》将纪善生和昭庆的往昔经历和眼前的向墨脱进发历程相互联系在一起,现实的与历史的相互推动,构成了一个现代的剪接拼装文本,这种拼装的形式非常切合小说在简单的故事中潜入人物精神深处死结的写法,在面对旅途的困难时,主人公克服艰难困苦的巨大动力显然来自于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记忆。《莲花》的故事框架很简单,但安妮宝贝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忧伤和时时刻刻的对生命的体悟,充实了文本的内容,将小说写成了三个人物的心灵传记。安妮宝贝的这种切入人物内心世界的语言能力是在多年的写作中练就的,文中对人物生存处境的哲思的语言比比皆是,诸如:“必须接受生命里注定残缺和难以如愿的部分。要接受那些被禁忌的不能见到光明的东西。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无法占有的感情,无法修复的缺陷。”“我不觉得这个城市里能够有爱情。人们已经习惯把感情放置得很安全:掌握完全的控制权。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不表达对彼此的需要。不主动,也不拒绝。他们只相信自控自发的绝对行动。相信现金。相信时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以贸然的姿态靠近,那么将会被义无反顾一脚踢开。”这种充满思想火化的人生之思在安妮宝贝以往的作品中也经常见到,《莲花》中作者更是将这种凝思辩察的语言天才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自1998年安妮宝贝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开始,安妮宝贝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金子招牌,安妮宝贝作品的畅销更加坚定了她写作这种柔美风格的作品,她的“关注人性”的伟大理想,使她的作品在病态的忧伤的边缘人的故事中,隐逸了一份现代人的深思与梦想。安妮宝贝作品的畅销对她自己的影响是明显的,在《莲花》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写作更为孤立的事情。那也许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孤立的写作者,我一直不知道这种孤立原来是骄傲的。它是我自己的事情。”作为一个出道多年的作者,安妮宝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从一个年轻的网络写手成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成熟作家,《莲花》中的淡定与超脱显然是与安妮宝贝多年“骄傲”地写作的心态分不开的。《莲花》中还告诉了我们安妮宝贝写作的另一重秘密:写作“始终要带着疑问和对抗进行”。写作的成功,对人生情感的认识成熟,安妮对残缺人生的认识更是上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生与死,得与失,浅薄的痛苦与快乐,一向就只有薄薄的一层界面。”“你如何来界定一个人生活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属性,还是放任自流,或者哪一种更接近幸福的真相?生命各有途径,不管它最终抵达的目的是卑微还是荣耀。这是力量的控制带给我们的界限所在。”这些散落在《莲花》中的句子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愁结在安妮宝贝那里已经有了明晰的答案,《莲花》的明朗显然也是与作者随着年龄增长的成熟相联系的。
通过以上对安妮宝贝前后作品风格的阐述,我们发现安妮宝贝的作品《莲花》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早期充满阴郁颓废的自恋到后期的自省,我们看到了安妮宝贝的成熟蜕变,从以前对城市边缘人极端、另类、残酷青春伤口的展览到后期《莲花》的淡定与超脱,我们看到作者已走出前期预设的壁垒,走向大气与从容。沿此轨迹,我们有理由期待读到安妮宝贝更多更好的作品。
①⑥吴过:《桀骜不驯的美丽———网路访安妮宝贝》,《告别薇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②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谢晓俞:《安妮宝贝小说的另类视野》,《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④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⑦安妮宝贝:《告别薇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⑧戴锦华:《世纪末的华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6年6月13日。
⑨任南南:《宝贝物语——关于“70年代以后”作家的思考》,《文艺评论》,2004年第1期。
⑩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发表于《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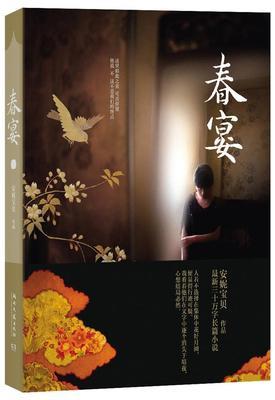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