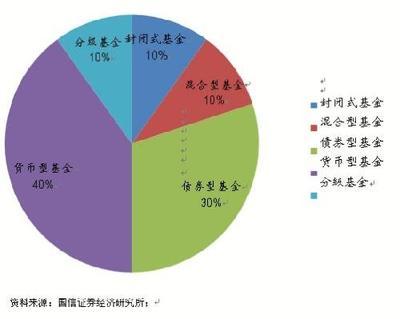《山海经》是一部谜书,而且有可能是中华文化史最大的一部谜书,谜得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读得懂它,直到我发现有这本《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
《山海经》是本什么样的书?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很多人就认为它是一本地理书,关于上古时期“世界地理”,顺便也和今天的“地理学”一样要讲述一下风俗民情的书。直到现在,“地理学”应该也是《山海经》研究的主流。
《山海经》还是本什么样的书?也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相当一部分人就认为它是一本神话书。这主要源于《海经》部分那些语无伦次文字下的那些稀奇古怪事物。试录《海外南经》几段文字为例:
“比翼鸟……,其为鸟青、赤。一曰在南山东。”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长野。在羽民东。其为人小颊赤肩。尽十六人。”
“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东。”
以上“比翼”、“羽身”、“连臂”、“长脸”等或人或鸟的东西,至少在有史可稽的人类文明历史上没出现过,由此,自古以来研究《山海经》者,很多就认定这是上古时期先民对神秘世界的想象。当然不能说上古时代的人们的想象力一定比我们现代人差,但任何的想象都要基于事实基础,那么事实基础又在哪里呢?
在找不到这些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学者就开始以学术想象力去应对他们想象中的古人的想象力。于是,神话学层面的《山海经》应运而生。至近现代,这方面的研究不乏大家,顾颉刚、鲁迅等尤其知名,再如袁珂先生以神话学为基础的《山海经》校本也随之产生。
我家里的书柜同时有袁珂校本的《山海经》,但说实在的,可能在于没有地理学神话学的基础,亦可能是我先入为主地把它当成是休闲消遣的玩意儿在读,我没读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亵渎”《山海经》的第二个理由倒是一以贯之,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的独盛,带有“舆地”性质的文献之研究,就只限于《尚书》中《禹贡》和《洪范》寥寥几篇,正史中的《地志》响应者已经是稀缺无比了。因而历史上被我们现代人冠以“地理学家”名号的郦道元、徐霞客诸辈,通通都有“不走寻常路”发自内心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但当初未必想以此成名没想到后来阴差阳错被标榜成科学偶像的经历。
地理学都如此,更莫论被经学思维——其中之一如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压迫在底层的神话学。历史中,在魏晋志怪、隋唐传奇、宋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学形态出现之前,那《山海经》就一直被文化人当作是不成体统光是满足好奇心的“怪力乱神”玩意儿看待。
尽管有这样那般的迷雾覆盖在《山海经》之上,但至少它的文本结构和叙事体例始终在,这也得感谢它“下贱”的地位——几千年下来没有人关心它的存在,自然而然就没有人去篡改它的内容。在中国“伪经”、“纬书”辈出的年月里,《山海经》很幸运地保持着它原始而神秘的身份。
要是仔细钻研这原始而神秘的身份,会发现,如果说《山海经》之《山经》部分显然还有那么一点古代中国地理学的轮廓外——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心的确是远古神州四方的山川、风物,那么若是把《海经》里面那些荒诞想象仅仅当作是神话来读,显然现代读者更主要的关注点就在那些稀奇古怪的插图而已——它们显得竟是这么奇怪,已经奇怪得突破了常理的底线。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先民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我们同样可以理解早期生产力不发达形态下对外来事物的考证失准甚而是失察的偏差,但我们绝对无法解释他们认为“神话”仅仅是吸引人眼球制造那些“出位”的视觉刺激的荒唐图画!
所以,《山海经》除了部分是一本地理书以外,它一定还是本另外意义的书——它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山海经》是一本“失落的‘天’书”。
《山海经》是“天”书。是的,“天书”这个词,我们现在运用起来一般是当作难以理解的文献资料来解释,是其引申义,殊不知,“天书”也有它的本来意义。“天书”,就是研究天文的书。
一下子就从“地理”跳到了“天文”,跨度好大!无须大惊小怪,古时候天文和地理正好就是一对双胞胎,地理还真不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来,它就得靠考察天文推演而得出来的,否则,就没必要发明“仰观俯察”这个词了。
《山海经》怎么和天文发生联系的,首先就是《大荒经》里重点讲述的七对太阳和月亮出入之山的坐标——“常羲生十二月”。
如果望文生义,“常羲生十二月”,哇,“帝舜的妻子常羲生下来了十二个月份”。这样理解错了么?不完全错,只是它忽视了“常羲怎么推导出十二月”的天文意义。不管是天文学还是地理学,我想最根本的元素之一就是坐标,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回到“坐标”去,即《山海经》的文本上去。
限于篇幅,除去上下文和语气词连结词等外,七对日月出入之山的名称,也就是它们的坐标点是分别是:东七座由南至北——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孽摇頵羝、猗天苏门、壑明俊疾;西七座由北至南:方山、丰沮玉门、龙山、日月山、鏊鏖钜、常阳之山、大荒之山。
不用管文字,只要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比如判断每一天黄昏将至会说成是“太阳落山”,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月份里,太阳究竟要落在哪一座山上还不一样;还有一定历史地理常识——比如说知道中国在地球的北半球,而太阳光从南面的赤道直射过来,而古代中国地理都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道理,显然,以上十四座名字怪怪的“山”,几乎肯定就是古人观天授时的“坐标”。
是啊!古人不笨,他们知晓地球运行轨道和太阳运行轨道夹角,也就是赤道和黄道夹角的问题,也许他们还没有南北回归线的概念,但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山脉,来规范太阳终年活动的“视域”。
也就是说,上面那十四座坐标之山,就是太阳做周年运动的“场域”,它们同时也是《山海经》中“大荒”世界人们观测暑来寒往的最直接证据:上半年,冬去夏来,太阳从南到北,从最南面的“大言”山逐渐移到最北面“壑明俊疾”之山。夏至时,太阳到达最北面的一座山之后,下半年,又开始调头南移,从最北面的“方山”逐渐移到最南面的“大荒之山”,于是,暑消寒长。自然,位于东西坐标中间的两座山:东面“鞠陵于天”之山和西面之“日月山”,其天文学意义也一目了然,二者就是“春分”和“秋分”。
可见,《山海经》之《大荒经》不是神话,它是一本天文书。古代中国以农而立,先民们尤其重视天体运动对地理亦即农业生产的影响,因而除了对天文学意义重大的“二分二至”的测量外,还要“计时”。时怎么计?由谁来计?说出来可能吓人一跳。它是靠“夸父追日(影)”去计!《山海经》里首先出现夸父的形象,原来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天文学家。
想一想道理也简单,古代人没有钟表,老百姓的计时系统考官方制定——说到底是由体制内的天文学家说了算。《失落的天书》对《山海经》的还原,夸父被除魅破解了神性是一例,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射掉了九个太阳的大英雄后羿和那颗挂有十个太阳儿子的大树一起仅仅是早期的“日晷”,西王母不过是丰收日子上为助兴而跳大神的女巫,而被越穿越神的西方的不老仙山昆仑也只是古代天文台——“明堂”而已。
在夸父、后羿、西王母、昆仑山被摘取神秘外衣的同时,《山海经》在整体上也顺理成章被去妖魔化,前文所举什么比翼鸟、羽民国,竟然只是古代先民观风的鸟羽表竿——原始气象台!什么二八神、毕方鸟,竟然只是古代先民祈雨的乐舞方阵——原始合唱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