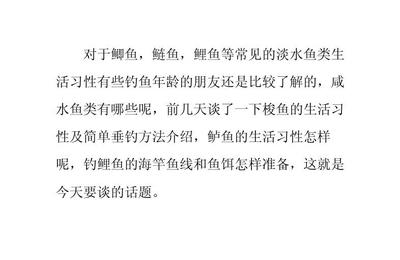——曲江系定义了这个时代的罪孽之后,我们是否可以直接、独自面对佛祖?
因为,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如果世界上存在罪孽的话,也是剽窃来的。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
——奥斯卡·王尔德
我的朋友林向松居士,在《不要让佛陀再流泪》一文中引用了一段“佛和魔王波旬的对话”,意在讨论曲江系对法门寺犯下的罪孽。
整篇文章,情真意切。当我读到良卿法师在文革期间自焚保卫佛指舍利之处,感动到流泪抽泣。
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消化这篇文章传递的信息。我也一直在想,“抵制法门寺景区,要求舍利回家”公民联署行动,最终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受到林向松居士文章的启发,我得出一个结论——除了坚持抵制到底,我们在这个抵制的过程中,应该准确地去定义这个时代的罪孽。
把曲江系的罪孽跟魔王波旬相提并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样,佛教徒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罪孽的大致形状。
不过,在此,我愿意对林向松居士的定义做一些补充,目的是更加精确地“刻画”这个时代魔王的形状、性格、习性。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知己知彼,让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去跟这个新魔王进行攻防战。
简单的说,我想引进天主教的“赎罪券”概念,来重新定义魔王波旬的性格。
原因是:魔王波旬的性格里面,缺少“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仔细考察曲江系对佛指舍利的挟持、绑架、销售、包装……我们就会发现,曲江系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魔王波旬所没有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基因。
这也难怪,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引进了西方国家太多的资本主义的方法,好的坏的都引进了。“甚至是罪孽,也是剽窃来的。”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成功引进可以制衡邪恶的三权分立,以及言论出版新闻宗教等自由。所以,我们把“婴儿和洗澡水”、“西式现代化和西式罪孽”一同引进的时候,忘记了,或者故意没有引进可以遏制罪孽的机制,清理污水的机制。
我这么说,不是要否定引进资本主义,我本人是亚当斯密经济学著作的忠实读者。我想要表达的是:魔王波旬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纯种的魔王,他已经是西式罪孽和老波旬的混血儿。
关于波旬,林向松居士比我更有资格去论述,因为他是一位佛教徒。虽然我是一位佛教迷,但是还不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我想重点谈谈“剽窃来的罪孽”。
“中世纪晚期,为筹措资金,当时的罗马教廷授权神职人员前往欧洲各地售卖大赦证明书(由羊皮纸制成的“纪念证书”,即通常意义上的赎罪券)。大赦沦为当时教会之敛财工具,本已矛盾重重的欧洲社会被激起动荡,更引发宗教改革,并最终导致基督新教的产生。”
想想看,曲江系挟持佛指舍利,进行敛财的行为,的确跟欧洲中世纪的“赎罪券”有几分相似。法门寺景区120元的门票,109元的开光粽子,600元的几碗凉皮,28880元的长明灯,5万元一个单位的阴间地产单位,60万元的功德碑,100万元的佛龛供奉费用……更像是对中世纪“赎罪券”的进口和进化。魔王波旬仅仅给曲江系供应了邪恶的血液,但是纯种的波旬应该没有这种财务上的智商。
如果我们认定这种罪孽除了有波旬的血液,也有中世纪“赎罪券”的基因。那么我们的抵制行动就应该引进马丁·路德的一些方法。
路德认为,“上帝最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上帝单独对我说话,使我成为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个人,在我与上帝之意,没有其他人和人群。”
根据路德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呼吁佛教徒独自面对佛祖,我们是否能够相信佛祖最重视的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佛祖可以单独对我说话,使我成为直接与佛祖建立关系的个人,在我与佛祖之间,没有其他人和人群?我们不需要曲江系这个中间商。
既然佛指舍利已经被曲江系劫持,我们就不要进入法门寺景区。甚至连10元钱的翻墙的租用费也不需要支付。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与佛祖建立联系。
我们抵制法门寺景区,并不会妨碍我们跟佛祖的关系。反而,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拉进跟佛祖关系的一个契机。
我想佛祖也不会希望大家仅仅执着与他遗留下来的“佛指舍利”。连十恶不赦的屠夫都可以“立地成佛”,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绕开曲江系,在内心中与佛祖直接连线?
我们不需要购买曲江系120元的门票,我们不需要花109元购买开光的粽子,我们不需要曲江系这个中间商,这个像罗马教廷授权的神职人员一样的中间商来代理我们跟佛祖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需要给曲江系缴纳通往佛祖之路的过路费:那28880元的长明灯、5万元的阴间地产单位、60万元的功德碑、100万元的佛龛供奉费用……所有这些代理费用,其实从来没有得到佛祖的授权,甚至也没有得到佛祖弟子的授权。看看2009年法门寺僧侣愤怒地推倒景区围墙,我们就知道,这些过路费不是佛祖及其弟子认可的。
我想听听林向松居士、布衣诗僧、马鸣谦先生……的看法——我们是否可以参照路德的方法——直接、独自地面对佛祖?
在佛教的历史上,是否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劫难,最后又是否曾经找到过比较智慧的新方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