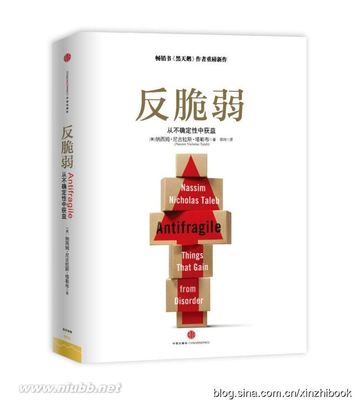人 心 不 古
──读池益岓《生如夏花No.1》之感想
要死的人用最后一口气通知每一个人,
我是他顽固的敌人。
人类,正在一个病人的统治下,
非直立行走。
──张殇裳《人与鸟》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董存瑞、刘胡兰、阿Q、海子、顾城……他们有的是自己找死,有的是被人杀死,有的是自己杀死了自己。董存瑞死得最痛快,刘胡兰死得最豪迈,阿Q死得最爽快,只有海子、顾城死的不明不白。
我小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离奇的梦,我梦见我掉进一口大菜锅里被煮死了,随后我哭醒了,看到天还没亮,玻璃上的霜花被鬼舔开了一个黑洞,原来是可怕的鬼前来捉我,而我几乎无处可逃,吓得大喊一声……虽然这是梦中之梦,都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梦到我死。
古往今来,死于非命的人实在不计其数,有的蒙冤遇害;有的殉情自尽;有的因病而亡;有的罪该万死;有的死得其所;有的死有余辜。在现实中,我几乎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可是,若说我也有罪但我罪不该死,若说我想殉情可我无情可殉,若说我遭迫害我却没有仇家,若说我被图财害命我又无财可图,若说因病而逝我竟然健康得不像患者。
如果命中注定我这一生不可能病死老死,而必须提前死,我相信我既没有董存瑞式的魄力,更没有刘胡兰、阿Q式的胆识。我只能做逃兵或叛徒,不可能当英雄或烈士。另外,我也没有勇气像海子那样卧轨,像顾城那样上吊。我始终认为,通过暴力无论消灭别人还是消灭自己,都不可取。
当我看到池益岓的人物雕塑《生如夏花No.1》,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死亡,其实是一种鲜艳的娱乐方式,远比庸庸碌碌地活着高尚得多。人生在世,不是庸庸碌碌就是忙忙碌碌,都没多少乐趣可言,尽管可以饱尝一番世态炎凉。池益岓的作品普遍有一个明朗的特征,把人的本身以及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畸形与失衡,通过他独特的触觉突兀出来,每每令人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继而把世人的种种情态与境遇分别予以展示。例如那件让我难以释怀的《生如夏花No.1》,把人本身在迷惘中的觉醒、抉择后的欣慰,发掘得淋漓尽致。
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虽然也表现了人性的一种内在的律动,但是只能让人对眼前的世界更加惊恐与无奈。而老池的作品则能让人从中更加立体更加生动地读出世界的多面性与生命的多重性,在忘我的解脱之际享受额外的快感,体验出魂灵的升华与鲜血的甜味,而不是那种蒙克式的落落寡欢。那股残酷且乐观、深刻且直白的格调,正是他帮助我们找到了别人熟视无睹而又正在苦苦寻觅的地方,那是一处人人可及,却又辗转反侧的疆土。我同一个没与我上过床的女性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泰然自若,而且津津有味,就像我们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样,并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她说她听说在水里割脉一点也不疼痛,她最欣赏那种方式。亲眼看着自己的血从自己的身体里面一点一点流出来,把水渐渐染红,直到把血流干,多浪漫呵!我们那次所设想的方案无论多么唯美,只是我们一直也没实施,恐怕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看似很残酷的情景,竟然如此美丽与畅快。
数月之前,我在宋庄老田的艺术空间首次见识池益岓的《生如夏花No.1》,顿有一种共鸣开始隐隐约约缠绕着我。我深沉地抚摸着主人公用斧头在自己的脖子上进行的再创作,虽然我的左手没被鲜血染红,但我分明已经嗅出想象中的血迹散发出来的水果的味道。因为主人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且知足的微笑,潮水一般一波一波提醒了我。那种提醒,不是诱惑我们用斧头砍断自己或者别人的脖子,而是鼓励我们眉开眼笑地面对一切:空气其实是甜的,脚下的路也是甜的。头顶的太阳,角落里的阴影,通通都是甜的。在街头乞讨的残疾人、在垃圾筒里翻弄矿泉水瓶子的拾荒者、为男人提供有偿服务的女大学生、吃苦耐劳的民工,他们原来都是那么美丽,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了。
《生如夏花No.1》中的主人公在看似自残的过程当中,仿佛是个淘气的孩子,在他脸上看不见凄楚,读不到悲伤,对方几乎由此真正抵达了极乐世界。死亡并不恐怖,而是一种凄美的境界。人走的路各是不同,活法亦有区别。可是,又有几多情愿?又有几多亢奋?
我和朋友曾连夜探望过一个精神失常的患者,患者虽然还能认得我们,却已口不择言,声称他将统一所有的宗教,而他就是真正的主。我们在归途上对其嗟叹不已,命运无休止地捉弄我们之际,竟能让人有如此的雄心壮志。
我那个的朋友想起一句诗来:
君弹天上瑶池曲
我抱琵琶地下听
朋友说有一年他回老家探亲,返程之际一个同学塞给他一张纸,纸上写的就是这个句子。当时他很奇怪,可也没去多想。直到听说那个同学在自己的身上绑了炸药引爆身亡,才感触到那句诗的意味出来,开始反思该同学的言行举止。唯一的不同处,就是该人沉默寡言,也不与谁同餐共饮。另外,我的朋友还乡之时整日忙于各种应酬,基本上忽视了他那个同学的存在,于是没与那个同学做特别的沟通。死者的动机不明,成了一件憾事。
美女画家张殇裳在她的诗中声称“要死的人用最后一口气逼死每一个人,”明明告诉我们,虽然人总是要死的,其实都是被逼死的。甚至连上帝也在逼迫我们。在温热的沼泽地里,只要把眼睛似闭非闭,就能洞察许多不协调的情形,连一些海岸线,都会显得营养不良。如果大脑失灵,哪怕用老二想一想,也能知道有些事情像猫叫春,人也痉挛得不男不女。广场上的假面舞会惊动了酣然入睡的蛇,我们经历着忍无可忍的浮躁,本来挺葱翠的思念抽搐得弱不禁风。童年时的星空长满青苔,僵硬的梦魇与秋雨乱伦,泪已流尽,只剩下了虔诚的苦笑。一个少女花枝乱颤地与嫖客交媾,另一个少女眼巴巴地跃跃欲试。教主手忙脚乱地唱着颂歌,敌人咬牙切齿地念着咒语。一阵喧嚣的风刚刚掠过,又刮来另一阵风……
我们挣扎于这荒诞的棋盘上,董存瑞、刘胡兰、阿Q、海子和顾城等人的最后一刻,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性质的产物,都已在我们心里栩栩如生。人的生命在自己的身上,会比泰山还重。在别人的身上,却比鸿毛还轻。虽然比鸿毛轻,也能牵动人的心思。就如老池制造的醒世作品《生如夏花》系列,足以启发我们在混沌中如何跋山涉水,以各自的姿势积极地在死亡中复活,让自己生如夏花,完成一种定格。
完稿于2008.11.10.卧夫
卧夫与雕塑家池益岓。(池益岓的雕塑作品《生如夏花No.1》目前已由卧夫收藏,该作品近期将由中国美术馆展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