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上课孙玉祥
现在大学里教授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本科生上大课,那简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上课铃响就得进来,否则算迟到;下课铃响就得出去,否则算拖堂。一节课讲什么,一学期讲多少,那全有大纲规定,讲不完算没完成任务,讲多了算跑马观花。其他诸如口齿不清呀,离题万里呀,上课抽烟呀等等,都算违规违纪,轻则批评教育下不为例,重则下岗待业另找饭碗。
以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不是这样,要按咱们现在的规定,那时的教授上课自由得几乎就是逛自由市场。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上下课时间和上课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时,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放在讲台上,他自己呢,则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着讲着,就点燃烟袋,在吞云吐雾中阐释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而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到了五月十五晚上,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他不但上课时间自由,讲课内容也随心所欲──在教《昭明文选》时,他老先生游哉悠哉,一学期才讲了其中《海赋》的一半内容!与此相似的是联大另一教授闻一多。他上课不喜欢在白天,而是要调到黄昏时候上,理由是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而且,上课时他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在讲台上坐下,也会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
不过,刘、闻二人调课也好,吸烟也好,一学期讲半篇课文也好,他总得讲,总得开金口发玉音。可有的教授根本就不讲──比如,叶公超教授。他上课更是奇特:一上堂,他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如果有人回有问题他是不是就该讲解了呢?也不讲:当有人提问题时,他的做法是大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当学生查字典也查不着,小声向他请教──“这个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回答:“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还是不讲。沈从文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时,也是讲了10分钟就无话可说了,结果,他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么着把1小时混过。学生于是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耳朵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还有人更绝,借口天气原因根本就不来上课。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课没有上多久,绰号倒先戴在了头上──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校方居然同意,于是,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更出格的是,这家伙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居然嬉皮笑脸对大家:“这里有个知识点,我研究了多年才弄清──专靠学校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至于其他口齿不清──比如周作人,比如朱希祖,比如顾颉刚……就更不是问题了,照样名教授,照样高薪水。
今天教授上课的严谨和过去教授上课的稀松,是不是就造成了过去教学质量不如今天呢?每一个对现代学术史现代教育史有了解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答案──毕竟,自由,才是学术繁荣的充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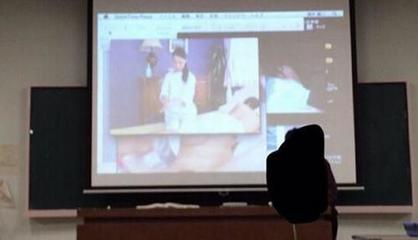
本文选自2010年7月27日《杂文报》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