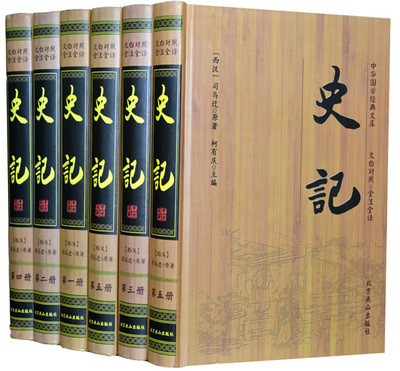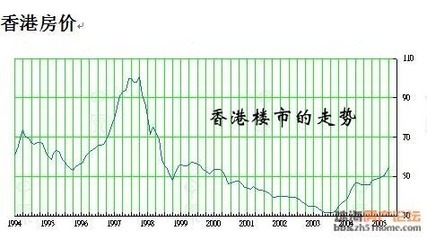“哐铛!”,陶瓷的裂碎激烈绽响。竹清用冷漠的眼神目睹那一盆仙人掌,翻惊摇落。一地碎瓷旁,泥土稀稀松松,散懒铺开去。而那株仙人掌垂着头,默读她的忧伤。竹清俯下身子,自言自语,为什么,别人都碎了,你却没有。难道你比谁都坚硬?可是,没有人回答她,四周出奇安静。
那盆仙人掌是戴沐白送给竹清的。竹清曾经问过戴沐白,为什么要送仙人掌给我呢?他应声回答,像你啊!
对于这种长满利刺的植物,竹清是陌生的。可是戴沐白一脸坚定,将它郑重地递到竹清的手心里。竹清接过手,内心夹杂。竟然是仙人掌呢,在他的心中,她不是玫瑰,不是蔷薇,她是一株仙人掌。想当然,她带着刺。
别的花朵渴求一切滋养,她不屑。而那时,他执意要做她脚下的泥土,为她耗尽所有。这株仙人掌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带着他对她信誓旦旦的诺言,一心祈祷地老天荒。可最终,他还是疲惫了。故事的结束并不需要轰烈的理由。仙人掌只习惯孤独,时间久了,一切不再似绸缎般光滑。
精疲力竭后,他不再日以继夜地追随。他离开了,被泥土遗弃的仙人掌原来无法独活。
不久后,竹清和戴沐白仓促的相遇。抬起头,竹清尽量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眼神瞥视。那一瞥,犹如五雷轰顶。戴沐白挺拔的身旁有一个女生。那是一朵无色的兰花,听说她叫楚涵。他最终还是选择让自己好好过。竹清昂起头,骄傲地掠过。她是朱竹清,她从不认输。
擦身那一芒,戴沐白微微别过了头。竹清用清冷的目光直视,他却避开去。那一刻,竹清看清了他眼里的闪烁。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可是,孩子从不承认自己犯错。
谁都明白的,有些事情,没有反悔的余地。
夏末,运动会的季节翩然来临。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被簇拥,除了3000米。操场绵长的跑道,在这种时刻有些可怕。班长一边一边苦口婆心,可是却没人响应。“小涵可以。”一个悠扬的男声划破一片死寂。于是,所有的目光聚焦。楚涵在戴沐白的鼓舞下战战兢兢地起身。戴沐白站了起来说,她可以的,小涵可以的。他用一种很柔软的微笑。他的脸颊如同春日里绽开的花苞。竹清坐在墙角,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竹清也开始笑,她仿佛听见一阵群鸟滑落林间,发出撕锦裂帛的声响。然后,她也站了起来,她说,我也可以。
四周,吃惊,喧哗,此起彼伏。
竹清直视着戴沐白,她清冷地微笑,执拗地挑衅。戴沐白的双眉带着忧愁的凹陷,他叹了口气别过眼去。
小舞拉了拉她的衣袖,暗自叹息。竹清是真的伤心了,小舞想。
运动会那天,天蓝蓝的,竹清仰起头,看到一朵朵云,云朵如浪花般浮动。
那头,广播开始频繁地报幕,周围人群骚动。对面,戴沐白用细腻的眼神与楚涵对望,那么深情。忽然,心被挑了,一阵潮起潮落。竹清深吸一口气,伸出手用力地绑紧裤脚。忽然,戴沐白走了过来。他说,你加油。小舞拿着矿泉水在一旁冷言嘲弄,不劳您关心,您去关心您容易受伤的小鹿吧。竹清抬起头,很生疏地笑。她没有应话,拉着小舞昂头而去。
3000米,原本是件望尘莫及的事。报名,只为一口气。她亲眼目睹戴沐白对楚涵说,你可以的。那么真挚一语,不是对她,是对楚涵。心,已经凉透了。竹清明白,曾经的曾经,真的已经擦肩而过。
起跑线上,选手们拥拥挤挤。竹清身边是楚涵。楚涵的眼神冰冷,她使劲地用手肘将竹清挤到身后。竹清忽然发现,这个女生并不像她的外表般柔弱。3000米,没有个人跑道,没有清晰的起点,所有的人只能纷拥,推攘。竹清淡漠的眼神扫过人群。人群里,金发邪眸的戴沐白,像一朵闪眼的踟躇花,落落而立。此时,他的眼睛里只有楚涵。他有十分的焦虑,却没有一分为自己。就那一瞬间,竹清忽然想哭。
哨声鸣笛,选手们箭步如飞。竹清卖命地跑,在一瞬间,超过了楚涵。她可以输,但绝不能是楚涵。很快的,楚涵的身影划过竹清的眼界。此时的楚涵有一种很凌厉的表情,只是除了竹清,谁也看不到。
她和竹清忽前忽后地跑,这场比赛几乎成了她们的独场,不断地超越和被超越。这好像是一场一无止境的赛跑。竹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拼命,其实,早在赛前她就输掉了筹码。
忽然,竹清的脚被绊住。一跌一宕后,只见两个帛锦般的身躯,摇转在尘土里。竹清的脚肘疼痛如针锥,咬着牙不让自己落泪。而一旁跌坐着,嚎啕大哭的楚涵。一小顷后,班上的同学纷纷围密过来。最先的是戴沐白,他看看竹清,又看看楚涵,一个生硬如石,一个柔软如柳。
谁也没有开口,可是楚涵哭得天昏地暗。很明显的提示,她,朱竹清绊了我,不怀好意。竹清抬起头,望着戴沐白,她的眼神拥有铺天盖地的锋芒。竹清在告诉戴沐白,她没有。忽然,脚肘一阵刺痛。竹清紧紧皱了一下眉,疼痛忽然来袭。竹清坚硬的身影淀进戴沐白的眼里,在水光里一圈一圈荡漾。戴沐白俯下身子靠近竹清,他说,你没事吧。
那一边,楚涵的哭声突得划破天际。戴沐白转过身子向她望去,在竹清薄暮般的眼神下,挣扎片晌,最终他还是走向了楚涵。
楚涵的眼泪就珍贵了吗,流出来的眼泪才有价值吗。竹清咬着牙站了起来,疼痛蔓延着疼痛,她坚硬的身心早已溃不成军。竹清拒绝一切的援助,挺直身躯,一步一步往前走。戴沐白和楚涵的身影像是透明般被暖暖漠视而过。
竹清漫无目的地走,耳边有群鸟疲惫的撕叫声,一切伪装的坚强像天空一般从蓝转灰。
第二天,竹清和小舞看到戴沐白和楚涵成对的身影。楚涵穿着棉布的连衣裙,在戴沐白身边飘来荡去。小舞撇撇嘴说,戴沐白他什么眼光,她还真够俗。竹清昂起头,拉起小舞的手,从他们身边飘摇而过。竹清雪纺的裙摆,像雾里的薄纱,淡蓝蓝的天空忽然一阵姹紫嫣红。竹清的眼角高傲,一切全当漠视。她有鲜花,有掌声。她很美丽,她很出彩,她被很多人簇拥。她告诉自己,在戴沐白面前,她永远也不要失去骄傲。
只是眼眶还是湿了,叶子卷起了孤单的手掌,黏稠的液体很静很静地散开去……
午餐的食堂里,人烟沸腾。不远处,戴沐白和楚涵笑语而来。小舞冷冷哼哼地说,有必要这么招摇吗。还真以为是神雕侠侣啊!竹清沉闷地笑了笑,一阵苦涩涌动。穿这么长的裙子拖地啊,最好她绊一脚,小舞将餐盘狠狠砸在餐桌上。竹清望着小舞,忽然觉得,友情的感动才可以地老天荒。要是楚涵真的绊倒了会怎样,菜汁会喷到她那条碍眼的长裙上,而她会一脸彷徨无助地哭泣。而戴沐白,他会心急如焚吧。保护会让人拥有成就感。
想着想着,竹清的胃口大失。她站了起来。恰好和他们撞个满面。楚涵的双手一抖,一盘的饭菜很准确地倒在竹清身上,美丽的雪纺裙,刹得一片污渍。
她,是故意的。餐盘哐铛落地,坐着的小舞像猫一般飞扑过来。小舞骂骂咧咧,你不长眼啊你!你故意的你!楚涵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呜咽一声躲进戴沐白的身后。竹清看着戴沐白,戴沐白一脸尴尬。他说,竹清这怎么办,赔你一条好吗?竹清生冷地一笑,字字顿顿,不用,脏了就扔。竹清转过身子,在一片喧哗中,独自离去。
即使狼狈,她眼神破绽光芒。裙子脏了又怎样,没有了戴沐白又怎样,楚涵不用指望看她的笑话。
冲出餐厅,天空忽然倾盆大雨。眼前,一片片迷蒙,终于眼泪可以悄悄释放。天空暗自收割着寂寞,一片光华不再,泪却已成河。每当看见他们,竹清都好想闭上双眼,不让疼痛泛滥。可是,即使闭上双眼,她也不能假装那个笑逐颜开的男生,不是戴沐白。
竹清在暴雨中不顾一切地跑着。很早的时候,他对她说,她是一株仙人掌,习惯刺痛。他曾是那么溺着她,无论她是多么的刺厉尖锐。曾经,那个温暖的微笑真真切切的属于过她。可是现在一切成了镜花水月,他只会对楚涵微笑了。那么,她又怎么拿别人的镜子去照自己呢?可他不知道吗,仙人掌虽然有坚硬的刺,可是内心却及其柔软。剖开来,全是稀稀的水呐。她快淌干了,悲伤依旧那么深刻。
竹清飞奔回家,换掉雪纺裙。她打开窗,将裙子狠狠地抛出去。雨依然在下,淡蓝的雪纺裙落地,仿佛尘烟乍起。竹清背过身子,泪流满面。
每一个女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可是,她的王子骑着白马飞走了,飞到了彼岸,他找到了他的新公主,可他忘了,其实她还在这端痴痴的盼,而那头,人早已不在。
星期天的清晨,晨露迷蒙。远方,飘荡着熟悉的歌谣,唤起雪花般的记忆。落叶枯瘦,带着遗憾凋零。而分离,其是无法逃离的宿命。
竹清立在窗边浅浅叹息,秋天了呢,气温变化无常,那般恰似人心。现在,戴沐白在做什么,他一定正陪着楚涵,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竹清在无数个清晨挣扎着想起戴沐白,手心一阵寒冷。竹清深深呼吸,抬头眺望远方。家对面的香樟树下,立着一个少年。心口忽然一阵激烈地疼痛。竹清的眼眶忽然丰盈泪珠,不是她的王子,为什么还要替她守候?
第二天,竹清走进教室。教室里,人烟沸腾。当竹清走进后,却又鸦雀无声。竹清抬起头,迎上了楚涵怨毒的目光。竹清冷漠地撇开,转头望向戴沐白的课桌,坐位空空。竹清皱了皱眉,坐回坐位。小舞忽然塞给竹清一张纸条。竹清摊开一看,清晰的字体不断放大:他们分手了。竹清手一抖,摆在一旁的水杯被碰撞,哐铛一声,洒了一地。
竹清冲出教室,天空一阵雷声隆隆。抬眼,是戴沐白。戴沐白一把拉住竹清说,我们谈谈好不好。竹清细细望着戴沐白,曾经英挺的少年,如今日渐消瘦。戴沐白,他过的一点也不好。他说,竹清,你还好吗。心忽然被疼痛扯裂,竹清在漫天的落叶中望着戴沐白,而曾经的风景已不在。为什么要问我好不好,谁在乎,竹清应声。戴沐白直视着竹清,很认真很认真地说,我在乎。他说,竹清,我知道有些可笑,可是我,戴沐白顿了顿说,我,真的很在乎。我在乎你过的好不好,在乎你的微笑失去了方向,在乎你望着我眼神薄凉。一瞬间,竹清的眼泪崩离眼眶。秋叶暗动,载着眼泪飘零。可为什么,为什么事到如今要对我说这样的话,戴沐白,你真的很过分,竹清躬下身子,泣不成声。
她该昂起头,嚣张地往前走,竹清想。可是竹清一点也不快乐,矛盾过于纯粹,她不过只为一口气。背过身,她坚硬地昂起头,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戴沐白,你知道吗。在希腊神话中,每个祭祀女神都拥有一个守护神。他会张开羽翼誓死保护着女神。当守护神收起羽翼背叛后,他会被永远驱逐。戴沐白,你被驱逐了……
回到教室,小舞一脸担忧地飞扑过来。竹清环住她的肩膀说,没事。小舞笑逐言开,那是,那是,虎狼岂能被犬羊欺。
竹清也笑,一切云淡风轻,只是有一点落寞,正中红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