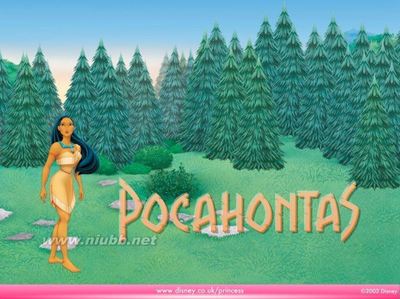北冥有鱼(逍遥游)
原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译文:
北方大海有一条鱼,名字叫鲲。鲲鱼不知有几千里之大;变化而为鸟,名字叫鹏,鹏的脊背不知有几千里之大;它奋起而飞,双翅如同天边的云彩。这只鹏鸟,在海上飞行,将迁徙到南方的深海去。南冥这个地方,是一个天池。齐谐这个人,是专门记载奇人异事的人。他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深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浪涛,振翅拍击着旋风飞到九万里的高空,离开了北方的大海,花了六个月才飞到南方的大海停下来休息。”春日野外林泽中蒸腾如奔马的雾气,是飘荡于空中的尘埃,它是生物用气息相互吹拂的结果。天空的深蓝色,是天空真正的颜色么?天空真的远得无所至极么?鹏鸟自上而下察看,也得不到真相啊。而且水积得不深的话,就无力负载大船。在厅堂的坑洼之处倒一杯水,那么小草可以当船;放一个杯子进去就会胶着不动,只因水浅而船大啊。风所积聚的力量不够,它托负大鸟翅膀的力量就不够。所以鹏鸟能飞九万里是因为有狂风在下,使它能乘风而行,在蓝天中自由翱翔而没有能够阻遏它的东西,然后才能按照计划向南飞行。寒蝉和小灰雀讥笑它说:“我们迅速飞起,突过榆树和檀树,有时还飞不到而掉到地上呢,哪里可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再向南飞?”到郊野去的人,准备三餐就行,返回时肚子还饱着呢;到一百里远的地方去的人,出发前要用一宿来捣米,准备好粮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去的人,三个月前就得准备粮食了。这两只小虫哪里能明白呢?小智慧不如大智慧,寿命短的不如寿命长的。怎么能知道是这个道理呢?朝生暮死的野菌没法活着经过两天,夏生秋死的寒蝉不懂得世上有春季和秋季:这都是因为寿命太短了。楚国的南边有叫冥灵的树,把五百岁当作春,五百岁当作秋;上古的时候有叫大椿的树,把八千岁当做春,八千岁当作秋。还有彭祖以极其长寿而闻名于世,普罗众生和他相比,不就太可悲了吗?
商汤是这样询问大夫棘的:“北方不毛之地,有一个很深的大海叫做天池。里面有一种鱼,体积之宽有数千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这种鱼叫做鲲。有一种鸟叫做鹏,后背像座大山,双翅如同天边的云彩,振翅拍击着旋风飞到九万里的高空,穿过云层,背负青天,然后计划着往南飞,将要飞往南方的深海。小雀讥笑它说:‘他要飞到何处去?我腾跃着飞上去,不过几丈高就得落下来,在蓬蒿之间翱翔,也算是飞到极至了,他要飞到哪里去?’”——这便是小与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知道,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之职的、品行能合乎一乡人的心愿的、道德能符合一君之心的、能力能取信于一国之人的,他们看待自己也像小雀呢。而宋荣子却笑他们。世人全夸赞宋荣子,他不会更加努力;世人全责难他,他不会更加沮丧。他能确定自我与物外的分别,分辨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也就如此罢了。宋荣子对于人世中的追求,并不急急忙忙,虽然如此,他还有未曾树立的消遥之德。郑人列子驾着风行走,多么轻妙美好啊,十五天后方才返回。列子对于幸福的追求,并不急急忙忙,但这样虽能免于行走,可还是有所依凭(指风)。至于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把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疆界的人,他还需要依靠什么啊?所以说:道德高尚,顺应自然而长寿的至人是忘我的,超脱于物我之外的神人是不立功的,道德境界臻于完美的圣人是不求名的。
我思:
我们习惯于说“老庄老庄”,有的人便把老子和庄子混为一谈了。事实上,老子与庄子的区别很大。老子的学说可治国,庄子的学说只可修身。因此,庄子的学说从未为政治服务过。这种学说有局限性,却也有无比曼妙、无法逾越的精神高度,也因此,成为了历代失意或不失意的文人的精神栖息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