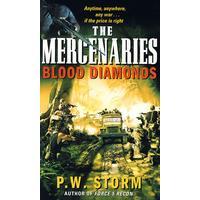路内、阿乙、阿丁、曹寇、瓦当……他们将改变一个时代的文学形态。游走在主流之外的“中间代”,会逐渐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这是必然的。一篇小文,见《百家评论》2013年第6期,写阿丁。我不是评论家,以新闻人的笔法写文学评论,让方家见笑了。
人性黑洞的自我救赎
——阿丁及其小说

老四
1
写此文之前,我读了加缪的《局外人》。这是一部存在主义的经典之作,其开篇“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被无数人膜拜,和《百年孤独》的开头同属伟大行列。加缪诠释了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人民公敌”的:一次过失杀人,被冠之以“丧失了全部人性”的罪名处死。我突然想起阿丁来。
阿丁目前最看重的一部小说《无尾狗》,按照他的逻辑,所要阐述的是:“当一条街被所有砍掉了尾巴的狗占有,偶然有一条长尾巴的狗闯入它们的街区时,它们就会扑上去,把后者的尾巴咬下来。于是,新的无尾狗也成了它们中的一员,一起奔跑、吠叫、嬉戏,狗的世界就此和谐,再无纷争。”这显然和加缪有着相通之处,当一个人成为和大多数对立的异类,他应有的结局无非两个,一个是毁灭,一个是趋同。加缪选择了毁灭,阿丁选择了趋同;毁灭是麻木的终极目标,而趋同则意味着长久的麻木和痛楚。趋同其实是更加残忍的毁灭,阿丁沿着加缪的道路,继续向前探索。
这似乎也是阿丁作为一名作家的意义所在,他试图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写出不一样的小说,将当年余华们未竟的先锋“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到,阿丁丰富的履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阿丁原名王谨,上世纪70年代出生,河北保定人,十六七岁便参加工作,做了将近十年的麻醉师,后来辞职和父亲一起开诊所。小说《无尾狗》中,主人公丁冬辞职用一个处方写的辞职报告,这个情节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我的辞职就是用处方写了一个辞职报告给院长,然后就走了。当时是很震撼的,我们属于国家干部,都包分配的,辞职意味着丢掉一切。”
开了两年诊所,像一个老中医一样坐在那儿消耗青春,他感到自己“被那些病菌、病毒在吞噬,吞噬我的青春”,后来他又去做生意,创办“阿拉丁工作室”,最终不了了之。困顿之时,他到网吧写文章,偶然的机会,进入媒体工作,先是在重庆,后来辗转跳槽到天津的《每日新报》,《新京报》创刊又跳槽到《新京报》。
“真真正正开始写作,是进了媒体。当时我跟阿乙,有事没事电话聊天,聊文学,几乎不约而同地就开始尝试写小说了。”那一年,阿丁33岁。阿丁和阿乙,两个“大器晚成”的70后“盲流”,成为后来小说界的传奇。
早年的经历成就并丰富了他的写作,阿乙也是如此。一个是前医生、麻醉师,一个是前警察,两人还有一段共同的媒体从业经历,后来又担任了不同文学杂志的主编,继而进入出版行业。他们的小说也有着诸多共性,尤其对死亡、暴力的高歌,有人甚至会将他们的小说弄混。都带有强烈的小镇意识,都有着对死亡和沉默的天然嗅觉,无怪乎一个阿丁,一个阿乙,中间独独空了一个阿丙。
说句题外话,研究中国70后小说的人,完全可以把阿丁和阿乙放到一起,作为对以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一种致敬,他们有着独特的话语权。
相对于60后的沉稳早熟(余华、格非等),以及商业化大潮下80后的风起云涌,夹缝中生存的70后作家,似乎长期找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诗评家霍俊明在论述70后诗人的境遇时说他们是“尴尬的一代”——这似乎是70后一代作家普遍的无奈与彷徨。“他们活在60后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80后的市场影响力。他们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沉寂的一代、夹缝中的一代,他们也确实沉寂了多年。但在这一群体普遍过了30岁以后,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班嘉旭《文坛“中间代”与铁葫芦》)
当很多50后作家在他们这个年龄便完成最重要的作品(贾平凹的《浮躁》、《废都》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酒国》等,张炜的《古船》),60后作家更以天才的笔触,完成经典之作(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苏童的枫杨树系列),作为70后代表作家的阿丁、阿乙等人,很难说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已经进入小说家创作黄金年龄的后期(我们总是被“70后”这个标签蒙蔽,实际他们已不年轻,阿丁42岁,阿乙也已38岁),他们才刚刚开始,因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文本呈现,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文学责任。
以阿乙、阿丁、曹寇、路内等为代表的70后作家,提出“中间代”这一概念。按同属“中间代”作家阵营的慕容雪村的戏语,年代的基本划界从1968年到1978年。这是一批以70后作家为主,夹杂些许60后、80后作家的创作群体。相对于较早成名的一批70后作家,他们大都长期从事与文学无关的职业,在人生的“后青春”时期才开始涉足写作,凭借丰富的阅历,写做出与所谓学院派完全不同的作品。
由于出道较晚,他们似乎都有一个或几个提携者,北岛之于阿乙,韩东之于曹寇,马原、野夫之于阿丁,前者广阔的文学影响力,尤其是在文艺青年中的号召力,为他们已有的人气增添了不少光辉。
出道晚并不意味着没有后发优势,恰恰相反,30多岁才爆发出文学潜能的阿丁,很享受“中间代”这一标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我坚信,如果70后作家不出好东西,是不可能的。”与50后、60后作家相比,他毫不讳言,称“其实苏童这些人在文学领域是集体退步,越写越差”。
不过应该看到,中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还停留在经验写作阶段,由于履历丰富,逝去的那些时光总是在冲击他们的文字。路内至今大部分作品指向“戴城”,那是他的故乡的代称;作为现实存在的艾国柱的警察经历,丰富并成就了作为作家的阿乙。至于阿丁,无论是《寻欢者不知所终》中的某些篇章,还是《无尾狗》的故事框架,生活经验注定了他的小说走向,冀中平原上的那个小城,成为他最终写作的母体。
2
阿丁的作品数量并不大,至今为止,他仅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历史随笔集,并主编一本文学杂志《坚果》。
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是阿丁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与很多作家的小说先发表再出版不同,这些作品先是在豆瓣、天涯等网站流传,然后才结集出版。这十四个短篇小说,分为三辑:有关记忆;有关逃离;有关存在。
这十四个短篇小说,无疑是阿丁文学理念的一个大杂烩。书的封面上写道:“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无力逃离,不得不时常背叛内心,终生扮演着自己不想做的那个人,于是才有了嫉妒和仇杀。”阿丁用一本小说,向自己的前半生致敬。
记忆—逃离—存在,预示了人生的三个历程:过去、现在、未来,从经验写作开始,走向人生的哲学存在。
我第一次接触阿丁,便是他的短篇小说《成人礼》,后来被收入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被归入“有关记忆”。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成人礼,属于对逝去青春的总结和成长,看似没有新意的题材,阿丁写得温情脉脉,却又寒意逼人。乔凤鸣对老乡杨小通的关心和爱护,并最终赠送给他一次成人礼——和自己的女友做爱,故事表面背后的施虐和受虐,呈现出了人性的多层寓意,也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读完这篇小说,我立即想到了余华的《我胆小如鼠》,同样是一个懦弱的男人的故事,两篇小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可以放在一起,用以查看国人的人性黑洞。
本辑中的其他几篇,想喝人奶而导致失明、瘸腿的悲惨兄弟,看黄色碟片被告发从而逃跑的父亲,少年被设计的出门远行。阿丁说:“欺骗和背叛也许是你在成人礼时最大的收获,很多时候你自己就是祭品本身。”阿丁以精准的构思,完成了对青春的祭奠,就这一点而言,他埋葬青春的文字便超越了大多数所谓的青春写作,具有了悲壮的思想价值。
小说集的名字来源于“有关逃离”里的第一篇同名小说,一个妓女去公安局报案,她的一个嫖客失踪了,作为记者的“我”连夜前去采访,妓女开始向我讲述她与嫖客的关系。嫖客雇用他,充当自己的小三,目的是让妻子和自己离婚,而他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他离婚,仅仅只是想离婚而已。为了编造一个世俗的理由,他需要一个妓女作为演员。小说最后,“我”在警察朋友肩上推了一把:“你他妈干吗拷上她,那是个疯子,一个会编故事的疯子。”这句话,何尝不是阿丁本人的自讽?回过头去,再把故事梳理一遍,我们会问,到底谁是逃离者?是那个叫冰的男人?显然他是,还有呢?妓女?她在逃离什么?编造这样一个故事,是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或许,没有任何道理才是这个小说最终的道理。
至于“有关存在”里的几个短篇小说,则是现实的阿丁向精神的阿丁转移,《W与M》是精神病人的喃喃自语,《晚安,秦舞阳》以魔幻主义解构历史,《查无此人》通过科幻故事诠释理想主义者的幻灭。
阿丁试图变换不同的角度,十四个短篇,便是十四种方式,直叙、倒叙、插叙,第三者的在场,时空的流转,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传奇。
从阿丁身上,我看到了加缪的影子,也看到了布考斯基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说一句题外话,在性格上,阿丁和布考斯基有着些许相近之处,他对布考斯基的评价颇为精准:“布考斯基被称为底层的桂冠诗人是有道理的。但要是称他为大师,就可笑了。我想以他的个性,会从墓地里爬出来笑嘻嘻大骂的。布考斯基的文字是独特、不可复制的,他用自己的真实生活和话语方式趋近了文学。”或许,用这句话来描述一个侧面的阿丁也是完全可以的。以戏谑面对文字,文字却还之以压抑的情感、撕裂之后的阵痛。
3
阿丁的首部长篇小说《无尾狗》,以纯粹文学的眼光来看,还存在一些漏洞,技巧的缺乏使他很难像一些成熟作家一样对长篇巨制驾轻就熟。但说来奇怪,正得益于他的“拙”,才成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无尾狗》的出版在《寻欢者不知所终》之前,初稿更是在2007年便已完成。这部奠定阿丁文学地位的长篇小说,无疑更有杀伤力,并成为2012年长篇小说领域的一个话题。
小说创作起源于苏联作家巴别尔在某次苏联作协会议上说的一句话:“顺从得令人发指。”读到这句话,阿丁好像挨了一拳,突然意识到周边的人,包括亲朋好友以及自己,都是一群“顺从得令人发指”的人,“顺从似乎已经成了流淌在人们血液中的哲学”。于是,他把这句话当做了自己的QQ签名,同时,这句话调动起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一下子挖掘出纠缠他很久的一些素材,长篇小说《无尾狗》应运而生。
诗人野夫评价《无尾狗》:“本书是对吾族阴暗历史和心性的一个诅咒。”每个人都是肮脏的,我们活到现在,每个人以及他的祖上,都充满了原罪。想想看,能保证几千年绵延不绝,一次次精子与卵子结合,才有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祖先,他们的阴暗史罄竹难书。
小说开头,阿丁让主人公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样,失去了人形,但他没有让这个叫丁东的人变成甲虫,而是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体内的败絮,那是动物尸体腐败进程中发出的恶臭和植物腐殖质的芳香的交织。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经典诗作《腐尸》,那具“充满恶臭的肚皮”,在太阳的照射下,“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养分,百倍归还伟大的自然”。
这是一部叙事独特的小说,时空的错乱,人物的前后夹击,使故事显得散乱,看似没有头绪,却又有一个内在的线索把整个故事串连起来。
在这个错乱的故事里,每个人似乎都在经历着从有尾到无尾的过程,有的人热烈拥抱这个过程,有的人在褪变的道路上半推半就,有的人被迫把自己的尾巴割掉,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尾狗。比如医院里那些医生,红包的多少成为他们证明自己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还把这个行为当做资本炫耀给后来者,苏卫东的结局无疑会是这种人,当他终于发现了丁东的弱点——前女友是院长的女儿,便毫不犹豫地铲除了这个影响自己仕途的师弟。而舅舅则显得复杂一些,为了爱情,他义无反顾地娶地主的女儿为妻,后来被批斗,最终自己把尾巴割掉,扛着沐浴更衣后的妻子,把她献给了自己的仕途。
丁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这个赋予了作者极大情感的人物,一次次挣扎在无尾和有尾之间,每每把自己装点成罪恶的化身。某天夜晚,酒鬼丁东面对浩瀚的天空,发出了一声长嚎:“晚安,这个城市中所有的于连、所有的拉斯蒂涅、所有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于是,我们把他定性为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混合体。为了前程,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前女友,同样为了前程,他大胆追求胖姑娘刘满月,“将蹬着这个肥硕稳健的肉梯尽可能地向高处攀爬”。在出卖灵魂的道路上,丁东接受了自己的“敌人”舅舅的告诫:“当爷们的,裤裆里的鸡巴也是吃饭的家伙,可不光是脖子上的脑袋。”于是,他用身体勾引刘满月,并用身体充当雷春晓的男宠,每次做爱换取200元钱。这个一心想往高出攀爬的“凤凰男”,最终摔回了原点。
阿丁善于揭开人性中的丑陋,并将这个丑陋撕碎了呈现在你面前,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在耸人听闻。比如乱伦、性幻想,灵魂深处最恶毒的变态想法,阿丁毫不保留甚至添油加醋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显示出了与现实决绝的勇气。
“割自己,让别人疼。”这是几年来我给自己的写作的一个定位,我还没有做到,阿丁却早已将其发挥得游刃有余。阿丁把自己的尾巴割掉,却是割开了无数人断尾处的伤疤,伤疤在流血,恰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一声声忏悔。
阿丁对“无尾狗”的哲学定义还在继续。2014年3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这部小说走到了《无尾狗》的另一面。书的宣传语中说:“假如你读过《无尾狗》,这部小说极有可能会让你产生疑问:这是阿丁写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花心”的小说写作者,你永远也猜不到他的下一个‘兴奋点’是什么、在哪里。”
如果说《无尾狗》是对人性黑洞的简单呈现,那么《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则是更进一步的实际行动。这部小说让人想起了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的《我要在你坟前吐唾沫》,小说中,混血黑人安德森,由于弟弟被白人烧死,他开始了疯狂报复,以强奸、虐待、残害白人女孩来实现目的。书中充满了触目惊心、情色暴力的场景。阿丁再次用一种暴力,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鞭挞。
谈到《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阿丁说:“三个中篇三个短篇连缀在一起,自己也说不清该叫她长篇还是什么。”本书以树为喻,引出小人物的一段家族命运。在阿丁看来,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穴居生物,终其一生都活在有形或无形、宽敞或逼仄的洞里。而“洞穴”的内径是随人类的欲望生长的,因此没有谁能破洞而出。
很早之前,阿丁就有着一种奇怪的植物崇拜。在《无尾狗》后记里,他便写道:“我对自己作为动物的肉身存在无计可施,因此希望自己拥有植物的思维。”阿丁以植物的瞳孔观察人类,在他眼中,人类就变成了秃鹫、鬣狗和大肠杆菌的形状,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言说功能。
《无尾狗》是阿丁30岁阅世之后对自己的交代,《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则是40岁之后,不惑之年的阿丁,向生命发出的叩问。他把动物的肉身毁掉,成为再也不会伤害别人的植物。
4
阿丁曾写作大量专栏,以“软体动物”为名,在《南方都市报》刊载,后结集出版。他品评历史人物,挖掘古代文人的B面,试图将他们最丑陋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看来,阿丁在小说中的一些尝试,也被他运用到随笔中来。可是后来,他放弃了专栏写作,专心写小说,摆脱功利心。
他把姿态放得很低:“我觉得写小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工作不能贯穿一生。我和主流作家圈子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获得过文学奖项,写小说是兴趣和爱好所致,也不想出什么名,我把微博的V都去掉了。不管外界怎么定位,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他还做过一本文学刊物《坚果》,他提倡小说要有坚果味儿,剥起来费劲,但味道和营养不错。一个好故事应该像坚果一样,需要耗费脑力,品出上佳的味道。但这个杂志只出了一期,便夭折。
后来,当阿乙曾担任执行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宣告停刊时,他不无哀伤地说:“《天南》‘西去’。有人说这年头做文学必死。想了一整天也没想出来一件做了可以必不死的事,那么,继续。”
他依然在写作之外追求一种文学的理想状态,于是,在《坚果》“死掉”之后,创办中国第一个专做短篇的APP——《果仁》。阿丁要拓展自己的领域:“我现在要做的事之一,就是想挖掘一批完全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让有才华的人见天日就更理想了。”
在阿丁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体制外小说家的理想状态,追求灵魂的自由,对罪恶的鞭挞和嘲讽充满智慧。他追求小众化,“爱谁谁”不仅是他的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他的读者定位,说到底,他只是为自己写作,别的事,爱谁谁。但我想,只有真正做到为自己写作,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之于当下的小说江湖,阿丁的写作,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命题。
(作者简介:老四,青年作家,《齐鲁周刊》首席编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