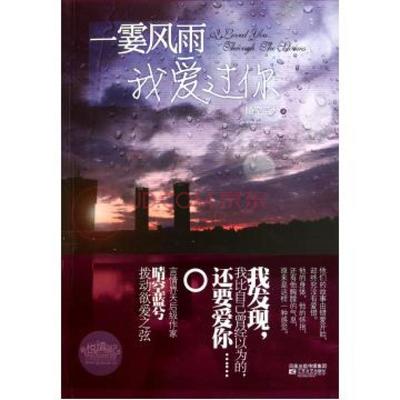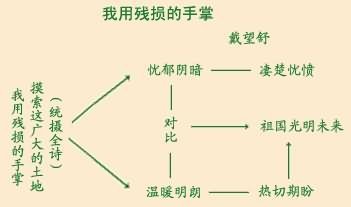我们促膝相坐在夏日尽头,
那个女人,你的密友,她美丽温柔,
还有你我,在一起谈论诗歌。
我说:“一行诗也许要我们几个钟头,
若它读来不似瞬间的感发,
我们斟字酌句也只是白搭。
还不如将你的那对膝盖下跪,
去洗刷厨房地板,或像老朽的穷鬼
顶风冒雨做着各种零活苦工。
要想把声音组织得甜美成诵,
就得比这一切更加劳苦,不消说
银行家、校长和牧师之流的数落,
他们喋喋不休,视我们为闲人,
而烈士声称他们才是世界。”
然后,那个女人
以她温柔而年轻的嗓音喃喃低语,
多少人因听到这声音而内心痛楚
它是那么年轻、温软而低柔。
“有一件事我们女人都应看透,
虽然我们在学校从未听到——
要想漂亮我们就必须操劳。”
我说:“自从亚当堕落以来,肯定
不再有毋需操劳的优美事情。
曾经有些恋人,认为爱情应该
由许多高调的殷勤儒雅组成
于是他们会扮出饱学的神情唉声叹气,
从精美的古书中援引先例;
如今看来真是件无聊的行当。”
我们因提到爱情而默然相向,
坐看白昼燃尽最后一抹晚霞,
飘曳着蓝绿色暮霭的苍穹下
一轮月亮,仿佛一枚贝壳,
因时间之潮的冲洗而疲乏失色,
那潮水随星星涨落化着岁月时辰。
我有一种感想只愿你能耳闻:
你曾有娇颜艳容,我也曾尽力
用古老的方式爱过你
一切都曾那么幸福,而我们终究
倦怠疲惫犹如那轮空洞的月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