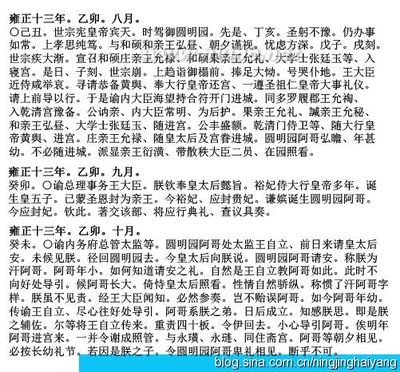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它给不少人(包括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人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人”二字,或曰礼教“吃人”,或曰仁义道德“吃人”。其实,《狂人日记》中“吃人”二字,其内涵要比上述印象以及建筑在这种印象基础上的理解丰富得多,也要复杂得多。
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人留下的“礼教吃人”的印象被放大,与吴虞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就叫〈吃人与礼教〉,是读了〈狂人日记〉之后写的。吴虞在这篇文章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在文章结尾时又说: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的这篇文章,是由鲁迅的〈狂人日记〉引发的,吴虞对于礼教的这种认识,却并不源于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在1915年7月,他就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着重对礼教中的“忠孝”二字予以猛烈的抨击,在当时也可谓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吴虞将“吃人”与“礼教”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与鲁迅〈狂人日记〉之原意并不完全一致,有过于极端之嫌,却也有闪光的真理。如今,有人为鲁迅开脱,说提出“礼教吃人”的不是鲁迅,而是吴虞,这话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以此为鲁迅“开脱”,却是没有必要,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表达的意思,即使现在看去,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有关“吃人”的那段话,应当有这样三个层次。
其一,中国“古来时常吃人”而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这并非就是礼教“吃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其“日记”中,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吃人”的例子,一是《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的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易子而食”;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说的“食肉寝皮”(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以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等杂文中都曾说到“食肉寝皮”,可见印象之深);三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四是“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五是徐锡林(麟)的被吃;六是“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所有这些“吃人”的实例,大概都是从每页都写“仁义道德”的字逢里看出来的。只是“狂人忆中有误”,才将易牙“蒸其首子(应为子首)而献之(齐桓)公”说成了“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又将唐代《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误为明代《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这些因为出于小说人物之口而有些“变形”的史实,未必都与“礼教”有关,例如易牙将自己的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未必就符合孔子或儒家的主张。但《论语》没有提到此人此事,《孟子》虽然说到此人,说的却是他的烹调,至于他的那件灭绝人性之事,连提都没有提及。这可以说是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吃人”。

其二,是那些“吃教”的人,借礼教之名“吃人”,这也不是礼教“吃人”。
这样的人,也就是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说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人,他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被孔子称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齐桓公,周襄王拿祭肉给他,说他年纪大了,不必下拜尽君臣礼节。他与管仲商量后,还是下拜尽了君臣礼节,从这一点看,此公似乎也讲“礼教”,然而,易牙的儿子却是给他吃了的。一个是“以太牢祀孔子”的汉高祖,吴虞称他为“崇儒尊孔的发起人”,然而,正是这个汉高祖,“诛粱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醢”是古代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这位“崇儒尊孔的发起人”对彭越用了这样一种酷刑之后,,不但自己吃用人肉剁成的肉酱,还要让他的诸侯们都尝尝这种肉酱的滋味,大概也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然,这都是“礼教”的旗号正式打出来之前的事,虽然也都与“礼”有关。“礼教”的旗号打出来之后,这样的事只会有增无减。鲁迅很熟悉的魏晋名士嵇康,就是因为钟会打了小报告而被害死的,这小报告中有一条罪名,就叫“害时乱教”,此“教”不正是“礼教”吗?然而,被嵇康目为“礼法之士”的钟会,又哪里就真的信奉“礼教”?倘若钟会真的严守纲常名教,日后会落到那个下场?当然,钟会还只是“吃教”者中的想当权势者的人,至于“吃教”者中处于权力顶层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权势者们之“吃人”,更是怵目惊心。那个采用董仲舒之“八字方针”的汉武帝“吃”了多少人谁能说得清楚,不是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太子呢——都被他“吃”了吗?那个“效周公辅成王”的朱棣,即日后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亲自为之制序的永乐大帝又“吃”了多少人,那些个真正信奉礼教或纲常名教的,不是都被他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吃”了吗——有的如练子宁被割了舌头,有的如铁玄被投入沸腾的油锅之中,那个“读书种子”方孝孺,还被灭了十族。
其三,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确实也有“礼教”本身吃人的一层意思。这样的实例,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此说其实也是于史有据的,就是出于宋代的“割股疗亲”——“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出于《二十四孝》的,则是“郭臣埋儿”。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的“表彰节烈”,即表彰那些为丈夫或未婚夫活着守寡或死去尽忠的女子。如此鼓吹孝道,表彰节烈,颇似衍太太之所为,明知小孩子在寒冬季节吃冰会肚子疼,却鼓励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明知小孩子打旋子旋得多会跌倒。却鼓劲说:“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让子女为“孝”女子为“贞”而走上一条死亡之路。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中所举礼教“吃人”的臧洪与张巡两例,则是为“忠”的了。臧洪是汉末之人,在袁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之时,他居然“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后汉书·臧洪传〉)张巡是唐代睢阳守将,在“城中粮尽,易子而食”之时,“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以此为榜样,“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样血淋淋的“吃人”事迹,明明白白是在“礼教”的旗帜下出现的,还写入了《唐书·忠义传》。“礼教吃人”,当然也是通过具体的人去“吃”的,这是被“礼教”控制了的人,他们既“吃人”也被人“吃”,而这“吃”与“被吃”,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狂人日记》中的“我”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了……/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我想,《狂人日记》中说的“吃人”二字,应当从上述三个层面去理解,才是完整的,符合鲁迅的本意,而且无可挑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