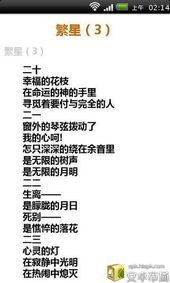要是你问作为一位女读者,和哪一位作家打交道最能感到骄傲,我当然会说是伟大的博尔赫斯。他曾说,只要盯着一个女人五分钟就不是一个男人。他想表达的是拉丁美洲的大男子主义,男人是不应该老是为着女人转的,却恰好表明女人在他眼中是诗意和浪漫的。在他失明后,也时常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女读者,他总是会把她们想象的比看上去要美。
博尔赫斯构造的小说世界和他看女性一样,是不触击现实的,现实只不过他驰骋幻想的一个载体。不过在他早期的《恶棍列传》短篇小说集里,博尔赫斯还只是像传统作家一样,替一些街头流氓和强盗们列传而已。他真正开始尝试虚构小说是从《南方》开始的,在那篇小说里他一次讲了三个故事。1976年3月在印第安纳大学演讲中,博尔赫斯谈到了他创作《南方》的构思,他说是受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影响,使他想在《南方》里一次炮制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其实也是一个故事,只不过有三种不同的结局而已,三种不同的结局反过来又使原故事变成了三个不同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胡安·达尔曼一天在上楼时,暗地里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额头出了血,第二天发了高烧,在床上躺了八天,后来被送进疗养院。病好后他乘上火车,想回到他渴念已久的南方,结果火车没停在惯常的车站,他在稍前一站下了车。他走到一家杂货铺子寻找马车,等车时,他在铺子里吃了晚饭。旁边一个喝醉了酒的小流氓向他挑衅,激将他去搏斗,这对于刚走出医院又不善于玩刀子的达尔曼来说,刚好给人杀死他的理由。达尔曼明白他不免一死,不过这种死法刚好复合他作为一个南方人的意愿,在“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于是“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这是一种现实的读法,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现实故事,这个故事里叙述的是一个不愿意死在手术刀下的南方人的野性回归,终于如愿以偿,在南方的旷野上死在小流氓械斗的刀子下。
第二种读法里它是一个寓言故事,比第一个故事感觉要有趣得多:达尔曼躺在医院里时开始渴念起南方,于是在病好后他乘上火车想回到南方,结果火车没有在惯常的车站停,他在稍前一站下了车。他走到一家杂货铺子,在那里吃晚饭、等车,旁边一个喝醉了酒的小流氓激将他去搏斗。达尔曼渴念南方,结果回到南方时,南方却杀害了他。一个人死于他所热爱的事物,这正好是王尔德所说的“每个人都戕害了他所热爱的事物”的颠倒。
在第三个故事里,达尔曼也许从未回到南方,他被刮伤之后,第二天发起了高烧。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八天,在他死于医院手术刀下之前,他做了个梦。在那场梦里,达尔曼并没有窝窝囊囊地死于医院的手术刀下,他病好了,乘火车回到了他渴念已久的南方。在那儿的旷野上他持刀拼杀,幸福地死于械斗中的刀锋下。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达尔曼幻想着一场南方人英雄式的壮烈死亡。
博尔赫斯最喜欢的是我们用第三种梦的方式去解读他的《南方》,他认为这种读法最好,把它当作一个梦,小说写的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死亡,而是临死前梦见的死亡。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对死亡美学的探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世界里,生老病死的的正常死亡是不值得提及到小说里来的,在他那儿,死亡必须具有一种美学价值。在《马可福音》里,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在洪水围着的乡村庄园里,他把一群乡村野蛮人变成了上帝虔诚的信徒,这群信徒却按照《圣经》里的方式,把他当作救世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一个人不甘心现实中窝窝囊囊地死去,在梦想中轰轰烈烈地死了,这类故事博尔赫斯也不止在《南方》里讲过,他在《另一次死亡》里也探讨了同样的主题。一个庄园雇工参加一次战役表现懦怯,被子弹吓破了胆,他活了下来,却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后半辈子决心洗清。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战役再一次在他的梦中出现,他英勇牺牲在战场上。这个庄园雇工的幸福死亡也是通过临死前从一场关于战争的梦里获得的。
我们把《南方》看作博尔赫斯小说的转折点,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生活里的确发生过。1938年圣诞前夕,博尔赫斯在快步上楼时,撞上了一扇窗,他觉得头上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流了血,伤口感染,他发高烧住进了医院。这一幕被写进了《南方》之后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达尔曼,小说里达尔曼先生的遭遇大致和这差不多。他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后来康复了,现实中的博尔赫斯没有像达尔曼一样死去,而是继续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冒险虚构。这个经历与小说《南方》的第一种读法一样,基本平常得很。事件之所以被看作重大,是它给博尔赫斯带来的后果,他在疗养期间,对自己的精神是否健全产生了怀疑。他母亲给他念克·斯·刘易斯的神学幻想小说《走出寂静的星球》时,他听着听着哭了起来,他说他明白了。他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作为作家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此虚构小说艺术的一场世纪中期的革命即将开始(詹姆斯·伍德尔给博尔赫斯写的传记《书镜中的人》有资料记载) 。
博尔赫斯后来很多小说都是故事中套故事,一个故事综合了几个故事的讲法,我们必须如读《南方》一样用几种读法才能把小说里的几个故事读出来。这种写法博尔赫斯说是模仿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这说明一个故事中套几个故事的写法,他不是第一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人。
《南方》作为博尔赫斯小说革命性的创作转折点,并不是他在一个故事中讲了几个故事,而是他抹去了现实和虚构的界线,他一笔勾消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虽然这种一笔勾消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界线是博尔赫斯在《南方》之后,成了他习惯的创作方式。我不认为他是唯一的先驱者,在卡夫卡在《变形记》、卡尔维诺在《不存在的骑士》等小说里,我也同样读到这种不动声色的抹去现实和非现实的创作方式。
这位伟大的阿根廷小说家,189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的创作灵感多半来自他博览的群书,而不是生活。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博尔赫斯最初和主要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室,人们想象中那个在宁静幽暗、满是灰尘的图书馆里坐拥书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的形象,可能是个误解。至少在他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歌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他被公认为上个世纪中期颠覆了小说世界,或者如他可能说的那样,颠覆了世界上的小说。但我认为他讲故事的方式其实古已有之,在他之前,那些能从古代传流至今的民间故事都有这样语言简洁、过目难忘的特色。博尔赫斯自称是《一千零一夜》和《圣经》哺乳大的,晚年时他不算谦虚地表明,希望他的名字会被人遗忘,他的故事不是通过书本,而是能像《一千零一夜》一样,口头流传下去,那才是讲故事的最高典范。
大凡能经过上千年流传的故事,经过千千万万人讲过的故事,也许后来人讲的和第一个人讲的有很大区别,甚至走了样,完全变了形。但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流传,故事总是不断撰改,每个人可能都会对它添油加醋。他主观地认为添加的内容是最接近完美的,令听者感到满意的。但是到了另一个人的口中,或是经过了几代人流传的时候,别人也在添加,讲故事的人会有意添加自己幻想出来的情节,但是他不会刻意放过一些精彩的内容不讲。一些内容在流传中流失了,绝对是那情节不够精彩,不值得记住,或者老是让人想不起来讲,所以就失传了。因此能一直流传来的故事情节绝对是经典的,是能突出故事特征的情节。所以也根本不怕那故事在流传中走样,既便走样,也只会越来越经典,直到某人突然有一天把故事给记录下来了,这故事走形就比较缓慢了,这就成了文学。
在博尔赫斯看来,能像《一千零一夜》那样讲故事一定是经典。因为那是最古老的一种讲故事方式,却也是最卓有成效的。但是越是最简单的方式,越不好把握,博尔赫斯却轻而易举地就掌握了这种讲故事的特征。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世界注重的是故事,事实上当你想起博尔赫斯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传奇故事(就如同你想起莎士比亚,你首先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哈姆雷特、罗蜜欧等)。他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了一个洗尽铅华的文学语言的愿望,他的魔力就在于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并把这种方式提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本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说,不注重小说技巧就是不注重艺术创造。博尔赫斯颠覆小说世界就是从《南方》开始,展现了他高超的讲故事技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