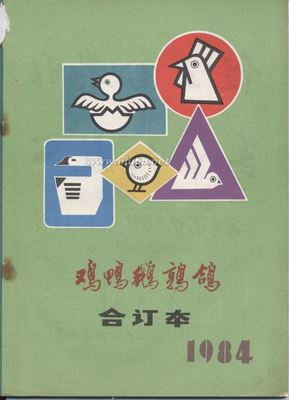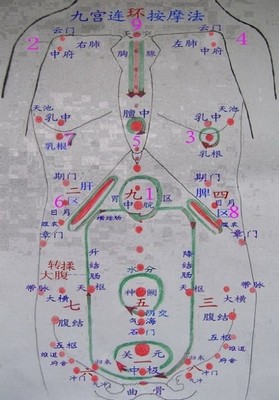大约在一个多月前,有朋友不断问我:“你给春晚写小品啦?”我以“怎么可能”作答;后过了些日子,一家报纸上载文说春晚语言组用我的一篇小文改成小品,效果颇好,我虽奇怪怎么春晚无人与我联系,但亦一笑了之;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再也笑不起来。
在消息见报之后,先是有人自报家门(春晚剧组)不报姓名地问我,是不是写了如此一篇文章,然后又传来一份资料让我看看是不是一样。这是刊载在2009年11月下半月刊的上海《故事会》,署名“陈志宏”的一篇抄袭之作,我想两文读后结论自有。我的小文首发于2008年8月14日的新浪博客,200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马未都说·车上篇》第36页,名为《量力而行》。其后经过三番五次的电话盘问,我都如实禀报,电话另一头剧组小姐总是将信将疑地说出不算悦耳的话。我年长,她年幼,我不和她计较。可她后来的话比较刺人,她告诉我说:“我们(春晚语言组)本来是根据陈志宏在《故事会》的文章改编的,可没想到您也写了一篇。”我听这话确实也糊涂了,我怎么早在他之前“也写了一篇”?好像有点儿不该的意思。
后来,剧组小姐又打电话告之:“陈先生愿意与你共同署名。”我只好告诉她,我不认识这个陈先生,我不追究他抄袭是我大度,但我不可能“共同署名”。我当时还退了一步,我说“让他在改编里署名吧,我也不计较了。”谁知剧组小姐郑重告诉我说:“你理解错了,我们改编另有别人。”
后来,剧组小姐电话通知我,并发一邮件《确认书》让我确认同意改编,然后用快递给春晚剧组寄回。我在我的权利未弄得十分清楚的前提下,主要是怕被蒙着“共同署名”,没有及时寄出;剧组小姐就电话急催,毫不知道什么叫客气,从这事发生我接了她几十通电话,有时甚至在半夜,但我总是耐着性子听她那番道理。我告诉她,《确认书》是个单方面的凭证,签字后如寄出,我手头就没有任何凭证,此事应该签合约,双方各执一份。她先告诉我春晚几百份都是这样签的,没有其他法律文本。我说那我不签,她这时只好说去问问再告诉我。
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可以签合约,不签《确认书》了,马上发合约范本给我。我收到合约后把空格的地方一一问了她,她告诉我说空格不要填,只签名寄出就可以了。这事很奇怪,天下的合约都没这么签的,要命的地方都空着,让乙方(即我方)签字,那这合约有什么意义呢?!我问她一个文人难以启齿的问题,空格内的“作品许可使用费”金额是多少呢?她告诉我1000到2000元,每个人都一样,节目播出后就给。
接下来的事有点儿匪夷所思。我告诉她这样的合约我不太想签,主要是……,剧组小姐有点儿着急上火,口气不太友好:“我告诉您吧,这节目上不上还不一定呢,签不签随便。”说完把电话挂了。我愣了半天神才省悟过来,估计所有作者都特想为春晚增光,为自己积累,上不了春晚等于白瞎,所有作者都有求于人,剧组的工作人员盛气凌人也是有原因的。可这招对我不管用,这个节目上不上春晚,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后来,我的电话就没断过说客,连我都记不起的发小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当我如实招供后,他们也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又让剧组小姐找我赔礼道歉。按说我再次接她的电话就是原谅了她不恰当的做法。她和我约了时间,到观复博物馆找我,她在路上电话指示我,让我自己先打印合约5份,她亲自来取。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不用自己花快递费了,她迟到了,我心里依然以路不好走为她解释。
当我们终于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剧组小姐向我致歉,她说:“我不知道您的身份,我要早知道就不会这样。”我告诉她: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尊重每一位作者,不管他是谁。我后来出出进进打印文件,她跷着二郎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我心里依然用她可能上学时缺乏社交礼仪教育为她解释。可当我跟她说,合约某些条款我不同意,如她不能做主,让她回去商量时,她突然不悦,告诉我这样她的饭碗就会丢了;这让我内疚,进退维谷。我只好告诉她合约是一个双方自愿签署的法律文本,一旦生效,不可反悔,所以要慎重云云……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十分难堪,她开始哭闹,我在她哭闹的间隙跟她说:任何合约都不会因哭闹而签。她不听,仍我行我素。后面的细节及言语限于篇幅,对她也不好,我就不想说了,反正我没签合约。
这些天,春晚剧组的人我认识的不认识的,直接的间接的拐弯抹角的都给我打电话,说事关重大,时间紧迫,还是签了吧,否则大家麻烦一团……春晚总导演金越也来电话向我道歉,只是电话里我没法说清至今未签的原因。
我想,此时我更应该主张权利,让尊重作者权利不再是一句空话;让本次事件作为社会同类事物的一个范例;让其尊重作者的无形资产成为习惯。我原来的想法是,为了全国人民,我可以不要一分钱让他们改编。但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我决定,我要在合约中要求15万元的作品许可使用费,这笔钱如剧组支付给我,我将悉数捐出。
我至发此文之时尚未同意春晚语言组改编我的小文《量力而行》(即小品《两毛钱一脚》),尽管他们已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已彩排通过,但至今未获原作者通过,这不是我个人和剧组的悲哀,而是我们民族习性的悲哀。
2010.2.8
《马未都说 车上篇》

《故事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