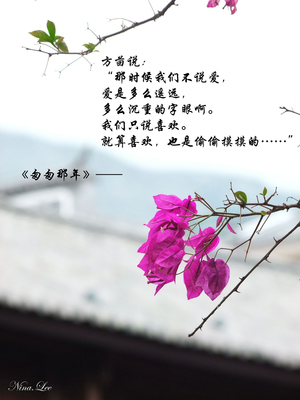四牧场也挤满了淘金客,我们住在当地农户腾空的牛棚里,味道颇不好闻,不过已经比那些露宿街头的强了不少。剩下的几天主要是采购工具和粮食。溜槽、毛毡、金斗子、橡皮水裤、钢钎,十几副铁锹和十字镐,上百公斤的米面,还有不少清油、食盐、砖茶,全堆在一辆架子车上。新疆跟口里不一样,买粮食都是论公斤称的,这点让我印象深刻。
东西采办好后,大哥说今年淘金的人比去年还多,得先上山探路占地方,他领着甘肃老头儿和一个河南人先走,让我和武建超在牧场守着,等他们捎信儿下来,再带着人和东西进山。
我本来也想跟着去,却被大哥揪到一边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什么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我留在后边是为了照看东西,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交给别人不放心。
在阿勒泰淘金,一般初春冰雪刚开化,探路的人就要进山踩点,之后大部队跟进,扎下营盘干上小半年,秋天前就得撤出来。北疆冬天雪太大,山里呆不了人。除非有些大老板发现了富矿怕被别人占了,才会雇人留在山里过冬看场子,好等第二年回去继续淘。2010年新疆闹雪灾,电视上播报十几个淘金客困在深山里,最后被解放军的陆航直升机救了出来,我猜可能是在山里坚守的人,为了一个月几千块钱,却险些送了命。
大哥走后,我们在窝在牛棚里苦等了一个多星期,山上终于送下信儿来。因为牧场离真正淘金的地方还有一二百公里,我们当天下午就雇了辆手扶拖拉机,向大山进发。
***
北疆的初春,仍然寒风刺骨,拖拉机沿着戈壁滩上的砂石路“突突突”的往前开,一路带风,刮在脸上像小刀一样。我们几个人穿着棉袄棉裤挤坐在晃晃悠悠的车斗子上,缩着脖子抄着袖,不停地流鼻涕。武建超爱喝酒,拿出随身带的装酒皮囊,给我们一人灌了几口驱驱寒气。
有个河南小伙子却兴奋地要死,说等淘金赚钱了,他也要买辆这样的拖拉机。新疆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一直很高,而那时的内地农村,几万人的公社才有一两台拖拉机,包产到户分了地,有钱人家也顶多买头小驴儿,也怪不得他眼红。
戈壁滩看似空旷,其实交通线比较固定。我们走的砂石路是条牛羊踩出来的牧道,所以一路上看遇到了不少拖家带口,赶着畜群转场的哈萨克牧民。我大学念的是畜牧兽医,虽说没能毕业,但看到这延续千百年周而复始的游牧生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拖拉机速度不快,天黑时才走完了一半的行程,晚上要继续赶路,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淘金的河谷。其实新疆地邪,当地人都相当忌讳赶夜路,不过那拖拉机师傅没办法,如果他当天下午不走,而是等到早上出发,用一白天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晚上就得自己一人开车回去,还不如七八个人一起走夜路安全,好歹人多有个照应。
司机怕我们夜里睡着了从车上掉下来,说带了个收音机让我们听。可等他把收音机拿出来,全把我们吓着了,心说新疆人用的东西就是剽悍,这哪里是收音机,这根本就是个军用收信机,只不过接着电瓶,又安了个外放喇叭。旋钮一拧,“啪”一声通了电,频道是原先找好的,稍微调了一下,里边就传出了《三套车》的音乐。
奔驰在荒凉的戈壁上,喝着冷风,吃着干粮,欣赏着悠长深沉的苏联民歌,倒也是别有风味。曲子一首接着一首,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却突然没声儿了,静了一会儿之后,“突突突”的发动机躁音中,一个低低的女声缓缓地说道:“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
冷不丁听见这句话,我“噗”的一下把嘴里的干粮喷出来,边咳嗽边骂道:“妈的,莫斯科,苏联电台?”
阿尔泰山北边就是苏联,那军用收信机的功率又强,收到苏联电台倒是一点不稀奇。只是自从1960年中苏交恶起,苏联电台就算是敌台了,尤其是这种针对中国的汉语电台。“文革”那些年谁要是偷听敌台,是要被当做特务抓起来的。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拖拉机转了一个大弯拐进了一个小山坳,突然头一歪,一个急刹停了下来。我心不在焉,差点被巨大的惯性甩下车,其他人也差不多,骂骂咧的问怎么回事,结果大家抬头一看,顿时被眼前的场景被惊呆了——
羊,全是羊,前方不远的小路上,挤挤嚷嚷的一大片站满了羊。拖拉机昏黄的车灯下,竟全是层层叠的羊头和羊背,几乎一眼望不到边。
没听说过大半夜赶羊堵路的,拖拉机师傅把火一熄,气急败坏的跳下了车,打着手电,扒开羊群上前边找人理论。而发动机的声音一停,羊叫声就传了过来,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狗吠,因为羊实在太多,本该断断续续的“咩咩”声响成了一片。
紧随其后的是一股子浓重的羊骚味,大家几乎同时捂上了鼻子,皱着眉头互相望着,一时摸不着头脑。武建超喝了口酒,砸吧着嘴嘟囔了一句:“狗日的,这事儿不对劲。”
其实不光他,是人都会觉得这事不对。我学过这个所以我知道,羊在夜间视力差,很容易走丢,没人会在晚上放牧。而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新疆与内地时差两个小时),转场的牧民早该找地方搭临时毡房休息了,牧道上绝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羊。况且这些羊全是挤在一起不走,这就更古怪了。
****
不一会儿,司机带着一身骚臭回来,身上粘满了羊毛。对我们说前边堵着三四家牧民的羊,一共好几千只。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太阳落山前就这样,不管谁家的羊群走到这儿,就跟当兵的被喊了“立定”似的,齐刷刷的站着不动,头朝东背对着太阳乱叫唤,怎么赶都不走。马和骆驼也一样,狗也不听话,总之全乱套了。
我们问那怎么办?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牧民们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都傻了,不过好在羊也全在那儿站着,没一个乱跑的,倒不用担心丢。
羊不但把路挡了个严严实实,还站满了两边的山坡,拖拉机开不过去,没有办法只能等。我顺着车灯看过去,发现一只只羊果然全是头朝东,嘴里吐着白气咩咩叫,也不知道发的什么神经。
来新疆前就听人说过新疆地邪,我起初还不信,没想到这时自己也遇到了这种怪事。我们几个人还在车上议论纷纷,那拖拉机师傅却变戏法儿似的,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叠黄纸,嘴里念念有词的,蹲在车边烧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好像很多新疆司机的车上准备的都有香烛纸钱一类的东西,按他们的话说,别看戈壁滩上一马平川没什么东西,其实东西多着呢,只是我们人看不见。有时车在哪个地方无缘无故趴窝,怎么修都不行,可纸一烧,车就走了。
不过当时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封建迷信的做法,那堆纸都烧完了,事情依旧没有改观。倒是们这些人都在拖拉机上坐了大半天,浑身又僵又冷,既然一时没法往前,就索性跳下了车,活动活动手脚。别人都抽烟聊天,而我是第一次来新疆,看什么都新鲜,就把司机的手电要了过来,走远了几步想瞧瞧周围的情形。
可没想到只是这随便一看,还真看到了点不寻常的东西。
****
不远处的山坡上,矗立着一个很不自然的小山包。我本来只是拿着手电毫无目的地四下乱照,可光柱扫过那地方的时候,不由自主就停了下来。
那山好像是硬生生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周围都是比较平整的山坡,只有它孤零零的高出一块,显得很突兀,而且是尖尖的三角形,跟这一带圆头的秃山很不搭调。
我正想再走近些看个究竟,武建超却从后边把我叫住了,说天黑不太平,别到处乱跑。我说那个小山包看着挺奇怪的,问他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顺着我的手电筒一看,哈哈笑说那不是什么山包,是一堆石头,天亮了就能看清楚了。
我又问是不是蒙古人的敖包,《敖包相会》我倒是听过。他却摇头,说敖包虽然也是一堆石头,但没这么大,而且上头插得有幡。说完把手电抓了过去,用手电指了几个更远的地方给我看。光线很弱,不过还可以分辨出那是几块立着的长条形块石,歪歪斜斜的站在山坡上。
我说不就几块石头么,又怎么了?他却告诉我那些其实都是石人,上边有刻出来的人脸和衣裳,跟那个大石堆是一起的。类似的石人和石堆不光新疆有,他以前在内蒙也见过,据说外蒙和苏联也有不少。应该是古代少数民族留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倒是不知道。
我还想靠近了再瞧瞧,武建超却一把将我拉了回去,说他凡是到了这种有石头人的地方,心里就会阴测测的不舒服,老感觉要出事,叫我别瞎跑。
我看人家也是好意,就乖乖没去。回到了拖拉机那儿,给他递了支烟,他推开了没要,说自己只喝酒不吸烟。我又问他羊群全堵在那儿不走,会不会也跟这些石头人有关?他有点犯疑,不过又摇摇头说不会,新疆春天羊赶雪,牧民春秋两季转场都要走这条路,以前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
我还想再说,却见他突然冲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别出声。我跟着一愣,这才猛的意识到周围的气氛很不对头。
因为刚才,除了我们俩,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在说话。
牧民转场的场景。
(博客中的图片,有些是在天涯连载时热心网友搜集发上来的,有些是本人在网上找的。如果原作者认为此举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早告知,我会立即删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