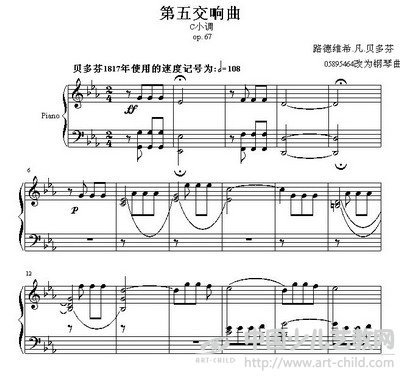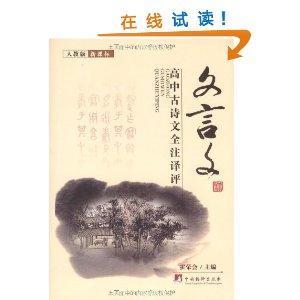马勒的《第二交响曲》,C小调,作于1894年,因为末乐章使用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作《复活》,而命名为《复活交响曲》。这部作品,1895年3月4日由理查·斯特劳斯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首演了前3乐章,1895年12月3日由马勒自己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首演全曲。全曲包括5个乐章。
庄严肃穆的快板
⒈庄严肃穆的快板,C小调,指示“专心认真,而且要有庄严的表现”。第一乐章的题名为“葬礼”,马勒曾这样解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所送葬的是我的《第一交响曲》的主角,我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整个一生仿佛在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司时它又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生存的目的何在?你受苦是为了什么? 这是否全都只是一个可怖而巨大的恶作剧呢?我们全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答复就在最后乐章中。”这一乐章用布鲁克纳的开始方法,在弦乐衬托下,断断续续奏出第一主题,越来越强烈后小提琴奏E大调柔和的第二主题。第一主题再度出现时,全部管乐奏圣咏风格旋律。呈示部小结尾前,圆号与木管奏葬礼进行曲。发展部可看作3部分,第一段小提琴以C大调优美地奏第二主题开始,低音弦乐奏第一主题动机,鼓荡加强后又趋平静。长笛奏第二主题,开始抒情的第二段。第三段又以第一主题动机加强而出现高潮,最高潮达圣咏风格的旋律,回到C小调而进入再现部。再现部比呈示部的对位更为精彩,结尾部变成葬礼进行曲,最后以下行半音阶风格结束。
中庸的快板
⒉中庸的快板,降A大调,指示“极为轻松地,绝不可急躁”。马勒把第二与第三乐章当作跟在葬礼后的间奏,回忆和幻想。他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了一个你所亲近的人的葬礼,然后,也许在归途中,你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幅很久以前的欢乐时刻的画面,就像一线明媚的阳光,没有任何云遮雾障,于是你可能把刚才发生的事几乎忘掉,这就是第二乐章。”这一乐章如舒伯特的兰德勒舞曲般明朗,用了两次中段。第一个中段,圆号与小提琴对应细微的动态,升G小调。回到降A大调后,轻快的主题再现,第二中段更活泼而富色彩。然后主题以第三次弦乐拨奏再现,木管接替。
G小调
⒊G小调,缓缓流动的动态,三段体的谐谑曲。这个乐章运用了马勒的歌曲集《少年的魔角》中的《圣安东尼向鱼儿说教》的旋律。此歌曲描写帕图亚的圣安东尼在湖岸上长时间耐心地向鱼儿布道,劝说它们改变贪馋的本性。鱼儿愉快地聆听布道,但过后重又各自追逐自己的猎物果腹。这个乐章是幽默中带有讥讽。马勒这样解说:“当你从怀念的白日梦中醒来而必须回到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中时,那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日常活动,没有意义的喧嚣奔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不寒而栗,仿佛你在注视着灯火通明的舞厅中旋风般起舞的人群——而且是在外面的黑暗中看着他们,离开那么远,因此听不到那里的音乐。这时,人生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可怖的鬼域世界,对它,你将发出一声憎恶的喊声而退避三舍!”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像流水一样奏出主题,这个乐章以各种乐器加入来进行层次刻划。中段由低音弦乐以断奏的动态开始,表现出明朗的旋律。两种旋律以发展风格作立体性进行,经对比后,自由地再现第一段,以片断性再现主题而结束。
降D大调
⒋降D大调,指示“极为庄严,但是简朴地”。这个乐章记有“原光”的标题,马勒说明:“传来了单纯信仰的歌,我变得像神一样,也许我将回到神的身边:”这个乐章是末乐章的引子,由女低音独唱,歌词大意是:“啊,红艳艳的玫瑰含苞待放,人类多少贫困,人类多么悲伤,我多么希望走向天堂,我来到宽广洁净的大道上,有个天使,他想把我前进的道路阻挡。不,我不听他的话,我决不回头。我从上帝那儿来,我回上帝那儿去,亲爱的主将赐我一丝微光,他将照亮我的路,永恒的幸福日久天长。”
解说
⒌马勒对这个乐章的解说是:“在荒野中传来如下声音:人类的末日已经到来,最后的审判日已经临近。大地震动,巨石裂开,僵尸挺立,人世间伟大的与渺小的,帝王与乞丐,正直之士与不法之人都一齐走来。伟大的声音传来,启示的小号在呼唤。于是在可怕的静寂中,尘世生活显示出最后颤栗的姿态。夜莺之声远远传来,圣人与神合唱‘复活吧,复活吧,你可能被宽容。’然后出现神的荣光,奇异而柔和的光慢慢渗透我们内心。所有的一切归于沉默而幸福。在那里没有任何审判,也没有罪人,没有正直的人;没有强权,也没有卑贱,没有惩罚也没有报应。爱的万能的感情,净化了我们走向幸福的极致。”这个乐章共3段.第一段指示为谐谑曲速度,标题为“在荒野中呼叫的人”,相当于呈示部,以强烈的音响开始,以长号表现第一主题,圆号轻轻地以C大调进行曲风格奏出第二主题,木管奏第三主题与第四主题,其中长号透示出关于复活的动机。第二段相当于发展部,又分为两段。第一段为第一主题与第三主题对位性的多彩发展,通过缠绕而表现紧张,紧张平静地进入第二段。第二段发展第四主题,结尾第一主题亦登场掀起高潮。第三段是“伟大的呼声”,以合唱为中心。先以第二主题开始,以长笛与短笛的缠绕表示夜莺的叫声,然后开始克洛普施托克的圣诗《复活颂》。马勒在创作这首交响曲达到末乐章高潮时,曾苦于找不到理想的结尾。著名指挥家彪罗去世,他参加他的葬礼,听到在管风琴旁的合唱团唱起《复活颂》,他说,当时“我所感到的心情,想到的死亡,与我所作的作品精神完全一致。听到克洛普施托克的复活合唱,像是受到电击一样,我受到了感动。”在这里使用的合唱歌词是:“我这一把尘土,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复活。神召唤了你,他将给你不朽的生命,像种子一样你将被播下又开花结果。收获之神继续前进,刈割亡人,如捆禾束。”然后是女低音、女高音和合唱:“请相信,我的心灵,你的追求不会成为泡影。凡是你所渴望的归你所有,凡是你所爱和所奋斗的,归你所有。请相信,你的生命并非白白度过,或生存或痛苦,无不有因。凡已生者必死,凡已死者必将再生。不要再颤抖,复活就在眼前。痛苦无时不在,但我能逃脱痛苦。死亡能征服一切,如今也被我所征服。”最后则是凯歌式的合唱:“展开我已为自己展开的翅膀,我将高高飞翔,心中感情激荡,把世人难见的光明寻觅。我将死去,为的是求得复括。你将复苏,我的心灵,复活只在朝夕。你的奋斗的英雄搏动,将把你带到上帝身边!”最后,形成巨大的高潮,圆号以第二主题带动其它管乐器,在崇高的音响中结尾。
听马勒应该止十年了。最早接触的是瓦尔特和哥伦比亚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一第二交响曲,CBS的正价双张,当时中国公司唱片门市部卖78元。听完之后很是喜欢,陆陆续续又听了第五,第四,第九,第八,还有《大地之歌》。《爱乐》创刊之后,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马勒第二,题目叫作《生的渴望与死的超越》。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再听,发现很多与作品相关的事情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包括思想和音乐层面两方面的问题,因此那篇文章了语焉不详。只好正本清源,重新来过。
家
卡里希特,靠近莫拉维亚边界的一个波希米亚的小村。这里是马勒出生的地方。在德国出品的一个有关马勒的纪录片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村庄,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不大的村庄还是那个样子,静悄悄的:池塘,木屋,栅栏,缓坡的绿地,稀疏的树木,还有掠过小村上空的风……马勒家的木屋样子极其普通,屋顶很大,带阁楼的那种,不止一本传记上说马勒家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可是谁能料到,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的古斯塔夫却给20世纪西方音乐的历史开启了一扇刺目的窗。
这个小村不可能给马勒留下什么印象,他只在这里长到半岁不到。影响他生命和艺术进程的应该是伊格劳,一个布拉格与维也纳之间的带有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城镇。由于帝国对犹太人居住管制的放松,他跟随父母搬到这里,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吧。随着他的长大,不和谐的家庭生活让他感受到压抑,积淀在他的心里,家庭的阴影毫无疑问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马勒在对一个朋友谈到前两部交响曲的创作时说,它们包括了“我全部的生命内核,我把我所经历和忍受的一切统统写进了这两部作品……要想真正了解这两部作品,就要透彻地了解我的生活在作品中的流露。”16口人的家,留给马勒的大多是痛苦的回忆:粗暴的父亲是个勤奋的酿酒商,他所作的唯一的好事就是让马勒拥有了一架钢琴。前后生过14个孩子的病弱的母亲,却一天也没有得到过爱。父亲的固执和母亲的温柔是水火不相容,他们之间长期的紧张的精神状态造成了马勒异乎寻常的压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构成了马勒矛盾的心理结构和音乐风格。弗洛伊德记载的那个故事是可靠的:晚年的马勒给心理分析大师讲述了童年的遭遇,每每无法忍耐父母的争吵夺门而出的时候,碰上的却是街上手摇风琴的滑稽的歌谣。重与轻,严肃与幽默,悲愤与嬉笑,这些天生对立的因素奇异地贯穿了马勒的全部作品,早期的作品自然了不例外。
家庭成员不断在减少,死亡的气息似乎总是在家中盘旋,14个兄弟姐妹前后夭折了7个,(到1896年只剩下4个)这让马勒直接面对了死亡的残酷。弟妹们被运走的小棺材,他们垂死前的境况,无疑都给马勒以刺痛的感觉,他的一个妹妹甚至在临死前还做着游戏。马勒回忆说:“她在床的四周放上蜡烛,随后躺在床上,把蜡烛点燃,她本人几乎完全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另外一个弟弟恩斯特的死对他刺激更大,那是他少年最好的玩伴。马勒在早期的一部歌剧习作中表达了弟弟之死的哀伤之痛。不妨想想,自贝多芬以后,有哪个作曲家在早期作品中就把葬礼进行曲作为交响曲的一个乐章?只有马勒。在第一交响曲中,你可以听到不可思议的阴郁和带有讽刺性的欢乐,怪诞而且绝望。用马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受到严重创伤的心灵经历了送葬行列的阴风惨惨和愁云密布”。家庭的阴影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第二交响曲的开始,劈头就是葬礼进行曲,把他以前所作交响诗《葬礼》几乎原封不动照搬过来。张力巨大,恰似风狂雨骤,撼人心魄。“我把第一乐章称为《死者的葬礼》,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那就是我的D大调交响曲(即第一交响曲)的主角,我把他带到墓地,我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出发,在一面纯净的镜子里看到他的一生。”(见马勒与他的朋友马尔夏克的通信)马勒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懂得了跳出家庭悲剧对死亡作更高层次的思考,其实马勒一生都在不断反躬自问,在音乐中苦苦探求生命的意义。当那个时代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都把死亡与生命的意义当作头等问题来思考的时候,马勒也同样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生存的目的何在?你受苦是为了什么?这些是否全都是个可怕的恶作剧呢?我们都要以某种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同上一封信)在救赎与永生的宗教困惑中,马勒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而最终在第五乐章里才给出了答案。此是后话。
第二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是一首悲惨世界和哀伤心灵的挽歌,它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而成为世纪末的悲歌。对于马勒来说,如果说家在狭义上是个噩梦的话,在广义上则是生命个体的无所归依,而且是三重的无所归依。正如后来他的说的那样,“奥地利人说我是波希米亚人,德国人说我是奥地利人,其他地方的人说我是犹太人。不管去哪儿都是外人,永远不受欢迎。”长达20分钟的第一乐章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葬礼进行曲,一首悲歌,或像贝多芬《英难交响曲》那样的挽歌,它要更苦难深重些,是对毫无意义、充满矛盾的人生一个争辩性的、寻问性的探索。马勒曾经说,演完这个乐章后至少要有五分钟休息的间隔,用来反思,反省。足见其伤痛之深。
回忆
在缺少家庭欢乐的环境中长大,在严父的恐惧中心理痉挛,暂时的逃脱是一个男孩儿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伊格劳的家门外,教堂,街巷,广场,军营,每天进入马勒的视线。犹太人集会就在离他家不远的教堂,犹太儿童和天主教文化环境之间似乎还有着莫名的紧张,街巷里,可以听到捷克女仆的歌声,上学路上,在市中心广场经常看到操练的军队,听到他们整齐的脚步,各种号声和进行曲,而在郊外,林木葱郁,鸟鸣欢歌,大自然的抚慰成了最好的解脱。于是,犹太圣歌,军队进行曲,奥地利民间舞曲,一股脑儿地混杂在他的脑海里,它们相互叠加、覆盖、融合、甚至变形,走进他的梦境,保存在他的记忆深处。这些片段的旋律在他四五岁时幼稚的儿童口琴里吹响,在外祖父母家阁楼上的那架破旧钢琴上跳跃,多少年后蔚为大观,终于形成了他解释世界的宏大篇章。
回忆是一条逃遁之路,让人暂时淡忘了死亡的片断。那些在生活中淡漠的形象,偶尔闪现的幸福的影子,有时会像思念的歌调响在作曲家的耳际。马勒把第二乐章当作跟在葬礼后的“间奏”、回忆和幻想。这是瞬间的温情回顾,沉重的送葬之后的喘息。他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了一个你所亲近的人的葬礼,然后,也许在归途中,你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幅很久以前欢乐时刻的面面,就像一线明媚的阳光,没有任何云遮雾障。于是你可能把刚才发生的事几乎忘掉,这就是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是明朗快活的兰德勒舞曲,这种奥地利的乡村舞曲,让人想到自然之美,山水,田园给人类的慰藉。我们知道,这里的自然同他的出生地卡里希特没有直接联系,但与伊格劳郊外他童年的快乐息息相关。当然,马勒这时已在阿特湖畔的斯坦因巴赫建造了他的第一座夏日“作曲小屋”,眼前更为直观的湖光山色与往昔的回忆一同激发了他的创作活力,大自然的美轮美奂任你怎样想象都不过分,就像马勒所说的,在我的世界中,整个自然界都发而为声。
从承继关系上说,这个乐章有些像舒伯特交响乐中的舞曲风格,明朗、温暖而平静,但并不十分欢快。在这里,人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马勒“歌者”的本色。圆号与小提琴细微的对应,轻快的木管,弦乐的拔奏,一切都是内心的歌唱。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中所表现的大自然的明朗和清,人与大自然交融一体的狂喜心情,以及他所营造的爱情和幻想的园地,青春和生命的礼赞,在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中得到些微的回应。
书
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作曲家不同,少年马勒沉迷于书本,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创作带有许多哲学层面的思考。父亲简陋的“家庭图书馆”是小马勒另一个痴迷的去处,这些书给了他很好的文学基础。所以有专家说,马勒音乐最根本的影响来源有二个,一方面是他所处的童年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年幼时期爱不释手的书籍。其中深得他心的是一本题为《少年魔角》的德国民歌集,对德国人来说,这本歌集就好比是一本家庭必备的书,其中充满了大量玄思妙想的超现实主义故事。
歌德曾给予《少年魔角》以高度评价:“这部小书应该被放在每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的家里,在窗旁,在镜下,或者和歌本、烹饪书放在一处,以便在每个欢乐和苦恼的时候打开它。人们在里面总能找到相通或令人振奋的东西。”其中有战死的士兵听到归营号而魂兮归来,圣安东尼向鱼群布道,毛驴给杜鹃和夜莺的歌唱比赛作裁判,这些光怪陆离的角色与镜像对马勒产生了魔幻般的吸引力。接下来歌德还说,“最好把本书放在音乐艺术爱好者或者大师的钢琴上面,他们应该把里面的歌用喜闻乐见的流传下来的旋律进行处理……若是上帝高兴的话,那就通过它们引来新的有意义的旋律。”也许冥冥之中马勒得到歌德的引领,或是受到了上帝的眷顾,这本奇异的“百宝书”真的让马勒写出了“新的有意义的旋律”,而且让他终生受益。
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892年,马勒发表的14首钢琴伴奏曲中,有9首是根据《少年魔角》谱写的,马勒还把它们写成了乐队伴奏版。布鲁诺·瓦尔特称,马勒在《少年魔角》中找到他的精神故乡,找到了震撼他灵魂的一切:虔诚、自然、相思、爱情、离别、死亡、幽灵、儿童的嬉戏和粗俗和幽默,所有这些在马勒身上活了起来,他的歌喷涌而出。可以说,没有《少年魔角》的浸润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听到的马勒。当第二乐章那瞬间的美梦被惊醒的时候,幽灵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面前。这就是第三乐章。
马勒再次运用了《少年魔角》中的《圣安东尼向鱼儿布道》的大段的旋律。原曲是一首讽刺歌,讲的是帕图亚的圣安东尼因为没有人上教堂,故而改为向鱼群布道。鱼儿欣然聚集,然而听完说教后依然旧习难改,贪婪的照样贪婪,淫荡的照样淫荡。就像刚刚参加完礼拜仪式的人类那样,在尘世放纵的生活中重又追逐自己的欲望。马勒没有用原来的歌词,但原诗的讽刺、戏谑精神在此十分传神,幽默中带有辛辣的讥讽。对此,马勒这样解释道:“当你从怀念的白日梦中醒来而必须回到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中时,那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日常活动,没有意义的喧嚣奔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不寒而粟,仿佛你在注视着灯火通明的舞厅中旋风般起舞的人群——而且是在外面的黑暗中看着他们,离的那么远,因此听不到那里的音乐。这时,人生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可怖的鬼域世界,对它,你将发出一声憎恶的喊声而退避三舍!”
音乐里散发着讥诮的幽默,仿佛是狂乱的女巫之舞,这是马勒怪诞而邪恶的谐谑曲的经典篇章:每日的生活在偏狭、忌妒和琐碎中延续,旋转,无休止地旋转。这首谐谑曲还有更多马勒式的“世俗”风格特色,那是街巷、酒馆式的音调,粗野、鲁莽、俚俗。“一种粗野的幽默和剧烈的闪光照亮了它那邪恶阴沉的表面,然后出现在一声哀怨的荒野的呼唤之中”,瓦尔特这样评说道。
诙谐与粗鲁的表面掩盖不了心理暗流的涌动,痛苦也痛苦了,回忆也回忆了,笑闹也笑闹了,但生与死的困惑并没有消失。音乐的节奏也同心理一样,三个乐章一动,一静,又一动,等待解决。
呼告
尘世间如此多的困顿,让作曲家不得不仰望天空。女低音唱出纯净动人的《原光》,歌词还是来自《少年魔角》中的一首诗,旋律是马勒创作中最优美的。这是马勒交响曲中第一个有人声歌唱的乐章,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来第一次有人在交响乐作品中引入人声。就像谱子上标明的那样,曲调“极为庄严”,但同时又是那样的“简朴”。
马勒这样说道:“传来了单纯信仰的歌,我变得像神一样,也许我将回到神的身边。”《原光》(也译“原始之光”),多么耐人寻味的字眼。走投无路的马勒在转向上帝之后,终于见到了希望之光,再生之光:
人类多么贫困,
人类多么悲伤,
我多么希望去天堂,
我来到宽广洁净的大道上,
有个天使,他想把我前进的道路阻挡。
不,我不听他的话,我决不回头。
我从上帝那儿来,我回到上帝那儿去,
亲爱的主将赐我一丝微光,
他将照亮我的路,
永恒的幸福日久天长。
简明的呼告,坚定的信靠,一个女声从悲伤沉痛、压抑低沉中慢慢升起,变得明朗宽广,意志坚决。这是末乐章的引子,在末日审判之前,心灵暂时得以片刻的安息。
解脱
把最后的乐章写成合唱,这是马勒心仪已久的事。他急于找到能够充分表达“永生救赎的辉煌境界”的合唱歌词,就像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以席勒的《欢乐颂》来传达“四海皆兄弟”的理想境界那样。但翻遍了世界文学名著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歌词,包括到《圣经》原文中去搜寻。深层的原因是担心别人会指责他模仿贝多芬,他在心理上翻越不过这座精神的高山,所以犹豫再三,踟蹰不前。第二交响曲在这里停下来,马勒陷入了“长考”。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指挥家彪罗在1894年去世了,马勒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葬礼。当管风琴旁边的合唱团唱起克洛普斯托克的圣咏《复活》时,马勒刚听到第一句歌词“复活,是的,你将复活”,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我的灵台霎时间一片澄明,一切都迎刃而解。”马勒在音乐中表达了他的希望和信仰,用雄伟的音乐第一次解开了萦绕在他心头的忧伤、悲悯和疑虑。
末乐章是一个狂暴的开始,倏然而出,令人恐怖。毕竟要面临末日的审判,一系列精神形象和音乐进程之间显现出不安和矛盾。马勒精力设计了所谓“远程乐队”,四支小号从相反的方向吹响,声音不仅从音乐厅的舞台上传达到观众那里,而是从四下里传来,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空间音响。于是,人们听到了末日审判的立体声响,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聆听感受。至此,马勒把空间的构成和宗教思想的构成高度凝结在一起,让音乐厅与教堂的功能合二为一,让肉体的复活提升为精神的复活。这不能不说是个创举。
远处再次传来最后的号角,在此之上,独奏长笛(象征一只夜莺)犹如天籁之声。在一片寂静之中,无伴奏合唱轻缓地进入,唱响了复活的圣咏。马勒自己写了一段歌词来代替圣咏的最后部分,用来回答第一乐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展开我自己的翅膀,我将高高飞翔……我将死去,为的是获得重生。”独唱合唱昂扬澎湃,铜管高奏,钟声大作。痛苦被挣脱了,死亡被征服了,死亡境界提升为生命的不朽,铸成生命的永恒。马勒确信自己找到了神,“一股大爱照澈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与道为一。”
整首交响曲可以看作是一个青年人的悲剧人生,经历了青春的埋葬,美好的回忆,自我解嘲的戏谑,进而超越死亡获得永生。在第二交响曲中,马勒不仅表现出对救赎的信念与希望、对神秘激情的探索,更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困顿、混乱、欢娱、荒谬、怪诞等多个层面,展示了从怀疑、绝望到对信念的渴望与恢复,精神的再生这样一个复杂混沌的心路历程。马勒想要建构贝多芬式的交响建筑,只是规模更庞大,意志更执著,态势更逼人。他的创作模写了一个正在逝去的时代,在歇斯底里的表达中时时感到力不从力。梅纽因说他是“冲着迅速弥漫的黑暗大声喊中,试图挽救已经迷失的生活方式,同时努力抑制着对不可抗拒的变化的恐惧。”这一点看的是很准确的。
美国音乐学家列奥纳多则认为,“在创作第二交响曲时,马勒就打算谱写由普罗米修斯式的奋斗,启示录式的幻想,史诗般的葬礼进行曲和世界最后的复活构成的音乐系列,以此来超越贝多芬第九。”可惜生不逢时,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波浪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鼎盛时期的高峰。作为终结者也是挽歌者,马勒的一生大部分被持久的悲哀所纠缠,对世界的悲观笼罩了他和他的音乐:圣歌式的赞美,贝多芬式的冲突,英雄式的辩解,遥远号角的召唤,最后审判的号声,黑暗而阴郁的感伤,偶尔穿插着欢乐的民歌和舞曲,军队进行曲,宁静的自然……把一堆如此复杂的素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对于前辈大师尚且不易,到了马勒手里自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古斯塔夫·马勒是当今最迷人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吸引了今天几乎每一个指挥家去指挥,而且也让众多的听众们为之着迷。在马勒的作品里,他将自己带入到种种假设的情境中,并通过自己的种种感悟来阐释人生的意义。因而,马勒追求的交响乐要涵盖整个宇宙万物,要描绘世上一切事物的精神也吸引了今天的很多人。因为极少有作曲家的作品如马勒那样,曲如其人。马勒擅长树立一个英雄形象,并将自己带入这个英雄形象中。而且,这个英雄形象不仅贯彻了他的某一部作品,而且也贯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这种手法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已经确立。在他的第一交响曲里,作品的开头部分的那种万物初创,由混沌走向有序,并且欣欣向荣的气息就预示了马勒的时代的来临。确实,马勒第一交响曲里开创的世界成了他之后的所有作品的大背景,以至于我们无论再听他的什么作品,都能找到这个英雄的影子。然而,他的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并不成功,甚或说是遭遇了当时观众的巨大的排斥。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勒在他的第二交响曲的一开始就安排了一个葬礼进行曲。
马勒是一个非常擅长写葬礼进行曲的人。他在第一交响曲里,就用了一种谐谑的手法描谱写这种死亡的音乐,以至于那段音乐听起来既荒诞又诡异,甚至带有着一丝邪气。而马勒的第四交响曲里,这种邪气就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在第二乐章里,代表着魔鬼撒旦的小提琴引诱着孩童走向那未知的黑暗;然而倘若在不知道这个背景的前提下去听这个乐章,则又是一个非常优美欢快的乐章。而在他的第五交响曲里,我们又看到了与第二交响曲相仿的开篇就是葬礼进行曲的结构。如果说,第五交响曲开篇的葬礼进行曲是预示着第六交响曲最终的幻灭的话,那么第二交响曲开篇的葬礼进行曲则显得单纯得多。
第二交响曲开篇的葬礼进行曲多少带有一些埋葬第一交响曲首演的失败带来的阴霾的意思。这点不难理解,在初出茅庐的第一交响曲遭遇失败之后,马勒那种敏感脆弱的心理必然会影响他之后的交响曲的创作。而实际上,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并不是马勒在那个时候写成的,而是之前的一部不太完美的作品《死之祭奠》。因而,选择这部作品作为第二交响曲的开篇其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马勒不会单纯地为了用葬礼进行曲开篇而这么写。实际上,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有着共同的英雄形象。在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当那一声镲过后,随之而来的管弦乐一片欢腾便将英雄从地狱拉到了天堂。那么在第二交响曲里,马勒延续了英雄的死亡,将这种死亡进行了进一步地深化和升华,并将英雄的这个形象大而化之。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写的作文,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发,最后一定会用某个道理或者哲理作为总结。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也是如此。而且,最后的这个哲理带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而马勒的宗教情结也在这部作品里暴露无遗。
马勒是一个很喜欢连得勒舞曲的人。这大概跟他的身世有关。而且马勒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用到了连得勒舞曲。比如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乃至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不得不说,连得勒这种奥地利乡村舞曲在马勒的笔下焕发出了非常多样化的色彩。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正如马勒所言,当你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葬礼后,你难道不会回忆一下有关这个人生前的许多美好的事情吗?那么这个第二乐章也是这样。
没有过分的悲痛,也没有马勒一贯对死亡的妖异的描写手法,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乐章,优美得令人心碎。主题三次变奏,第二次以大提琴醇厚优美的音色呈线性流畅的演奏,而第三次则是弦乐的拨弦,以点盖面地将主题呈现。年轻时的马勒并不像他后期的作品里看起来的那样神经质。相反,在他的早期的作品里无处不流露出浓浓的田园风情。而正是在这种田园风情里,马勒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生前的美好的回忆。
第三乐章是马勒创作的最为绝妙的乐章之一。它有着非常富有流动感的旋律,处处流露出灵性,并且极为神似意识流。这个乐章的旋律就像托卡塔一样地流动着,欢快,狡黠。后来,这个乐章的主题也大量出现在贝里奥的交响曲(Sinfonia)里,并被贝里奥理解为这个乐章可以看成是“一种近乎意识流和梦的解释。因为那种流动性,是马勒诙谐曲最直接的表征。它像是一条河流,载着我们途经各种景色,而最终消失在周围大量的音乐现象中。”
而马勒在这个乐章里所要描述的,也是一个非常狡黠的故事: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向鱼类布道。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森林里的动物们该如何体面地生活,要互相友爱,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而森林里的动物们在此刻也极为认真地聆听着。然而当布道结束后,动物们马上又四散开来,过着与之前并无二致的生活。
其实,马勒在这个乐章里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哲学命题。他在用这则寓言影射当今在世的人们:人类虽然拥有着高科技,可以环游整个地球,甚至踏上了月球,但人类的情商,或者说人类的心智却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就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草履虫一样,依然有着非常明显的趋利避害的行为。马勒以他的形式在这里挖苦人类,因为人类不肯追求更高的道德束缚,不肯从过往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更为了世俗的财物而放弃道德的约束。所以,这个第三乐章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谐谑曲,但其内涵却是极为深刻的,其哲学命题之尖锐和深刻也是古典乐作品里少有的。
紧接着,当一声吊镲的叹息声过后,便是短小却又深邃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初光”是一段非常宁静而又深刻的与灵魂和上帝对话的音乐。从歌词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勒对于人生世俗的生活以及人死后该何去何从的思考。他像一个孩子一般地渴望上帝的一点点亮光,希望被这点亮光指引过上幸福永生。
马勒是一个相信来世的人,所以他对复活的理解也依附于他向往的来世。而这种复活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复活。这在第二交响曲的末乐章里将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阐释。
在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初稿里,作品本该到此结束,因为马勒实在找不出足够匹配的素材来引导出这部作品更为深刻的内涵。直到他参加了汉斯·冯·彪罗的葬礼,并在克罗普斯托克为之所写的赞美诗“复活”中获得灵感,以此完成了恢弘的末乐章。
第二交响曲的末乐章是一段效果惊人的幻想音乐。在这个乐章里,马勒以天马行空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异常玄幻的场景。从这个场景里,我们不难发现马勒追求音乐涵盖宇宙万物的精神。我们可以窥见天地初开,太初有道的那一刻,也可以窥见万物复兴,欣欣向荣的一刻,更能通过合唱团唱出的赞美诗窥见马勒对上帝的赞美。的确,能驾驭如此复杂的线索,充分地调动每一样乐器以及庞大的合唱团来完成这个乐章,也只有马勒能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乐章里,合唱团之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勒以他极强的戏剧性张力和丰富的音色表现力所构建的这个乐章,也是其对来世所谱写的一个序奏。当场外的铜管乐响起的时候,我们不难联想到《圣经·启示录》里有关天使的七个号角的传说。只不过,在《圣经》里,天使每吹响一个号角,地球便被毁灭一部分;而在马勒的这部作品里,号角只是一盏灯塔,指引人们走向美好的来世,过上幸福永生的生活。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来世?它是怎样到来的?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光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是不够的。马勒有着非常强烈的宗教情结,这种宗教情结不亚于布鲁克纳。所以,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圣经中对于“复活”和“来世”的记载。想要理解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从“哈米吉多顿大战”开始。
所谓“哈米吉多顿大战”,实际上就是上帝与魔鬼撒旦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是上帝最终打败撒旦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撒旦纠结了地球上各地的王,在哈米吉多顿联合起来与上帝对抗。联合起来与上帝对抗的地球上的诸王象征着地上的世界的堕落,因而,上帝就会毁灭这个世界,并创造出“新天新地”,也就是之后的“地上的乐园”。
那么,人类该何去何从?圣经记载,当“哈米吉多顿大战”结束之后,凡是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都会被复活,并且接受上帝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具体的实施者是耶稣基督,上帝是作为最终的审判者以及实施者存在的。在某些教派里,凡是被上帝审判为有罪的人,都必将在地狱里囚禁,被审判为无罪的,都将在天堂过幸福的永生生活;而在有些教派里则认为,凡是被审判为有罪的,都将获得一个重新认识上帝并接受上帝统治的机会,并同那些被审判为无罪的人一同在今后地球上的“新天新地”,也就是地上的乐园里过幸福的永生生活,而只有14万4千人才能升到天上,与上帝和耶稣基督共同统治地球。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审判在圣经里是具体的记载着的,而这种审判的前提就是“复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勒的复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马勒对上帝的依赖,也就不难理解马勒对来世的向往,也就不难理解马勒对死亡的描写。
但是,“复活”这个线索在马勒第二交响曲里的走向,在作品的结尾的合唱里却峰回路转了。从合唱的歌词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审判”这个字眼,甚至我们没有看到审判的实施者“耶稣基督”的字眼。也就是说,没有审判。审判没有了,所有人都平等了,人人就好像婴儿的诞生,自然而然地从一个世界过渡到了另一个世界。于是,众人唱出了虔诚的赞美歌,赞美来世的幸福生活,赞美上帝的仁慈,因为没有了审判。
至于马勒为什么有意略掉了审判,这恐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可能会跟弗洛伊德对马勒的研究扯上关系,所以在这里就不具体研究了。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马勒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人物,任何人对马勒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而在一定的宗教背景下来看马勒,恐怕其深邃复杂、敏感脆弱的心理又会有着更新的解释。
但无论如何,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已然成了他的除了第八交响曲之外最受欢迎的交响曲之一,也是内涵极为深刻的交响曲之一。这部交响曲阐述了马勒对于人类最终去向的看法,并且试图探求终极的答案。然而,正如他没有描写审判一样,所谓终极的答案恐怕也是不存在的。所以,马勒才有了之后的更多的作品,也从更多的角度和深度来诠释他对于人生的看法。也许,最终马勒发现了,终极的答案可能真的并不存在,任何精神都将会像第九交响曲那样,化为了一缕青烟,然后一切皆不复存在。
第四乐章 原光
啊,红玫瑰!
(女低音)
啊,红玫瑰!
人间的灾难深重之极!
人们的痛苦深沉之极!
我希望生活在天国里!
我来到宽广的道路上;
一位天使来临,要我返回。
不!我不回去!
我来自上帝,我要回归上帝!
亲爱的上帝会赐予我光,
照亮我永恒幸福的生命!
第五乐章 复活
(合唱队与女高音)
复活吧,我的身体,
经过短暂休憩,你将复活!
主召唤你,
将赐予你永恒的生命。
你将再次得到播种、开花!
我们死去后,
主收留我们,
如同收获麦捆!
(女低音)
请相信,我的心灵:
你的一切都未失去!
你曾渴望并为你所有的,
你曾热爱并为之奋斗的,都未失去!
(女高音)
请相信,你的生命并非徒然,
你的生活和苦难并非徒然!
(合唱队与女低音)
凡已生者必死,
凡已死者必复活!
停止颤栗!
准备再生!
(女高音与女低音)
啊,无处不在的痛苦,
我已将你解脱!
啊,征服一切的死亡,
如今你被征服!
我将展开获得的双翼,
在爱的热烈追求中
高高飞翔,
飞向肉眼看不到的光芒!
(合唱队)
我将展开获得的双翼,
高高飞翔!
我将死去,因此而永生!
复活吧,你将复活,
我的心灵将在顷刻间复活!
你曾为之奋斗的
将引导你前往上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