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与烘托是古典诗歌创作中描摹形象的常见的艺术手法。
渲染原本是国画的一种画法:用水墨或淡的色彩涂抹整个画面,显出物像阴阳向背,以加强艺术效果。这种加浓形象的手法,就是渲染。诗歌中也常常用到这种艺术手法。
诗歌中的渲染,属于对形象的正面描写。其形式之一就是借助反复来突出形象,抒发感情,创造出优美的意境。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诗的中心形象是写采莲少女的,但作者并没有直接描摹她们的形象,甚至自始至终也没有让她们在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过,诗中只是着意涂抹、反复描写“鱼戏莲叶”的不同画面,但其艺术效果却是把采莲少女采莲时的愉悦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渲染手法的妙用。
借助各种意象的描摹,来加浓环境气氛,以便更好地刻画形象,也是渲染的表现形式之一。例如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诗的前六句先后描绘夕阳西下、群壑昏暝、松际月出、风吹清泉、樵人归尽、烟鸟栖定等生动的意象,正面渲染出清幽的环境气氛,这就为下面生动地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作了渲染,使人好像见到诗人正抱着琴,孤零零地伫立在洒满月色的萝径上,望眼欲穿地期盼友人到来的情景。
为了表达深刻的主旨,传达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还常常采取多角度、多层面的描摹手段,尽情渲染,来刻画形象。例如寒山的《城中蛾眉女》:“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诗的前两句,写一位美女的花容月貌和华贵盛妆。“蛾眉”,形容她的美丽,“珠佩珊珊”,描写她佩带珠光宝气的神态。两句诗把这位美女写得有声有色,光彩照人。三四句分写她的生活情状:白天,她在花园里戏逗鹦鹉;晚上,她静坐月下弹琵琶自乐。五六句写她的出色的社交活动,经常出现在宴会场合,无论是长歌,还是短舞,她总是让万人欣羡,久久陶醉。这六句诗,从正面很好地描写了美女的荣华富贵、闲雅生活、特殊地位,为下面诗人向世人发出的“一切美景都不可能永远存”的忠告储足了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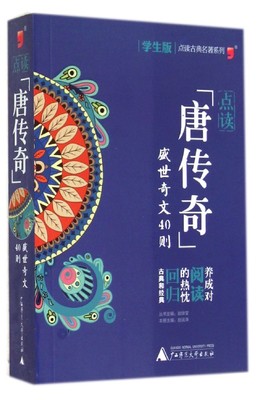
烘托是与渲染密切相关的另一种艺术手法。它也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像的轮廓外面点染涂抹,使物像明显突出。用于诗歌创作,则指从侧面着意描写,作为陪衬,使所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他所说的,就是烘托的手法。
对事物进行侧面描写的烘托,其艺术效果,可以与正面描写的渲染相媲美。例如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诗的开头两句写的是在花门楼前酒店的一位老人热情待客、美酒飘香的情景,用的是白描手法,但却很好地烘托出边塞安定、百姓安居的时代气氛。正因为从侧面烘托出了这样的淳朴动人浓浓情意,下文才可能“戏问”:“老人家,摘下一串白灿灿的榆钱来买您的美酒,您肯不肯呀?”诗人为凉州早春景物所激动、陶醉其中的心情也就自然流露出来了。倘若没有这样的侧面烘托,诗人的“戏问”就很难让人接受了。再比如汉乐府诗《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诗歌通过其他人对罗敷美貌的倾倒的侧面烘托,把罗敷的美写到了极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的余地。这种写法,往往可以使形象具有空灵感,又使读者参加到形象的创造之中。这样的艺术境界,有时甚至比正面描写的效果还要好。
渲染与烘托属于不同的艺术手法,它们之间是有不同的:渲染是对形象的正面描写,而烘托则是侧面描写;渲染是指从整体大处着手,而烘托一般是对局部的点染;渲染所描摹的意象,与所描写的形象一般有着直接的相关,而烘托所写的意象,往往是与所写形象相关的其他事物,诸如此类。但很多时候,人们在分析渲染与烘托手法时,却常常是“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之间确实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