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他人”不同,这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他者”(the other)与“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说后者表示主体的主导地位,那么,前者就是自我以外的其他东西。故而,“他者”关涉的是某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及主导地位的问题,它经常用于复数形式,极少针对个体。
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以主人与奴隶为例,这两个角色可互为定义,主人需要来自奴隶的确认,他的自我意识的获得要依靠奴隶的存在,没有奴隶,也就无所谓奴隶主,反之亦然。当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奴隶也就不复存在,至多会说他/她活得像个奴隶。以此类推,性别、人种也如是。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对照物的存在,因对照物的存在而对自我有更深的认识。
从哲学层面看,没有他者的存在,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可能清晰。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它赋予主体以意义,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对此,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很拗口地说:“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我们作为另一个人所凝视的目标的存在”,将这句话用大白话翻译出来就是: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其他人对我们的关注。
在心理分析领域,拉康提出类似观点: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是我们与他者的关系的一种作用。他的“镜像理论”将人(主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镜像时期、镜像时期和俄狄浦斯时期。在“前镜像时期”(出生后1-6个月)婴儿对自我的形成之初空无印象,“我”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他者的目光中;“镜像时期”(6-18个月)婴儿在镜中认出自己,这一阶段是主体与本人认同归一的过程,主体正式确立了自己,从意识上形成自我,但那仅仅是主体的萌芽。
主体的真正形成在“俄狄浦斯时期”(1.5岁以后)。“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弑父娶母的故事主角,俗称“俄狄浦斯情结”。拉康认为,由于父亲的介入,导致母亲和孩子强行分离。“父亲”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的是社会秩序和文化表征。当然了,社会秩序和文化表征先于主体(儿童)而存在,可想而知,主体的形成是一个自我不断分裂、不断异化的悲惨过程。在主体确立的过程中,“他者”的存在及对立功不可没,没有他者的眼光、没有他者的比对,主体不可能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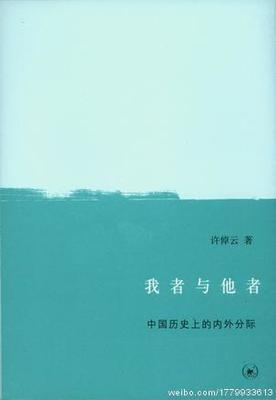
然而,“我”及“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他”及“他们”吗?我们如何了解他者的思想和感情;我们能否肯定它和我们自己的相似;我们能否将其行为作为他们思想和感情的一种可靠的反映来理解呢?答案是相当不肯定的。为此,西方哲学尽可能给它一个明确的地点,从而达到坚持压抑他者的目的。当他者与我们不同,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假设他们的思想、感情与我们自己的不一致,各种主人、统治者、殖民者习惯上就是依赖于这种假设,并据此得出一个恶意的结论:他者的思想和感情不仅是有差别的,还是粗鄙的、低级的。
自我与他者的联系是无法摆脱的,创造群体和个人身份的过程是确定差异并使这种差异具有意义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将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由此而产生形形色色的他者,比如:妇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就一再被认为是偏离了父权制的、异性恋的和白人的社会规范的。也即:将妇女建构为父权制下的他者;将同性恋建构为异性恋的他者 ;将有色人种建构为白种人的他者;甚或,将残疾人排除为他者,这既包括恐惧、害怕、厌恶的态度,也包含过度的保护和屈尊俯就的行为。
当然了,由于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出现,最著名的案例,要数西方将东方民族建构为他者。简单地说,就是从地域上划分自我与他者,将西方以外的中东地区视为他者(遗憾的是,东方学尚未能涉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地区及国家),其中关键的维度是民族身份,比如同处于中东的以色列,大致就不是西人眼中的他者。
在东方学中,西方对东方的观看,是将东方文化与人民当做“异域风物”(foreign)来对待的。在西方所创造的这种话语中,东方既拥有西方所缺少的东西——灵性、异国情调的浪漫化,与此同时又是衰弱的和败坏的。因此,对西方来说,东方既是值得向往的,又是必须被征服和统治的。——无疑,这为帝国主义的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至此,西人笔下的文本及影像图画就与权力及支配的问题联系起来。东方学的要义及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这一内在操作规则,此乃萨义德的贡献所在。
简要地说,为了认识“自我”,需要“他者”的存在。他者处于从属地位,且经常与民族、性别、阶级等维度相联系。在此过程中,涉及话语、知识、权力、支配及统治等问题,故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