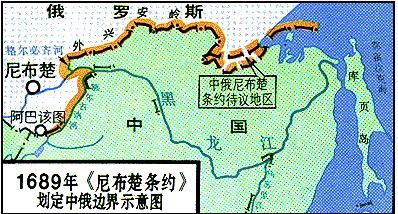中俄现代史上的“红色恐怖”一瞥
读完了《斯大林秘史》和《斯大林肃反秘史》两本书后,脑子里想到许多东西,比如与“红色恐怖”的有关的问题。
《斯大林秘史》一书的副标题是“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剧作家,犹太人,其父是名气极大的剧作家,我们最熟悉的《攻克柏林》就是他父亲写的剧本。尽管他父亲是个迷恋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名气太大,所以却没人敢动他。即使这样,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深怕那天也会与他的许多朋友一样消失在集中营里。他父亲生前对作者说过“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指斯大林——引者)的事”。他父亲于1969年去世,那年作者开始写作此书,于1996年出版。中文版是由李慧生、盛世良和张志强翻译的,新华出版社1997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
《斯大林肃反秘史》的作者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的真名是列夫·费尔德宾。作者曾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1938年7月从他被派驻的西班牙逃亡美国。他根据个人经历和见闻所写的这本书,提供了主要是1938年以前苏联政治清洗浪潮中一些人和事的细节,披露了斯大林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镇压的恐怖行为的若干历史事实。该书稿于斯大林死后不久的1953年6月由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并陆续以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版本印行,成为西方研究苏联的学者所重视的史料之一。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译者是斯仁。
在读这本两书前,我已读过国内苏联史专家戴隆斌写的《斯大林传》,对“大清洗”了解一些。另外我是在网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元贞先生对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的访谈录,祖波夫是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应普京2006年的提议,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这部书由他主编、40多名学者参与写作,书名是《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这部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我通过李元贞先生对祖波夫的访谈录,也获取了一部分关于“红色恐怖”的史实。
去年我还阅读了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代表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总结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即我们国内俗称的“秘密报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路线的大论战之时开始,我们一直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视为一个“修正主义”的报告。但阅读后才知道那是被误导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我以为赫鲁晓夫讲的没有错。当然赫氏的报告对列宁还是依然肯定的。其实,列宁就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笔者会在下文作分析。
我第一次听说“红色恐怖”一词是在1966年9月中下旬,那时“触及人们灵魂”的“文革”已经不是“请客吃饭”了。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学生代表宋彬彬时说了“要武嘛”,强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当时我所在的上海控江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乖孩子”多,所以“运动”还是较温和的。9月下旬的某天,几位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认为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太没有“造反精神”了,要帮我们学校揭开“斗争盖子”。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论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的,心想我们过去只听说过“白色恐怖”,那是指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镇压,怎么还有“红色恐怖”一说呢?记得很清楚,有两个身着黄军装的女学生,人也蛮清秀的,说话声音带着我们上海人听起来很好听的“儿”音。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她们两人给我们演示什么叫“红色恐怖”,命令朱立人校长和其他三四位“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的教师,跪在地上,还解开自己腰上扎着的武装带,抡起了就抽他们,顿时有的人脑袋流血了。这还不算,还让他们一直爬到大操场,边爬还要边唱“鬼见愁”。打那以后,我所在的学校“运动”被发动起来了,一些过去的“小绵羊”也学会“打砸抢”了。
这就使人想到在专制制度下做惯了愚民,就会成为当局的顺民;当“伟人”和顺民们的偶像想利用他们的忠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顺民就是一支能指哪打哪的生力军,这时顺民就变成了暴民。暴民会在一些群体性事件里面,以令人发指的疯狂,宣泄对某些阶层的仇恨、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直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是怎样倡导、阐述“红色恐怖”的理论,并且大力在俄国施行的呢?
按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这部书的说法,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军首领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这部书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党内理论家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资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布哈林的这段话,在《斯大林秘史》第168页上也有,不过译成的中文不太同——“都是为了把人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原材料变成共产主义新人。”
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1917年12月20日,列宁提议组建了一个国家安全机关,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提出“应当找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到这个岗位上去”,于是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主席。在1918年改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打击投机及权力滥用特别委员会”,电影“列宁在1918”就反映了不少当时“契卡”的情况。
1918年2月22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发表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在八条法令中第六条和第八条最为严厉:“(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反抗者枪毙。(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列宁选集》第3卷435、436页)苏维埃政府赋予契卡机关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1918年9月,列宁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给社会制造了极大的恐慌。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到1922年间,契卡的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打击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中指出,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书中记录了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被处死的情况:1918年“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苏维埃政府甚至颁布了《人质令》,要求“凡当地苏维埃知道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都应立即逮捕。应当从资本家和军官中抓相当大量的人质。稍有抵抗举动,即集体枪决”。“《契卡周报》写道:‘许多城市已经大规模地枪毙人质。这是对的。在这种问题上,半途而废最要不得,只会是敌人更凶残’”。(《斯大林秘史》第167、168页)
“红色恐怖”还有一个特点是“有组织的恐怖”。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接见记者时说,“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在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被刺后,暗杀事件成了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据此,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9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红色报》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的鲜血,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布尔什维克党当时贴出的传单,标题就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斯大林秘史》一书的作者写作此书过程中,曾在党务档案馆翻阅了斯大林批注过的书籍,作者发现了两本关于“恐怖”方面的批注。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暴力革命的地方,科巴(即斯大林——引者)都不厌其烦地高兴地注上:对!精辟!辟!是!!”另一本是考茨基的书,书名也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考茨基写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动。”作者说“科巴在旁注为:‘哈哈’”。(《斯大林秘史》第169、170页)“红色恐怖”的理论,现在有学者追朔到了马克思。拉津斯基发现在马克思语录“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的旁边,斯大林加了个批注:注:“注意”,“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斯大林秘史》170页)
列宁的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并把“专政”对象扩大化。我查阅了他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一文,其中有一节“‘完整的组织’和专政”,在那里他指出:“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34页)请注意,在列宁著作中,他一直是不信任农民的,把农民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由于从1919年起,列宁借口国内战争,搞“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除了必要的口粮外,余粮全部没收,农民无权卖粮,于是1921年6月农民起来造反了。列宁的指示是,“应无情镇压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应当搞个示范:1.起码绞死(一定要绞刑,让人看得见)100名顽固不化的富农;2.公布其名单;3.没收其全部粮食;4.点出若干人质,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看得到,受震动……”(《斯大林秘史》190页)最后出动4.5万名士兵,动用了5套装甲列车、18架飞机及喷毒瓦斯,数千名暴动农民被关进了集中营。其实,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已经消灭了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这时说的“富农”主要是勤劳致富的农民。1929年底,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指定莫洛托夫为主席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毙,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斯大林秘史》271页)著名的近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先生说“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由于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引发了特大饥荒。斯大林禁止谈论饥荒,拉津斯基书中估计饿死的人“大约是500万到800万”,1932年8月斯大林亲自起草了“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穗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10年徒刑,民间称之为“五穗法”。
当时对不听话的产业工人也是严厉的镇压的。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列宁命令:“与‘尼古拉’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
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人们把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的捷尔任斯基铜像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发布第9号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强行除掉剥削阶级、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等概念,导致了20—50年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摧毁了公民社会的结构,酿成可怕的社会分裂,造成几千万无辜人民丧生。”这就是俄国人对“红色恐怖“的政治清算,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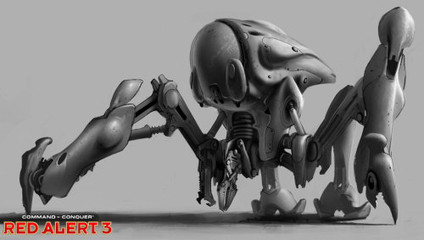
我至今没有看到中共文献上出现过“红色恐怖”的提法。但是毛泽东却说过“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和“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之类的话。我以为与“红色恐怖”这种刺激性的表述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毛泽东不怕乱,喜欢先破后立,大破大立;他还喜欢搞群众运动,人多力量大,以及办“学习班”、“群众专政”这类方式。这非常符合他的革命逻辑,即先“破坏一个旧世界”,再来“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凡是需要发动群众参加时,就会搞“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极左的思维的导向下和在“革命”的名义下,就会对“阶级敌人”大肆贬低、轻蔑,乃至消灭肉体。近年来此类史料不断在媒体上有所披露,以“土改”和“文革”为最典型。
先看几个土改中的例子。土改中有两段时间可以说是“斗争土改”的典型。
第一段是1947年的老区土改。由于刘少奇主持土改时没有下发对剥削和阶级划分的政策标准,变成了由工作队、贫农团“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谁定成地富”,“以致于贫苦农民求财心切,见富即打,一些根据地的村子中25%,甚至35%以上的村民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换句话来说,不少村子中竟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农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财产被瓜分,本人被打或被杀,家属被驱逐出家门,四处流浪和乞讨。山东根据地何以会有10万农民逃亡,原因不外如此。”(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毛泽东曾讲过,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刘少奇讲过更狠的,地主杀我一个,我就杀他二十个。这类强化阶级仇恨的话,虽然是因为你死我活的命运抉择决定的,但对使用暴力绝对是有催化剂作用的。山西省社科院智效民研究员针对晋绥边区的“斗争土改”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晋绥土改中的酷刑》,另一篇是《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都有具体的描述。在第一篇文中他举了几个骇人听闻的例子:一个是永年县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宋被一个老太太突上来用尖刀把耳朵齐根切断,会场上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主持人为县委书记临时电话请示上级,上级批准了枪决,当犯人枪毙后,主持人在现场看到只剩几根骨头了。一个汉子对这位负责同志说,“怎么把肉都刮去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接着捡起骨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吃,也算解恨了”。有个地主刘象坤当地老百姓认为很开明,1947年成了土改斗争对象,斗争会开一半,就被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他的儿子从部队被开除回家,正遇上斗争他父亲,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捅两刀,会后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如果说上面的例子还是对待汉奸和地主,对自己人也有例子。有个区长抗日很积极的,被斗时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在第二篇文章中,说的是有一位对革命做过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叫牛友兰,其儿子叫牛荫冠,1947年土改时已官至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建国后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早在1940年牛友兰就把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1942年在延安还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但在土改运动时,仍然在劫难逃。1947年9月,在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斗争会不好开,突然有个王明友的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是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他儿子牛荫冠拉着,牛荫冠不得不接过去,由于鼻翼下面骨头相当薄,就拉断了,“斗牛大会”后第三天,牛友兰在监禁中绝食而亡。
第二段是1951年的新区土改,又出现一次 “斗争土改”。中央曾一度纠正过1947年的土改的重大过错,土改的暴力化一度基本得到遏制。但由于抗美援朝和准备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原因,首先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中南局管辖地区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主张搞“斗争土改”的意见,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华东、西南、中原等地区。杨奎松先生在《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中列举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例子。如,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被逼自杀;郫县头两个月枪毙了562人,222人以自杀相抗;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全县划地主3760户,其中自杀261人;荣昌县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会上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当场死亡,有的地主恐被斗,拉到会场后用头撞柱而死。广东省1951年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4000人左右,仅东江地区上半年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着1047人,其中镇压了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自杀。中南局仍认为广东省保守,经中央同意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派陶铸来广东进行新一轮的土改,这段时间出现了暴力化,如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吊乳头、坐水牢、点天灯、假枪毙,以及用水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用木棍自胸碾到腹部碾出大便等残酷手段。结果又多划出来一批地主富农,仅恩平县又多划出地主1039户;华南分局报告称2月3日至3月6日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因残酷吊打,有805人自杀;全省这一段土改期间仅自杀的就死了1.7万人。
到底全国土改打杀造成什么后果呢?杨奎松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个说法,“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往论今》第153页)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数是否可信,很值得研究。因为地主富农有多少都是搞不清的数,他是按照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占农村人口的8%来计算的。杨奎松先生就认为管制的人数应是200万的好几倍,还有人认为杀了200万,(见陈沅森《谈土改“杀地主”》)这只能有待史学界进一步考证研究了。笔者也认为,土改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其中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我们为何不能走赎买的道路,像台湾那样进行“和平土改”?我们的“斗争土改”(有人称之为“暴力土改”)是局部性的问题,还是整体性的问题?但,土改过程中暴力手段能够大行其道,甚至以消灭肉体为目的,终究是一种“恐怖”,对此是歌颂呢,还是批判呢,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完全是依不同立场有不同回答了。我想,按照毛泽东“斗争”哲学,他老人家多半是“好”派。他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说过“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景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还有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毛泽东总的思想倾向是不会反对土改中的“过火”现象的:1948年,吴晗到平山请毛主席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主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成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红色恐怖”的序幕,这就是毛泽东自认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笔者也举几个例子。
一是大兴“死人”的事。本人在九十年代中期曾在大兴县工作过六年,期间任过红星区委书记、大兴县人大常委,与老同志闲聊中也听说过“文革”中的“八三一”事件。198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至此开始,乱打、乱杀现象迅速蔓延,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二是湖南道县死人的事。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成员和“黑五类",将所谓的“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要屠杀工人和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从8月l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中,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手段有从刀枪、棒打、绳勒到沉水、火烧、活埋等10种。(章成《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开放》2001年第7期)。
三是广西死人的事。晏乐斌同志是公安部退休干部,曾在1981年参加过中纪委等中央部委组成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他在一篇文章《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中说:1984年1月,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l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晏乐斌还披露了杀人手段骇人听闻,他说:“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他还披露了:l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l岁)跳坑而死。
四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死人的事。在“公安六条”的恶法护航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伤害了几十万人的性命。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1967〕19号),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六条规定中尤以第2条和第4条最为严厉。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第4条将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21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一条,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至于什么是“破坏行为”,如何“严办”,均没有任何解释和政策界限,任由人们随意去理解和执行,在为私设土牢、刑讯逼供、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号召全国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于是“文革”中一场打击面最宽、手段最残酷的一幕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不再是“当权派”,而是普通老百姓了,即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六条》规定的21种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比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陕西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河南新安县将一万多人送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浙江武义县“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江苏高邮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江苏如东县 “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各级革委会揪出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批斗。丁抒先生查阅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60多部县志与大量的历史文献,撰写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文,文中引用了各地打死、致残和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数字,数据翔实。据统计,在“公安六条”发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受审查被斗,50多万人死亡。(参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田园书屋2010年版,第485-513页)这场“红色恐怖”的残酷与祸害远远超过了1966年夏秋时的“红色恐怖”。
我们看到这里,对“红色恐怖”应该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了吧。“紅色恐怖”一词通常是相对于“白色恐怖”而言,按我们过去的理解是:“红色”指暴力革命,“白色”指反革命。“红色恐怖”最早被用于描述法国大革命最后六周的雅各宾恐怖統治。但实际上“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一样,都是反人类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还是有些区别的:第一,“红色恐怖”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的暴政,也就是“文革”中常说的“群众专政”;而“白色恐怖”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的暴政。第二,“红色恐怖”的主体是各种政治组织,如土改中的“贫农会”、“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等,当然也有狂热者和误认为追求社会正义的人,但又得到了组织或当局的鼓励、默许,或公开支持的;而“白色恐怖”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器。第三,参与“红色恐怖”的个人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有的则是从众或取乐心理作祟而去施暴的,道德与心理因素是重要驱动力,主体的罪恶感反而偏弱;而“白色恐怖”的参与者一般都是抱有执行公务或履行公民职责的意识,个人道德与心理因素是次要的。总之,相比起来,“红色恐怖”的欺骗性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人会怀念“文革”的原因之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