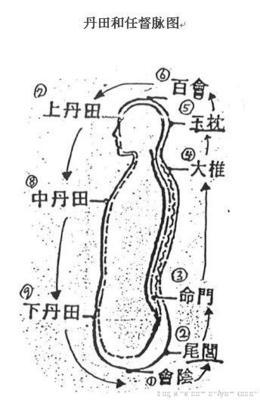回忆中面带桃花的小女孩子象永生的吸血鬼一一永远都长不大。三十、四十几年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打了个黄梁梦样的盹,醒不醒都一样。
我有三个妹妹,各相隔两岁,小时候照相,象不同型号的泥娃娃。人总说再有一个就好了,可以凑成五朵金花,但我们都喜欢格林童话里四姐妹的故事,一个看着另一个出生,大的抱着小的,手牵手一起长大,也有吵闹,小的不讲理,大的就让着小的,转眼还是亲姐妹。
我们是古代云梦泽东边的四小朵永生的桃花,身后是广大而阔气的江汉平原,绿意朦胧的画布,大大的雨点子划出了几条透明的水线。大平原中是活了几千年的汉口,是是非非的市井间悄悄流传着三长两短,一杯茶的时间,九个省已经家喻户晓。
汉口以北有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张公堤,张之洞主持修建的防涝工程,堤外有数条宽大的河和无数的湖泊,地处汉口和孝感之间,是一大片沼泽地,不高的几座山头底下,生活着不知道几世几代的原住湖北人。1957年,政府一声令下,堤外开始围湖垦殖,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涌进来几十万人,我们的父亲也在里面,才16岁。为了跟着兄长跑出来,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的母亲。东西湖就是这一片沼泽地的代名词,三面接水,汉江、府河、汉北河,一面临着张公堤。
几十万人先是围湖筑堤,他们称为“打堤”,意义相当于再造一条张公堤,为一向水患不断的大武汉再上一份保险。很难想象当时的场面,有点疑似秦始皇建长城。筑完了长城,兵士们有的回了原籍,有的留了下来,成了移民,教书,种地,养奶牛,养鱼,种植果树,开车,开小工厂,当官的当官,当兵的当兵,东西湖的百业都等着他们去兴,十大农场一个个建了起来。
我们便是这一批移民的后代。生于斯,长于斯,异乡变成了故乡,但女大十八变,象命一样,我们再次离开,应了父亲以前烦的时候说的话:“整天爸爸爸爸!长大了,一个上新疆,一个去上海,都给我走得远远的!”象他自己和他的祖先,从北到南,一代又一代,漂泊不停,走一站停一代,祖先的青冢永远向着异地的黄昏,世世代代都是过客。
然而隔着几十年的岁月,一想起东西湖,对我来说,这三个字里面装的东西却越来越多,颜色也日益丰艳,味道似乎也愈发的浓烈,比如在网中挣扎的泛青的白鲢,甩着尾巴打苍蝇的黑白花的奶牛,后腿上棕榈色的新鲜牛粪,闻不到臭味,因为还有金黄色的油菜花地,初春时稻田里长着红绿相间的紫云英,浩浩荡荡,它们在回忆中散发着百年陈酿的味道,心醉,也心碎,离人将散的气息弥漫于每一道冒似的美景,鼻息与味蕾之间到处是漫无边际的貌合神离。大平原象一大片墓地,空无一人,又象挤满了人。
夏日,雷雨下的稻叶子愈发的碧绿,小河小沟涨满了水,披着雨衣的小孩子弄张破网在水流最急的地方布下了阵,不知从哪逃跑出来的大鱼们经常不小心给他们网到,有时候也会遇到吓死人的蚂蟥,盯在人腿上不肯松口,但据说怕盐。吓得哭的小孩子跑回来,大人从盐罐子里抓一把盐,洒在蚂蟥身上,揉搓着,一股子血淌出一条小细河,蚂蟥才算掉下来,活不了多久。不过这只是想象,我怕水,也怕蛇,那时候只敢远远地望而却步。
不知道从哪来的故事,多半出自姥姥和妈妈,说遇到蛇不能打,要救,它们是仙,救了它们,在它们逃走之前可以许愿,而且一定能实现。似乎心愿最多只能许三个,不能贪,贪的人往往落空。时间短,心情急,心愿得提前预备。可心愿很多,难得取舍。
后来还真遇到了一条受伤的蛇。家旁边的沥青路上给车轧伤的,痛苦地扭动着,非常吓人,姐妹四人壮着胆子用泥巴糊了伤口,小心用一根树棍子挑起来,胆颤心惊地送到稻田边的小深沟旁边。远远站在那里看着它逃走了,方才想起还没许愿,都后悔死了。
张公堤下是一个好去处,密布着固土的树林,树林外面便是洒满小白圆点的荷塘,小孩子眼中肥绿的一片汪洋,狂风暴雨下最是好看,每张荷叶都象一个自恋的舞女,无数的绿衣女子疯狂的跳着集体舞,呼喊的风声里白色的荷花是王子,不过是陪衬。白荷花不怕狂风暴雨,也丝毫不惧烈日的焦灼,不象晒了整个夏天的小孩子,个个象刚从非洲染了色回来,浑身黑红,只有光着的屁股上有一抹黄种人的烙印。粉红的荷花似乎很少见,成片的白水鱼塘也分外的多,边上的小房子通常破破烂烂,是看鱼人临时的家,门口的小树上倒挂着刚换下的长腰胶鞋,鞋底子上是没洗净的新鲜泥渍。
泥泞是乡下的专利。小时候最怕下雨,因为没有长腰的雨鞋,买不起。那时候水泥地是一种梦想,平房里是红砖铺成的地,下雨天从外面进来,倒也不觉得脏。其实泥土怎么会脏?后来有次坐火车,对面一位是土壤专家,才知道近年来中国的土地污染得可怖。但在我们永生一般的记忆中,只有诗人说过的语词,譬如泥土芬芳。
泥土不但是生存的根本,还是现代孩子们玩剩了不要的橡皮泥,是我们的宝贝,可以捏小人小碗小家具,还可以做游戏。流着鼻涕甚至冒着鼻涕泡的小孩子,指甲里嵌着泥,捏了一只迷你碗,吐一口新鲜的芬芳的口水在里面,叭地一声摔在地上,谁的声音最脆响,泥碗底子裂出的口最大最好看,谁赢。不过到底是口子裂得大算赢还是小算赢,有点想不大起来。可是,穿越几十年的时光,泥巴们成了历史的尘埃,且向谁考证去?!
那时候平安,也平静。路灯依稀,大路上寂寥无人,汽车也少见。烈日下,四姐妹步行着去堤口的大伯父家,一个叫额头湾的地方。热烈的太阳底下,在张公堤上头,我们走一步数一步,几十到几千,总也记不住哪里起了头,走了几百光年,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唱歌唱走了调,小手牵着更小的手,小妹累了要背,于是背上她,走走玩玩,象走了一辈子。
记得那日刚要下堤,突然来了暴雨,可堤上居然没下!四个人站在堤上,一会儿看看雨,一会儿彼此眼对眼,眼神中充满了惊奇。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9岁。隔了整整30年,又象还背着小妹妹在堤上走着,走了一辈子;又仿佛还站在那,看东边日出西边雨。那时候的世界太奇妙,它不懂我,我也不懂它。恍惚间不小心一睁眼,30年的岁月已经溜之大吉,父亲也不在了。还是他够狠,不打招呼便带走了整整一个50年。
回忆的指针每走一秒,爱一样绝望的铃便响一声,流年只有一秒钟。
东西湖一共有28片大湖,这是离我家最近的金银湖,可能也是最大的一片。
百度百科:东西湖
百度百科中的张公堤:
在东西湖的东部,有一条长长的高堤,叫张公堤。她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长23.76公里,顶身高6米,堤顶宽8米,高程31.67-32.20米。张公堤张公堤边的旧碉堡
张公堤原为清光绪31年(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拨款所建,故称张公堤。
当时全堤长度约20公里,工程费白银八十万两。自建堤后,使汉口与东西湖分开,后湖等低地露出水面,可供居住和耕作。后经柏泉藉人刘歆生(人称汉口的地皮大王)筹巨资开发,使汉口市区由此大为扩展。1931年大水后,堤身普遍加高培厚,堤顶高程曾达到29.3米。武汉解放前,国民党军队为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大军,借张公堤为屏障,沿堤筑碉堡、挖战壕,铺设路轨,挖断堤身,使堤防遭到严重破坏。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又组织修复,加固加高。后又进行排泄闸站、防浪墙、块石护坡,子堤加高、防水墙等配套工程。1986年堤顶铺设高级路面。之后,又年年投资维护。特别是1998年武汉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后,市政府又大量投资,使堤顶路面的水泥公路全线贯通,使之成为汉口外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防汛堤变成了交通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武汉城市建设不断向外拓展,张公堤的内外竞成了一个开发的理想的外迁热土和投资的地段。东西湖区抓住这一机遇,沿张公堤兴建了被誉为“楚天第一道”的金山大道,从而拉开了加快发展的序幕。沿张公堤的一线摆下了后湖开发区、海峡两岸高科技园、金桥经济开发区等,一批企业在张公堤沿线的两边落了户。张公堤防汛堤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今已成为一道经济开发的热线,成为展望经济腾飞的一道风景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