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中国骑兵团原创 李梅五
第一部 血战远东
第一章 闯关东
(回忆录)中国骑兵团原创 李梅五
序言
这是一部真实(稍加改编),含有重大历史隐情的回忆录。
山东荣成的李梅五先生,耗时20余年,用毛笔字,将他在俄国伐木、淘金和参加中国骑兵团,以及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等不平凡的经历,记录下来,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一战期间,北洋政府以“以工代兵”的方式,向沙俄派出7万多华工,这些以段祺瑞的淮军精锐和东北义和团俘虏及劳工,组成的中国军团,于1918年4月,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完成大集结。
时任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在亲自率兵收复外蒙古的同时,命张作霖相机行事,令中国军舰封锁外海,准备一举收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
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协约国扶持的高尔察克政府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打的如火如荼,双方都极力拉拢中国军团,列宁通过孙中山,以归还沙皇占领的中国领土为条件,请求中国军团加入苏联红军。
中国军团加入苏联红军后,与高尔察克白匪军的后贝加尔哥萨克骑兵旅(沙皇九支哥萨克旅中最剽悍的一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展开浴血奋战,使白匪军的东线和西线战场,始终无法愈合,后又与苏联红军携手,夺回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
俄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军团的部分将士,有的进入政府部分,有的进入情报机关。李梅五来到哈尔滨,与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联系,以开出租卡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因其它情报员的工作失误,被日本人抓进大牢,受尽磨难,其俄国妻子(犹太人)用黄金贿赂朝鲜籍日本翻译官,得以出狱。
在斯大林清洗驱赶华人时,回到山东荣成老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击毙了旅团长吉川资少将,在一次日本人突然清剿时,为掩护乡亲和区领导,被捕入狱,在公开临刑前夜,借助雷雨,成功越狱。
出狱后,组织和领导了乡里的土改,带领乡亲们支援解放战争。“四清”时,来两人拿走档案,调离领导岗位,下放到农村老家,每月只发给26元的生活费,一直到1984年去世,享年88岁。
第一部血战远东原创 李梅五
第一章 闯关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都卷入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物质匮乏,工矿破产,前方血肉拼杀,后方叫苦连天,参战各国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急需大批劳力。
中国政府积极向协约国阵营靠拢,以收回德国占领的胶州湾。可小日本怕我中华崛起,于1914年9月抢先对德国宣战,出兵占领了青岛。段祺瑞政府及时对德奥宣战,派兵收回德奥两国租界,把租界内的德奥驻军缴了械,不承认德奥两国在满清签定的一切条约,把庚子赔款一笔勾销。
协约国要求中国政府派兵参战,碍于各种原因,中国政府提出“以工代兵”的方式,参加一战,同意协约国在威海、天津,哈尔滨等地招募中国劳工。
1915年春天,英法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威海是李鸿章修建的北洋水师基地。山上斑驳的炮台,诉说着苦难和创伤,黑洞洞的炮口,像圆睁的眼睛,怒视着海上的外国军舰和商船。
辛亥革命后,一些有头脑的中国人,大力兴办民族工业,引进了许多小型机器,像织布机,缝纫机,纺线机等。我当时在烟台资本家周洪武开设的织祙厂做工,织祙机是德国造,大约有80多台,工人全是男的,女人不出来做活。
中国人穿的都是妇女手工缝制的“土祙”,有高腰低腰又肥又大,织祙机织出的祙子合脚,销路很好,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工场管饭,周老板对工人很克刻,经常打骂工人,由于我的技术好,又能吃苦,他就让我到哈尔滨分厂当师傅。
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欧洲招募中国劳工布告,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在国内每月十块大洋,到了国外再补贴十块,那年山东大旱,收成很不好,一块大洋就能买100斤高梁,很诱人。
怀着好奇心,我来到威海,老远看到一大群骡子,被铁丝网圈着,有些人背着青草往门口走。我见过放羊放马的,可从来没见过放骡子的,过去一问,原来是招工局收购的骡子,也要随船运往欧洲,我好生奇怪,难道欧洲没有骡子。
翻过山坡,老远望去,20多间铁皮房被铁丝网围着,门口聚着好多人,外国水兵和中国警察把门。一打听才知道,凡是报名的华工,先到英国福布斯招工局办理登记家庭住址,体检,签约等相关手续,等都合格了就是定招,定招了,才能到劳工营吃饭睡觉,领取衣服,参加队操训练等,每人发给一个有号码的铜箍,套在手腕上。
我在铁丝网外观看,定招的劳工在出操,有些人做体能训练,一阵哨声响后,他们都散开,有的回到铁皮房里,有的跑到铁丝网前,和亲人闲聊。
中午,他们涌到一间房子前排成队,每人拿着一个搪瓷碗,一人两个白馍一碗菜,有的人拿着白馍跑到铁丝网前,和外面的人分着吃。我也饿了,在门口买了个煎饼。
我边吃边想,一走就是离家三年,到欧洲还要漂洋过海,虽然挣钱不少,可前途难料,织祙厂虽然很闷,但好歹能挣上现钱,乱想了一气,决定先回家看看,就起身走回头路。
到家和父母商量,家里不同意我到欧洲。有一发小,非要跟我到东北淘金,我想,哈尔滨也招募劳工到俄国,还不用座船,到哈尔滨再说吧,就这样,我在家里帮着秋收完,就和发小到了烟台。
我这发小叫王凯华,我们一同参加了收复失地的中国骑兵团,在与哥萨克骑兵的恶战中,被劈成两截。
周老板让我再带上两个人,我们从烟台座船启程,船上有不少到东北做生意的山东人,有人见我们年轻力壮,现点大洋让我们跟他走,我揣着周洪武的荐信,相信到哈尔滨,不愁能找到活儿,就没有答应。
到了大连就上了火车,我是第一次座火车,也是第一次看到高大的白俄老毛子,看着他们黄毛蓝眼大鼻子,还有点害怕,更没想到,后来要和他们浴血死拼。
沿途看着大平原和无尽崇山峻岭,觉得新鲜,只是越走越冷,到了哈尔滨,寒风刺骨,找到织祙分厂,围着大铁炉就不想动了。
分厂的老板是个时髦人,头发梳的油光,穿着高腰大马靴,翻毛皮领的大衣,我们吃饭时,过来看两眼,就扬长而去,当时不觉得什么,到后来发生冲突,才知他对我们山东人有成见。
哈尔滨是中国唯一没有城墙的城市,建筑多是外国样式,比中国的房子要大要高。洋人很多,日本人矮朝鲜人高点,中国人普遍是棉裤棉袄,外加棉袍,外国人穿的是厚呢制的大衣,当时觉得什么也新鲜,可就是冬天奇冷,滴水成冰。
我们从山东带的棉裤棉袄,抵挡不住酷寒,只好向老板预支,想置办棉袍和棉鞋,老板说了几句洋文,就让我们找账房。账房先生说:“你们拿到钱跑了怎么办?”,把我们当成了骗子,我当时就来气,拿着周洪武的荐信和他吵了起来,账房说:“从山东来的人,后来都跑到俄国淘金去了,好像这里成了你们的跳板”。
我也不知跳板什么意思,就是要预支些钱。我年轻气盛,吵嚷的声音很大,有人跑过来看,我才发现这里有女工,账房拗不过我,把钱全算在我一个人头上,写着凭条说:“你要是跑了,我们就通知巡捕房”,我也不管哪么多,拿到钱,几个人就出去买棉袍棉鞋。
果然没多久,那两个寿光人,说要到俄国淘金。光棍不挡财路,我就叮嘱他们要常来信联系,没想到过了20多天,回来了一个,病怏怏的躺哪儿就起不来了,我一摸头滚烫,心想不好,抓药请大夫又要花钱,我只好找老板预支,这次有短在人手里,我闷着头也不多说话。
老板随我到宿舍看了看,摇摇头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到账房支钱。我抓药煎药照顾病人耽误了干活,老板脸上跟挂了霜似的。老乡的病越来越糟,我想把他送回山东老家,可老板不同意,说:“你们连车都上不去,把他留在这儿治病已经不错了”。
我一边干活一边照料他,总希望他能早些好起来,可不想病越来越重,最后连药都灌不进去了。这天来了个日本医生,看完摇摇头,没有要钱就走了。
不多时,来了三个穿白大褂的人,进到屋里用被窝一卷,就外抬,我得到消息,跑出来就和他们扯故,老板过来说,他得的是传染病伤寒,要抬走烧掉。我知道这病没救,就央求老板,给买一口棺材吧,老板答应下来。
棺材买来,人已经凉了。我跟在车后,一路为他叫魂,来到乱坟岗,把薄板棺材劈开,架火烧了。我不知怎么向他家人交待,总希望能收到他同乡来信,让他把话传回家里。
后来,我在俄国连那金矿淘金时找到了他,他叫张士训,他参加的是孙富元的步兵团,受伤被俘,被高尔察克白匪军,吊死在铁路线的电杆上。
哈尔滨织祙分厂比烟台的还大,因为正值一战,所有物品都成了军需品,定货很多。我没命地加班干活,只为了能补上窟窿,一天只睡5.6个小时,老板的脸色好看多了。
分厂有女工,哈尔滨女人大脚的多,很爽朗,大声地说笑,而日本女人则不善言谈,只知埋头干活。她们都是日本拓荒团成员,属于最下层的日本人,每年要向军方交很多粮食,和中国的农民差不多,一年辛苦到头也挣不下多少,只好冬天出来做活,不管我们说什么,她们都嘿依嘿依。
朝鲜女工则不同,那时朝鲜已成为日本附属国,她们是“亡国奴”,只要出来做活,够自己化销就成,这两个国家本来就小,男人们不是当兵,就是出来做工做生意,很少在家。
我是师傅,带徒弟不分男女,一个朝鲜姑娘白净小脸,她先笑后说话,一笑眼就眯成缝,因为语言不通,我就连比划带说,我越比划她越笑,旁边的中国女人就嗤嗤地笑我,我不好意思,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只是很想和她亲近。
我哪发小对我挤眉弄眼,他说怕我找个外国媳妇,回到家乡会惹人们说闲话。后来,我真的找了一个洋媳妇(俄国犹太人)她很贤慧大方,俄国内战结束后,我们在莫斯科成婚。
(到俄国的山东人,有些就找了洋媳妇回家,受到当地人的围观指点,他们就举家迁到新疆,成为俄罗斯民族成员。)
到年底支薪水哪天,账房让我到老板哪里,我一听就知道没好果子吃,果真是里算外算,我反到欠老板钱了,一气之下,拽上发小就打铺盖准备回家,可连路费都凑不够。我就想起招工棚给的十块大洋,我想,无论如何要让他回去,这儿不能呆了,又冷又挣不上钱,日本人白俄和当地的匪霸都欺负中国人,说不定那天就要出事。
可这样走又不甘心,就找老板去理论,老板想不到我要辞职,因为我技术好,干活很卖力,老板就答应给我点补助,来年就加薪,总算争回一口气,可我还是不想干下去了,领着发小来到街头,转来转去舍不得化钱,买了两个大“咧巴”(面包)和“卜留克”(咸菜头),然后来到招工报名处。
我在门口踌躇很久,想来今年就没给家里挣多少钱,这一去白俄,三年五载是回不了家了,没法尽孝心,心里很酸楚,发小也想跟我到俄国,我眼一瞪,他含着眼泪不说话。
我不知说什么好,他看看我,我看看他,这时,从大棚里出来个人,嘻笑着往里拉我俩,我心一横进到里面,登记上领到十块大洋,出门交给王凯华,重重说一句:"别把钱丢了",扭头回到大棚。
沙俄太缺劳力了,只要登记上就给钱给吃喝,一切手续全在大棚里办,进去就不让出来,我座在哪儿闭上眼睛,想来我的命就值十块大洋,从15岁出来做活,到如今一无是处,没攒下钱也没娶上媳妇,还落个家里掂记,这一去白俄生死未卜,穷人命苦怎么折腾也是穷命,胡思乱想了一气,心一横爱咋咋地。
看那边人们围成个圈,凑过去一看是在耍纸牌。座庄的人,眼珠乱转,牙总是咬着,到输赢关头,耳根都抽搐,旁边有人吆五喝六,一个个眼睛瞪的大大,大冬天有人还出汗。
(座庄的是安徽人,叫霍世雄,是任辅臣团的营长,在攻占托博尔河铁路大桥战斗中,全营阵亡。)
中国人到哪儿都有赌局,天塌地陷都不管,常言十赌九诈,我不稀罕这骗钱的玩意,就起身走走转转。
这是一大间木制板房,两排大通炕,靰鞡草上面辅着破旧地毯,两人一床军用毛毯,不少人在睡觉,地上大铁盆架着胳膊粗的松木,火焰直冲顶棚,棚顶有腿粗的烟筒吸烟。
我走到门外看,也和威海劳工营一样,10多间大木屋被铁丝网围着,地上的雪都被踩平了,看来,这么冷的天还要出操和进行体能训练。
只见从栅栏门进来五六个人,都穿着中间系扣的棉衣,走路动作都一样,脸上冷嗖嗖的有煞气,像匪又不像匪,他们登记时我凑近,听口音是山东南边淮河一带人,我心想,山东天津都有招募处,何苦大老远跑到东北来应招,他们登记完把大洋交给一个人,四下散开睡觉去了。
快到中午时,又来了八个人,领头的盘着又黑又粗的辫子,大大咧咧地登记完,把钱揣怀里,就凑进赌局圈。不一会有人用车推来两大筐白馍和一桶菜和开水,车上有几大垛搪瓷圆底的碗,人们纷纷过来抢碗吃饭。
吃完午饭正眯着,就听得外面有哨声响,中国警察就大声吆喝着出操,中午太阳足也暖和些,我们排成队列,一个外国小老头,戴着高高的帽子,吹哨子指挥走步。
我从来没参加过队列训练,像逛街走着,我们后面全是新来的,都没有练过队操,这么多人乱腾腾地走,一会踩了鞋,一会撞到别人身上,小老头过来,哇啦哇啦地就用马鞭抽,抽在背上,隔着棉衣还生痛。
有人告诉我们两边看齐了走,一会我们就会听哨声走队列了,走了一大气就跑,开始慢后来快,滑倒一个摔一片,跑的慢的就挨抽,滑倒不起来的也抽,累的我们呼呼真喘白气,有的大口大口的吐痰,这一跑也觉得胸口畅快多了。
这天来了几个剃头匠,人们议价纷纷,都说要出国了,要发大衣了。我挤到前面排队把头剃光,好好地洗了洗脸,洗出一盆黑水,大棚里架着明火,烟熏火燎的几天也不洗个脸。
中国警察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核对姓名籍贯年龄。第三天又点名,核实了就发给打有号码的铜条和一张布制的牌,上面是用汉字和俄文写的姓名籍贯,都填写好营连排班。
劳工也按军队编制,都让把布牌缝在衣服的左胸前。第二又来了个照像的,正面是把铜条放在下巴照一张,侧面照一张,说是给办理护照,然后让把铜条弯成箍套在手腕上,中午吃的面包。
下午50个人排成一队去洗澡,洗头洗脸洗屁股全在大池子里,洗完后每人发一件俄式衬衫和睡裤(秋裤),出去时,我们的棉袄棉裤全用药水蒸过,又用高温烘干,为的是消灭虱子,那时天冷都穿着衣服睡觉,虱子很多,痒的不行,就脱下在火上边烤边抖,穿上衣服排队打预防针。
一个很漂亮的俄罗斯女护士给注射,我们都是头一次近距离看洋女人。她黄头发戴口罩,眼睛是蓝色的,眼睫毛很长,有的人直勾勾地看她,她顶友善,也不生气,推完针笑笑说,好了,又进一间屋子,有个俄国大夫用听诊器听几下胸部,就挥挥手,里间是个大夫检查生殖器,看是否有花柳病。
中国人得花柳病的少,日本人多,尤其是日本军人,他们乱嫖乱宿,互相传染,具说差点拖垮关东军,后来日本军方发明了避孕套才好些。
回到大棚,每人发一件俄式呢制大衣和毛里的皮棉鞋,穿上顶气派。我舍不得穿,就叠好放着,第二天,发瓷缸牙刷毛巾背包皮带等物件,一人给了10块大洋。有个人生拉硬拽地要我参赌,我说什么也不去,差点打起来,警察过来给了他一棒子。
(他叫章富林,当过列宁卫队战士,参加过红场阅兵,“大清洗”时,被流放到常年是零下50度的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他侥幸活了下来,参加了二战,后定居莫斯科。)
人们也不知从哪儿得知劳工营发钱了,铁丝网外面的人多了起来,有送人的,有兜售零食小家什的,也有收购棉袍棉鞋狗皮帽子的,有的人把退下棉袍棉鞋就卖了。
我没有卖,因为我的棉袍是新的,铁丝网里外很热闹,我没事做就瞎转悠,为的是多看两眼大姑娘小媳妇,到了国外可就看不到中国女人了,心想,要是哪个朝鲜姑娘送送我多好。
见有个小脚老太举着两颗鸡蛋晃悠,说是换点钱给孩子扯布做新衣裳,是啊,快过年了,年就是给孩子过的,没新衣裳多别扭,我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一咬牙买了一块大洋的熟鸡蛋,老太从怀里掏出10颗热乎的给我,又从筐里拿了十颗冻的,还一个劲地谢我。
我剥皮吃着吃着笑了起来,女人做月子时才大吃鸡蛋,我这是吃哪家子的鸡蛋。山东有喜事是送鸡蛋,满月喜寿生子都送鸡蛋,也有送白馍的,我一口气把热的全吃了,心里踏实许多,也许是鸡蛋让我想起了家乡,那时头痛闹个病了什么,俺娘就给煮两颗鸡蛋,吃了就好,可能得的是馋病。
第二天下午,我们2000多人都穿着新大衣,抱着个大面包,集中在火车站。这么冷的天,还有人敲锣打鼓地送我们,很是热闹。
沙俄正在开发远东,急需壮工,他们不要印度贱民和南亚人,只要中国人。从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初就招,已经招了20多年,到后来越来越难招募,他们就利用中国人喜欢热闹爱面子的特点,大张旗鼓地欢送中国劳工。
车站上人挤成团,很多人举着小旗子,还有个什么长给我们讲话,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之乡,到了国外要发扬什么什么传统,不许偷抢一大堆,送亲的出国的乱成一团,很多人把大洋交给家人,我和更多的劳工在哈尔滨没有亲人,就默默地看着他们。
老远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东张西望地找人,仔细一看是王凯华,我赶紧向他招手,他带着几个人跑过来,全是织祙厂的工友,还有两个中国女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山东,他说不想回,我把钱全给了他,托他捎回家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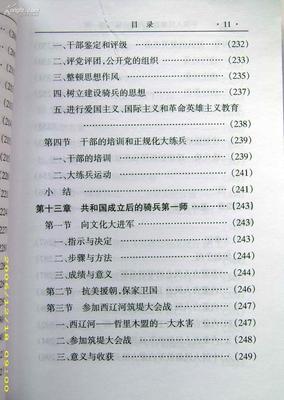
和他们说了会话,不由想起朝鲜籍姑娘,想问又不敢问,一个女人看出我的心思,告诉我说,我走后,她就辞职不干了,我闷了一小会,又和他们说笑起来。
我问,老板让你们来嘛,有人说,是俄国人花钱雇他们来的,一人一块大洋,我心想,这钱挣的容易,怪不得那么多人来送我们。
夕阳西下,人们排队上车,我不停地向他们挥手火车,笛声长鸣,一列满载希望和热血的火车,缓缓开出哈尔滨车站。命运的手,似乎扼住火车的呼吸,显得哪么沉重,气笛声声,似乎向莽莽林海,诉说不屈。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