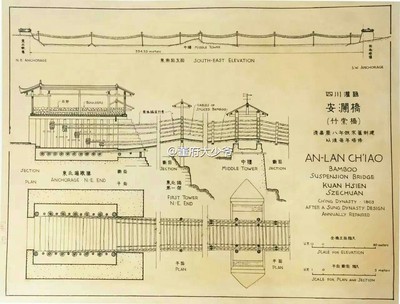北总布胡同的哀思
徽因女士:
今天清晨,京城雪花飘零。
我站在北总布胡同,飘零为瓦砾的您的故居面前,手捧从诫先生编辑的您的文集,念下您的诗行:
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
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
或流云一朵,在澄蓝天,
和大地再没有些牵连。
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志,
去触遇没着落的怅惘;
在黄昏,夜半,蹑着脚走,
全是空虚,再莫有温柔;
忘掉曾有这世界;有你;
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
这些个泪点里的情绪。
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
痕迹,你也要忘掉了我
曾经在这世界里活过。
此刻,我的心,正如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的落叶。
又是那么内疚与惭愧。
我要说一声:对不起啊!徽因女士!思成先生!
对不起啊!!!
思成先生:
那是在1930年秋季,您把家从沈阳搬到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
初为人母的徽因女士不胜东北天寒,患肺病,竟成终生之疾。
把家安顿下来,您又匆匆返回。在东北大学,有您无法离舍的三尺讲台,和莘莘学子——“那快要成年的兄弟”。
我还记得在北总布胡同的这个院落里,您写给东北大学第一班毕业生的信。
先生有言曰: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繁杂,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所以你们负有宣传的使命,对于社会有指导的义务,为你们的事业,先要为自己开路,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你们的责任是何等重要,你们的前程是何等的远大!林先生与我两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先生出生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那年,知事时起,就生怕中国被人瓜分,认定“那是一种不堪设想的前景”。
“我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且是狂热地爱我的祖国。”先生晚年,被打成“牛鬼蛇神”,被逼交代“爱国心”,写下的检讨,头一句话如此。
还记得那是在1997年冬日,在清华大学,青灯之下,展开这一册黄卷,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眸。
先生有言曰:
我之所以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当时自己确实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我的“一片爱国心”。我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上建筑史时,教授问起我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我难为情地回答:中国还没有建筑史。以后我就常想,这工作我应该去做。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民族、国家,怎能对自己的古建筑一无所知?怎能没有一部建筑史呢?
1928年,先生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心中凄凉,尽在笔端——
我在沈阳东北大学教书,多次因工程业务取道长春到吉林。平时在沈阳“南满铁道附属地”看到称王称霸的日本人,就已经叫人够气愤的了。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车站上的日本警察,手执赶大车的长鞭,监视排队买票上车的广大中国乘客,只要一个人站歪了一点,突然一皮鞭就从远处飞来。……我感到,东北还未沦亡,但我们中国人已在过着“亡国奴”的日子了。
日本人的长鞭,力从何来?先生自知。
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大地,日俄开战。事后,俄国人在写给日本人的报告中,以轻蔑之语称:“我们在战争中虽然败给了日本,但与欧美文化相比极为落后的日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与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后来,看到日本人费力经营的“满铁附属地”,俄国人服膺,认识到“把日本人与中国人等同视之是我们的认识不足”,遂承认对方为具有殖民统治能力的对等关系伙伴。
近代以来,伴随列强坚船利炮侵入中华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达尔文的声音。什么叫“具有殖民统治能力”?就是说你这一族,没有进化,只配被具有统治能力的进化民族殖民!
我泱泱中华,拥有如此灿烂文明的一国,竟遭如此屈辱!先生,您不得不退回北平。可就在北总布胡同刚刚安歇下来,“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人向前来调查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专员大作宣传,称中国内政纷乱,缺乏统治能力,几不成国。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套——你这个民族,就是需要由日本人来殖民!这也成为他们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先生,您怎么咽得下这一口气?可以想象,当年在北总布胡同,踱步于这处院落,您的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又是怎样的急迫?您誓言要活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来。在这里,如此难得的苟且平静的日子里,您的生命爆发出何等光彩!
此刻,我的心,怀着对您无尽的思念,又如此沉沉地失落。
我要说一声:对不起啊!思成先生!徽因女士!
对不起啊!!!
徽因女士:
在北总布胡同的病榻上,最让您不能安心的,与思成先生的一样,就是——中国之建筑无史!
打开弗莱彻《比较建筑史》,那上面分明写道:中国之建筑,“迄无特殊之演变与发展可言”,只配被列入“先史时代之建筑”。仍是在说:你这一族,始终没有进化啊!
这样的建筑史,是何等的傲慢,又是何等的无知!
您28岁时,在北总布胡同的书桌上,为中国建筑大笔直书——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它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您在北平,向西方人宣讲中国建筑,该是何等自豪!深爱着您的志摩先生,为听这一讲,急切地搭乘中国航空公司邮机北上,竟撞死在济南党家庄开山!
他是为爱而死!为中华文化之爱而死!!
思成先生到济南,向志摩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转过身来,再赴深山老林,踏上探索中华建筑的漫漫征途。徽因女士,您体质虽弱,却不让须眉,一次次伴着思成先生风餐露宿,用您的话来说,这叫“吃尘沙”!
您那不堪负重的双肺,又盛得了多少尘沙?您竟为此永远失去了健康,如此过早地离世!
此刻,我的心,郁积着无限的哀思,那正是没着落的怅惘!
对不起啊!徽因女士!思成先生!
对不起啊!!!
思成先生:
您一次次从这条胡同出发,在那处处烽火、车马难安的中国,如此艰难地朝着一个伟大文明的深处行进,心中是那般欣喜。
走出这条胡同,您到东四牌楼搭车远行,如此调皮地叙述:“一直等到七点,车才来到,那时微冷的六月阳光,已发出迫人的热焰。汽车站在猪市当中——北平全市每日所用的猪,都从那里分发出来——所以我们在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在那短短六年的时光里,您发现了独乐寺、佛宫寺木塔、赵州桥……您和徽因女士,终于找到了那处伟大的唐构——佛光寺!
那些年,您和刘敦桢先生,还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挑战着生命的极限。在那么艰难的时刻,您们负重前行,脚步覆盖如此辽阔的国土,一次次报来令人振奋的消息!
中国人终于能够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建筑史,能够在抗战与内战之际,为作战方开列长长的文化遗产名录,要求他们誓守保存中华文化的底线!
因为您们的工作,弗莱彻《比较建筑史》改写,庄严地补上中华建筑的篇章,成为真正的不朽。这才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啊!
感谢您们啊!思成先生!徽因女士!
感谢您们啊!中国营造学社的先辈们!
徽因女士、思成先生:
莫宗江先生在世时,给我讲过当年您们发现佛光寺时的欣狂:把所有的罐头打开,摆在辉煌的大殿前,吃它个欢天喜地!
可是,噩耗传来——“七七事变”爆发!
您们匆忙赶回北平。在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徽因女士,您给女儿再冰寄去一信: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可是,北平沦陷了!
您们毫不犹豫地拾起行囊,携儿带母,离开北总布胡同,奔向后方,共赴国难。
在长沙,日寇的飞机炸毁了您们的寓所,全家人险些罹难;在晃县,徽因女士肺病复发;在昆明,思成先生关节炎发作,肌肉痉挛,一卧就是半年。
费正清先生希望您们到美国避难,思成先生复信: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2010年秋,我在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分享您们的故事,念下思成先生的这番话语,竟是不能自持。
我还记得后来您们流亡至长江边上的李庄,双双病倒,思成先生勉强以花瓶支撑下腭写作。费正清先生赶来探望,留下如此记载:
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我还记得从诫先生回忆起母亲预备投江殉国之时,幼小心灵承受的震动:
有一次我同母亲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直逼重庆的危局,我曾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我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这个回答,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因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我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徽因女士,就是在那样的苦境之中,您被医生宣布只能再享五年之寿。
而您视死如归,依然奋笔疾书,写就《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把目光锁定在美国与英国的低租金住宅建设上,细研金融政策、资本经营模式、不动产税调节机制,以及标准化设计、快速施工等低成本房屋构造技术,深信“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多数国家都对于人民个别或集体的住的问题极端重视,认为它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眼前必须是个建设的时代,这时代并且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造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也是在那样的苦境之中,思成先生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再把目光投向战后中国的重建,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的社会理想。
您们的生命是如此绚烂,您们的爱是如此炽热!
您们是那么盼着那一个新中国的到来,不惜为此赴汤蹈火!
您们是中华民族最最宝贝的儿女!!!
拆毁北总布胡同这处故居的人们:
你们知道你们的肩上应该承担怎样的道义责任吗?
1948年12月,北平围城之际,人民解放军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派专员到清华园,请思成先生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为枪炮长眼,宁可牺牲战士,也要保文物不失。
后来,思成先生一次次回忆起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的场景。
1957年,思成先生写道:
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来了一位干部。他说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让我在地图上注明,并略略讲讲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1959年,思成先生又这样追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华大学获得了解放。解放军的自觉的纪律,干部的朴实,和蔼的态度和作风,给了我深刻印象。出乎意外的是,党十分尊重我的一点知识和技术。北京城解放以前,来咨询我关于城内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更深深感动了我。……我感到共产党挺能够“礼贤下士”,我也就怀着“士为知已者用”的心情,“以国士报之”。
你们怎能挥舞如此冰冷的铁器,将这处故居毁掉,还把木料卖掉,说这是“维修性拆除”?
我要告诉你们,正是出自那一份道义责任,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停止大拆大建;
正是出自那一份道义责任,2009年,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作出那神圣的决定,依法将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决心只要还有一丝历史信息留存,就要做最完全的保护!
你们分明是在挑战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啊!
但是,你们不会成功,因为我们这一族,拥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永远是把文化放在最高的位置,它永远不会被人踩在脚下!
这个国家正朝着文化复兴的方向!尽管还有艰难坎坷,但我们会一如既往,本能地、一代人又一代人地——付出最大的牺牲!
徽因女士、思成先生,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您们若在天有灵,真不知该如何打量北总布胡同,我眼前的一切?
但请您们放心,我和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失去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永远不会失去对人类文明的热爱!
我和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忘掉您们曾经在这世界里活过!!您们永远不会落花似的落尽、与这片土地再没有些牵连!!
念下那泪煞乡愁的诗行,我骑车西进——
故宫还在!!!
王军
2012年1月30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