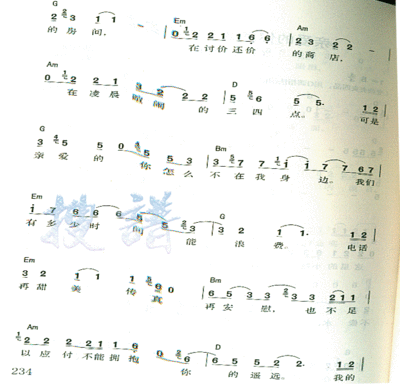(二)迷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国胜利而告终。此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方天翼的独立团也一样。活下来的人终于带着死去的人的心愿见证了这一刻,中国人用不屈的灵魂洒过血泪的土地是不容无理残暴的侵略者侵犯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土匪”、“强盗”势必会落败。
独立团经过战争的洗礼后逐渐强大,本应与同志们一同享受这份喜悦的方天翼却选择离开。十四年了,他和日本侵略者斗了整整十四年,他累了。既然日本都已投降,他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是时候回去陪俞梅了。方天翼向上级打了报告,给敬琳、富贵留下一封信,在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欣喜中的时候,悄悄离开,只身回到句容。
清晨,鸟儿在山中欢歌。那声音清脆悦耳,此起彼伏。阳光洒下来,穿过树叶缝隙,暖暖地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微风轻拂,叶子随鸟儿的歌声舞蹈。俞梅就在这片宁静祥和的土地上安静地睡着。
方天翼在这儿盖了一间木屋,又置了些田地,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周而复始,不厌不倦。有时,他会去镇里买些酒回来喝。他总托人替他买JOHNNIE WALKER,但是小镇地方偏僻,甚少买得到如此名贵的洋酒。每隔几个月,他都要去天目山看李长城政委,柱子,根彪等兄弟们,带上几瓶他攒起来的好酒,和他们痛饮几日。
夕阳似火,方天翼又提着一瓶酒从小木屋里走出来,去陪俞梅说话。他坐在俞梅的墓前,伸出修长的手指轻抚冰冷的石碑,缓缓滑过深深刻在碑上也深深烙在他心里的那几个字——爱妻俞梅,浅笑着。
“梅,有我陪你,是不是觉得没那么闷了?
“七年了,我离开你整整七年。你知道吗,这七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多的我都无法得到喘息的机会。松下健这个孙子被我送下了地狱,那次我受了很重的伤,如果没有成哥嫂子他们可能我那时就死了。你一定会怨我,怨我那么冲动,怨我只会用恨来衡量这个世界。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替你报仇。其实我是后悔,自责。我曾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在,容不得任何人伤害你,但到最后我却食言了。杀松下健那天晚上曾有过那么一瞬我几乎想要放弃自己,我受伤倒地,鲜血止不住地流,我觉得你就在我眼前,我想和你一起走。可是看到兄弟们奋力救我,我醒悟了,我要活着,从我对你说‘给我活着’,你回答‘你也是’的时候我就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我要为你好好活着,替你做你还没来得及做的事,等着看到你想看到的那一天。我对成哥说,我的感情就是我的信仰,你离开我并不代表我们的感情消逝,它一直都在,我要为那个信仰活下去,那个信仰里有你告诉我的‘和平’,也有你我的感情。
“你还别说,这心哪,痛到麻木,身上的伤口就感觉不到疼了。那次嫂子为我取子弹,没有麻药,我还真就那么硬生生地挺过来了。后来成哥为了救嫂子也牺牲了,他和你都是好样的,他是我敬仰的哥哥。我和婷婷、洪哥加入了新四军,富贵,根彪,柱子还有王文渊也跟着我投了新四军。我们团可打了好几场胜仗哪!我们成立了突击队,富贵给起了名字,叫黑狐突击队,这名头的意思非常之对呀,日本人那会儿一听到黑狐突击队可是要打个寒颤的。重兵围困之际我们都能炸了他们的虹桥机场,这一下子弄的,特漂亮。呵呵,我见过能吹的,还真没见过比我还能吹的。
“嫂子的身份被日本特务识破,我和斌哥去救她的过程中遭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头目坂田之助的暗算。多亏山口一男的帮忙我们才能够逃出来,可是山口还有野狼陈局长都没能活下来。陈局长和你一样,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山口一男对嫂子的情意我看在眼里,我大概能懂他为了嫂子能够放弃自己军人身份的心。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热爱他的国家,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维护一个军人的尊严,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实现他的忠诚。但是面对嫂子,他选择背叛自己。恐怕我都做不到他这点。他不是个称职的军人,但是他绝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这部队要是出名,走哪都得有人惦记着,你说是吧。浅田正雄个老匹夫集结大股日军围剿我们团,那场仗打得惨啊,我至今都记得我救回富贵时那小城里的场面,黑狐突击队几乎全军覆没,李政委,哦,就是你以前的上级李长城,还有根彪,柱子,胡俊,还有好多同志,都没了。若不是处座派沈晗救我,可能全团都……处座对我不止有知遇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可惜他与我立场已不同,这份恩情教我如何报答啊。
“我重建黑狐突击队,跑到上海找浅田和坂田算账,多亏王文渊背着我事先找了人接应,否则我们突击队损失就重了。嘿,我就说我肯定死不在日本人手里,王文渊这小子,别看他平时挺老实,心眼儿可真没少长。哎,那是陪我一路走来的好兄弟啊。民国三十年,国军以数倍于我的军队围困新四军,王文渊替我带队掩护独立团突围,我带着突围后活下来的人回到根据地,他没回来。
“梅,我还结识了一位江湖奇男子,上官敬举。他本来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为了抗击日寇,他变卖家产占山当了什么‘湖匪’,挺有意思的,我和他很投缘啊,一见如故,只可惜这样讲情义的大哥被日本人害死了。做弟弟的得对得起大哥,所以我和富贵替他照顾着他妹妹敬琳。我初次见她觉得她挺有胆量的,虽然她有些任性,好强,但是人很善良。这几年她要比我初识她时成熟很多。婷婷也成长了,懂事了,和你认识她那时可完全不一样了。她现在也懂得什么是组织,什么是纪律,那些个大小姐脾气统统不见了。近来她的情况我也不知道,都是保密什么的,也不让问,有时候我还真特着急。不过我妹妹嘛,不是我吹,她功夫那么好肯定很安全,这个我放心。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护送新四军伤员的女兵,她叫刘佳颖,人长得秀气。为了保护伤员,救被日军逼问残害的老百姓,也为给我的救援争取时间,她用身体堵日本人的枪口。看到她,我想到你。你们都一样,为救别人不惜牺牲自己。你们都是坚强的人,都是为信念不顾一切的人。
“还记得苏浙别动队吗,你手下的一个兵胡德荣现在可是我们独立团的参谋长啦,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夸夸你,也夸夸我自己。
“梅,战争结束了。我知道你一直等着这一天,现在它终于来了,你一定很高兴。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没有战争,那该有多好。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战争,我们能相守到老。我们会有我们的小家庭,有我们的孩子。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我嘛,儿子女儿都喜欢。女儿就像你,美丽大方,儿子就像我,胆大心细嘛。”
方天翼把酒洒在地上,自己也喝了一口,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把儿女都培养成才,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再看着我们的孙子出生,长大。到那时白发苍苍的我和你一起到处逛逛,我搀着你走,去我们最初相识的那家餐厅,去我出狱后你来接我的那个火车站,去你第一次为我面条的那林子里的茅屋……呵呵你看我脑子怎么不够使了?如果没有战争,哪有这些地方,你我有怎么能相识?”
一场战争让一对有情人在乱世烽火中相遇,却又让生死关头相约白首的他们相离。人间,有情;战火,无情。
转眼,已是第二年春天了,桃花早爬上树梢,梨花如片片白雪,被风从树枝上剥落,飞舞着落到地上,躺在泥土里。方天翼头顶一个破了边的大草帽,扛着锄头,从山中归来,俨然一副山野农夫模样。半年多的平静生活洗尽他身上的狂躁和戾气,但是他的眼神依旧明亮,坚定。
方天翼走到木屋前,把锄头摆到一边,摘下帽子扇风。脸颊上的汗珠滑落,滴到他的肩上,在洗旧的衣衫上晕出一朵小花来。当他转身准备去看俞梅时,他忽然立住,被俞梅墓前的景象惊得呆住了——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拎着银白色手提箱的男子正端正地站在墓碑前。怎么会有人找到这儿来?但是这背影……方天翼向后退了两步,伸手摸出袖口里的飞刀,眯起眼睛,做好比那人先出手的准备。
那男子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嘴角微微一扬,弯下腰,朝俞梅的墓深鞠一躬,笑着说:“我以为这几年你会把功夫荒废了,没想到反应还是这么灵敏。”这说话的声音?斌哥!方天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那男子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他,伸出双臂,方天翼扔下手中飞镖,走上前去,和那男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哥……”方天翼眼含热泪。
罗斌拍拍方天翼的后背:“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没出息。”
“在哥你面前,我不就是个孩子吗。”
兄弟之间,无需太多表达感情的话,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让对方感知,你是我兄弟。
方天翼和罗斌在俞梅的墓前席地而坐。夕阳温柔地落在他们身上,暖暖的。
“我这样守着她,挺好。”方天翼用黑色手帕仔细擦拭俞梅留下的手枪。那枪身光泽不减当年,精致如新。
“她值得你爱。”罗斌看到墓碑上“爱妻”两字,感慨道。
方天翼笑了笑,抬头看天。火红的云一层一层叠着,仿佛俞梅正躲在那层层红云之中,朝他微笑。
“哥,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去哪儿可谁都没告诉啊?”方天翼回过头来疑惑地问。
罗斌把手提箱拽到怀里,边开边说:“哎呀,我还不了解你?抗战胜利你玩失踪,不是到这儿找俞梅来了你还能去哪?”
“哈,要不说你是我哥呢,佩服佩服。”方天翼调皮地向罗斌拱手。
“让你佩服的事儿还多着呢。”罗斌打开箱子,拿出两瓶JOHNNIE WALKER,往天翼手中一递,“给。”
方天翼顿时两眼放光,迅速把酒接过来:“哥,你太神了。我最近就缺这个。你说这穷乡僻壤的,买不到啊,可把我想坏了。”
“就你稀罕这洋玩意儿。还有,正宗天津麻花。”罗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袋麻花来,塞到方天翼怀里。
方天翼启开瓶塞把酒往嘴里猛灌一口,说:“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麻花儿这玩意儿我可是多少年没见过了。”
“要不怎么说我是你哥呢。”兄弟俩相视一笑。天边夕阳更像燃起的伙,熊熊不灭。
“你来找我,不只是为了叙旧吧。”方天翼问。
“这半年多你都在山里,外面的事儿你可能不知道,”罗斌把酒瓶放在地上,“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恐怕免不了了。”
方天翼抚摸着俞梅的墓碑,说:“梅说过,她不想打。”
“我们是很有诚意地找他们谈判,可是他们敷衍了事,暗藏祸心,咱也没办法。”罗斌无奈地叹了口气,继续说:“戴汉清死了。”
方天翼猛一抬头,惊讶地问:“你说什么?处座他……”
“嗯,”罗斌点点头,“飞机失事死的,就前几天的事儿。老蒋现正在各地大肆举办悼念活动,以祭奠他这位‘党国忠臣良将’。组织上想……”
“等等,”方天翼打断了他的话,“处座对我恩重如山,我一定会去吊唁。但是你们那些什么任务,我不感兴趣。”
“天翼……”
“哥,自家人算计自家人的事儿,我做不出来,别为难我。”方天翼拿起酒喝了一口。
“天翼呀,”罗斌语重心长地说,“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个希望你能明白,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蓄意挑起内战的不是我们。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或许几个月前,你可以放手不管,但是现在形势变了,内战一触即发。国民党里有人只想争权夺势,根本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如果天下落在压榨老百姓的人手里,那穷苦人又没能翻得了身不是?你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俞梅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方天翼沉默了。他只想活得简单,活得明白。他不想卷入这些复杂的政治纷争。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卷进来,因为他有了信仰。局势变幻莫测,他还在为信仰奋斗的路上,不能停下来。
“哥相信你能想明白。”罗斌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张被折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方天翼,“这个,你应该会感兴趣。”
方天翼拿着报纸,满脸疑惑。
“看头版。”
方天翼怀疑地看了罗斌一眼,打开了报纸。他把视线移到报纸头版上,猛然一惊。一张国民政府官员聚集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头条新闻下方。照片拍的是重庆悼念活动的场面。尽管报上的某些部分都已模糊不清,方天翼还是能够认得出那张夹杂在众军官之中的熟悉的面孔。照片里德那个神情悲痛的男人在某些人看来或许不起眼,但却令方天翼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去重庆?”罗斌问。
“这就动身。”
汽笛声令本就喧闹的重庆火车站更显嘈杂。方天翼敏捷地跳下火车,身上深黑色长衫的衣角随他灵敏的动作掠起。他脚上质地柔软的灰色布鞋和僵硬的地面轻轻贴合有轻轻分开,几乎让人听不出半分脚步声响。他挤在人潮之中,毫不起眼。鼻梁上架起的木框眼镜装扮得他更像一个老实的教书先生了。他手提木箱,脚步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朝火车站外走去。
路过一个站台,方天翼忽地顿住脚步。他抬头看那块列车时刻表,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曾经,也是在火车站,也是他下火车,也是站在列车时刻表下面,有一个人站在站台前微笑着等他。他放下手中行李箱,看着那个人温暖的面庞,握住她伸出的右手,望着她如一汪泉般清澈的眼睛,告知她好久不见,很高兴再次见到她。方天翼仿佛看见,她就站在来往人群中,站在站台的角落里,等着他,对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方天翼的笑容满是苦涩。金陵生死一别,今生已无缘和她再见,他能做的,也只有守着自己脑中的这些回忆,背负她未完的使命,一个人代替两个人走完这条路。他们两个人的酒,就由他一个人来喝。
方天翼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
重庆火车站里来往人群之中,一个女人正四处张望。她穿的墨绿色短衫很干净平整。短衫下配了一条黑色裙子,脚下的高跟鞋落在地上咔咔作响。洋气的西式装扮更衬托出她的娇媚与干练。她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无疑让她成为人潮中最显眼的一个。她乌黑的长发盘在脑后,两道细眉如弯弯柳叶,一双细长的眼睛加上浓密的睫毛,散发出迷人的气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如红尘中的一支玫瑰,以超脱俗世的娇艳和醉人的香气,倾倒众生。
她看到一个四十几岁身着西装头戴圆帽的男人带着一个拎着行李的年轻人走来,便笑盈盈地迎了上去。
“袁世中先生,您好,”她伸出右手,分别和这两个人握手,“这位是您的助手许国成先生吧。”
“您就是段美瑜小姐?”袁先生笑了,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他印象中的女军人都是粗声粗气的,一见到段美瑜这般温润的女子,不禁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很好笑。
段美瑜点点头:“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我们党内的戴副局长不幸遇难,现在委座和其他领导都在处理这次事故的后续事宜,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到火车站来接您。”
“啊,没事儿,我理解。”袁先生只顾着往前走,并不把段美瑜的话放在心上。
“您是化学专家,能来重庆我们是十分欢迎啊。这个非常时期,党内急需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掌握先进的技术是发展之根本。上级很重视您,但是您来重庆的事儿还不能声张,怕会有那种危险分子得知然后对您不利,所以才没大张旗鼓地邀请您,也没让您通知家属。当然,我们给您安排住处后,会尽快把您的家人接来的。”
段美瑜紧跟袁先生的脚步,不敢冲到他前面走,更不敢落下,表现得毕恭毕敬。
袁先生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大笑道:“哈哈,我就是个做学问的普通人,来重庆是我很久以前就做好的决定,能为祖国出力我很高兴啊!你不必如此紧张,难道你觉得我很小气?”
“啊,不敢不敢。”段美瑜有点不好意思,但也为袁先生虽功成名就却依然平易近人的高贵品格而感到钦佩。
“快走吧,看看你们给我安排的住处怎么样,是不是能体现你们委员长的‘重视’,啊?哈哈哈……”袁先生幽默地说。三人一同走出了火车站。
天阴沉沉的,山城的天气闷热。太阳光始终不能完全穿透赶也赶不走的厚厚的云层,亮亮堂堂地照到地面上。但街上的商贩似乎并没被这压抑的天气影响,依然拿出自己最大的热情叫卖,希望留住过往行人的脚步。身披破布衫,脚上蹬着露脚趾的烂草鞋的人随处可见,他们面色土黄,没精打采的,像是刚从搬运工地扛包回来,却找不到可以让他们吃一顿付得起的饭的地方。隐居深山多时的方天翼再看到山城的满目萧条,心都揪在了一起。战争结束了,他以为老百姓可以过上好生活了,可是国府脚下都有如此穷困的人,那其他地方岂不是更困难?如果内战爆发,不知还会多出多少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方天翼匆匆走过一家又一家街铺,他不能在此鱼龙混杂的地方再多停留了。
方天翼仔细读了报纸上照片所对应的报道。他推断,照片里的人应该都是军统局的内部人员,而且职位不低。看到王文渊出现在报纸上方天翼还是很兴奋的,至少王文渊没死。但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文渊竟和军统一起,而且穿着国民党军装。
方天翼没有先寻找重庆地下党组织,而是直接去了军统重庆站办事处。在探查重庆站之前,他得对这座办公楼的周围地形和内部结构做一番深刻的了解。
雾都之中,阴云未散,迷雾笼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