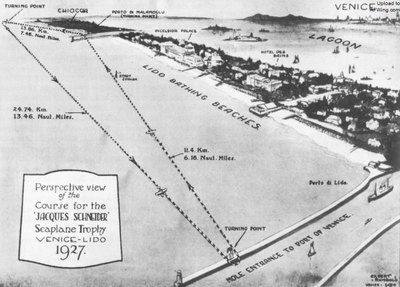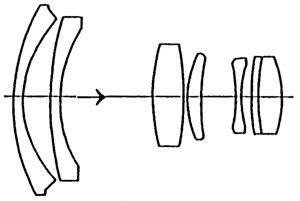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的爱情故事是二十世纪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由于阿兰·德隆对此缄口不提,即便偶尔提及,也很含蓄隐讳,再加上罗蜜·施耐德已经死去,因此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人们编造出的。而长久掩盖的事实是:在罗蜜的生活中,这位法国影星,不仅是她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忠实的男人。他是少数几个不利用她,不掠夺她,不榨取她的人之一,至少在经济上如此。
“我畏惧她忧愁的皇家气质,”阿兰·德隆说,“因为我最初认识的是银幕上的茜茜。但在真实生活中,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被她迷住了,我无法抗拒她的纯真。命中注定她将是个大明星,而不是德隆夫人。德国人认为,我拐骗了这个纯洁的少女,他们说:‘这只高卢公鸡,粗鲁地占有了他的猎物。’”
其实,罗蜜的继父汉斯·赫尔伯特·布莱茨海姆也说:“这家伙根本不适合这孩子。”实事上,布莱茨海姆不仅是关怀备至的“爸爸”,为罗蜜的名誉及自己的生意勤奋努力的人,同时,他也暗恋着继女。
罗蜜与德隆在卢加纳湖订婚时,罗蜜·施耐德向母亲玛格达讲出了一直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她“爸爸”的企图,没有用母语,而是用法语说:“他明确提出要和我睡觉。”
一直是德隆的代理人,也曾经作过罗蜜代理人的乔治·波姆,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的密友,在她死后说他“从没见过罗蜜比与阿兰在一起的时候更快乐。我相信,他是她生命中真正的男人。”
罗蜜·施耐德本人呢?她也说过:“我要生活,与阿兰一起生活,在穷乡僻壤也无所谓。我要生活,但同时也要拍电影,因为我热爱我的职业。我从来没有战胜过这个矛盾。”
罗蜜·施耐德遇到长她3岁的阿兰·德隆时,芳龄19,并已大名鼎鼎。在为《维吉的故事》及《女王的少女时代》进行的为期3周的宣传旅行中,她受到美国所有电视台的采访,在好莱坞的晚会上,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1958年夏,罗蜜·施耐德来到巴黎,举行《克丽丝蒂娜》开机前的新闻发布会,她及搭档也就是阿兰·德隆被介绍给了新闻界。她还将重拍由奥普西斯改编的施尼茨勒的《情人》,重塑玛格达·施耐德当年演过的角色。玛格达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1933年拍的《情人》中,玛格达·施耐德扮演了不幸的克丽丝蒂娜,威林的角色(并因此出名)。现在,这个角色由女儿担任。罗蜜·施耐德在机场被搭档接走了。
阿兰·德隆当时是法国电影界的希望之星。他英俊潇洒,大街上的男人女人都会为他回头。在被制片人发现之前,他已在生活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他在印度支那当过兵,长官只能回想起他的种种劣迹;他在巴黎开过出租车,当过跑堂,也曾在圣日尔曼大街上卖艺为生;现在,他成了演员(像罗蜜·施耐德一样,未受过专业训练)。与这位德国明星的合作,将带给他一次突破。由制片商安排的机场仪式让两人感到痛苦,两人都感到对方做作卖弄。之后在丽都举行的晚宴上,两人的坐位离得很远。
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在《克丽兰蒂娜》一片拍摄中的合影是立像,好像是“偶然”拍的快照。这不能说明两人的关系,或者只能说,记者在旁边窥视时,他们一直友好地站在一起。罗密·施耐德与阿兰·德隆在拍摄开始时,必须通过翻译,因为他不会讲德语,而她也不会讲法语。担任翻译的让-克劳德·布里阿里说:“他们在上面拥抱,而我在下面翻译。真的很滑稽。”
拍摄工作一切正常,离开摄影棚后,两人都觉得恶心。罗蜜·施耐德听到人们讲述的许多关于德隆的坏事,包括他对老女人的偏爱(那时,30岁就是老了)以及他为了前程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的传闻,感到既惊奇又恶心。人们还议论纷纷,看到他与一些不能与女人正常交往的男人在酒吧里。他与巴黎黑道人物的交往已不是秘密,这些人属于科西嘉黑社会。但这也只是猜测,没有依据。
后来她与他一起生活时,关于她的传说也广为流传,但与事实相距甚远。对此,罗蜜·施耐德只能付之一笑。她很快学会了不信任记者。在德国她被视为魔鬼,因为她竟敢从健康的德—奥茜茜世界逃到堕落的巴黎。从此以后,她一生都被记者追踪。
《克丽丝蒂娜》最后一段在维也纳拍。当阿兰·德隆乘飞机返回巴黎时,罗蜜·施耐德一直送到飞机旁。母亲玛格达及“爸爸”布莱茨海姆希望一切都会随飞机起飞而结束。但这种暧昧关系一直保持着,罗蜜与她的许多搭档都有这种关系。
结束了《克丽丝蒂娜》的拍摄后,这个年轻的姑娘本能地决定,要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将来的生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望去生活。茜茜终于脱下了让她头痛的假面具,卸下了伪装,把传统社会抛到脑后,以罗蜜·施耐德的本来面目飞往巴黎,飞向德隆。
在今天,一个姑娘离开父母去和她所爱的男人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时,不仅鲜有发生,而且在德国简直就是丑闻,完全违反了一个大家闺秀严格的行为规范。罗蜜比任何一个姑娘所受到的约束都更多。作为电影世界的产物,她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换来了名誉——但这个代价太大了。人们希望她循规蹈矩,她不只属于自己或某个男人,她属于全德国人民。为了保持最大的商业利润,她应该保持纯洁的茜茜形象,而不该在20岁时就与一个男人未婚同居,况且这个男人完全不符合德国人心目中的女婿形象。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罗蜜·施耐德更为自己的自由而高兴。即使与德隆分手后,她仍然把这件事当作少女时代快乐的回忆之一。
巴黎变成了她的故乡,在这座大都市里她有回家的感觉,这感觉她永远不会放弃。首先在生活方面,返回巴黎意味着进入美好的生活。在巴黎,她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远离以前她遵循的茜茜世界的价值观。晚上与德隆一起去酒吧和餐馆,与著名演员会面,他们当然知道茜茜,很高兴认识美丽的施耐德。
在激动人心的节日里,道德与不道德失去了界限,人们对此也毫不在意。但这不久就引来了阿兰的嫉妒,虽然阿兰明白自己不可能与一个女人厮守一生。罗蜜·施耐德在给德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宁愿在不幸的激情中生活,也不愿在平凡的幸福中沉睡。”她在巴黎没有经历到的,而且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是平凡的生活:邻居,采购,公园里散步。她的圈子里,真正的朋友少,假朋友多。这个圈子里的人像她一样有名,都是影星。
不久,施耐德与德隆搬到麦辛纳大街的一所房子里,房子是阿兰买的。拍了几部电影后,他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了。
虽然两人浓情蜜意,但工作对于他们仍是最重要的。他们互相鼓励争取更大的成绩。刚开始时,罗蜜·施耐德的名字总是排在演员表的最前面,而德隆的总是在最后面。不久,情况倒过来了。
德国电影业不再给罗蜜提供合适的角色,而此时,德隆却连直线上升。虽然根据原来的合同,罗蜜·施耐德仍在一些片子中担任主角,如《一半温柔》、《人间天使》、《美丽的骗子》、《卡佳——无冕女皇》等,她的片酬仍然很高(单是《卡佳》一片的服装费,她就得到600000马克),但在德国观众的眼里,她从第一名降到了第二十名。
《茜茜》三部曲后的所有电影都没有得到观众的喝彩,而被认为是电影院的毒剂。按电影界的行话说,罗蜜成了票房收入的毒剂,那些曾经向奥地利皇后大献殷勤的人,现在不再欣赏她。影迷们不想看到她演别的角色,发展她的演技。
她并不在意观众的这种想法。首先,她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钱;其次,她眼前的新世界更吸引她。“对于我来说,巴黎及阿兰·德隆才是最重要的,在这座城市里,有我的爱情,有我倾慕的人。”她毫不关注金钱,钱由布莱茨海姆照管。他每月汇往巴黎5000马克,她认为够用了,他却认为太多了。
与德隆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里,罗蜜·施耐德写下了大量的字条记事。有备忘录,有座右铭,也有愤怒,如她再也不愿见到某人(常常第二天就改变了)。这段时间保留下来的字条不多。内容主要是与她接近的人,他们收到了多少封罗蜜·施耐德的信和字条。这些信常常附有小礼物,是她随意找出来的,并无特殊意义。
罗蜜·施耐德很慷慨,对于钱,她向来马马虎虎。例如:和乔治·波姆住在一起时,一次,小偷入室行窃,丢失的东西中,有乔治的几颗卡蒂埃金纽扣。波姆述说了此事。不久后,在一次与安妮·吉拉多尔合作的戏剧的首演式上,罗蜜、施耐德从波姆身后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一个小盒子放进他的衣袋里,“扣上吧,想着我。”那是卡蒂埃的金纽扣。罗蜜·施耐德送礼物时,从不在意它值5千马克还是5万马克。
在巴黎那些忙碌的夜晚,这对已正式订婚的恋人之间有时风雨交加,有时波平浪静。阿兰·德隆的情绪爆发时,常常花瓶飞舞,棍棒交加,但也有安宁、真挚的时候。由于拍片外景地不同,他们只能互通电话,分离几周后,他们会在唐库见面。这是个小地方,德隆在这儿买了一幢房子,没用罗蜜·施耐德的50万法郎,虽然罗蜜很愿意出这笔钱。
这里远离巴黎的记者和朋友,阿兰·德隆后来说过,他当时曾努力做个普通人。7月的一个早晨,他站在花园里,卧室的窗下,手里拿着个小石头,往上抛。“罗蜜,起来,我们去教堂预定婚礼吧。”他想对她说。他抛了石头,罗蜜出现在窗前,但他却没说婚礼的事。罗蜜·施耐德如何爱他,从她父亲的信中可见一斑;“我亲爱的小宝贝,小老鼠,如果你一切都非常非常好,像你信中所说的一样,你一定是恋爱了。我希望他是个好人,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切。如果你的信里再用罗丝玛丽签名,我可要打你的屁股。”她给父亲的信基本都不签名,而是画一只小老鼠。
《明镜》周刊于1963年底刊登了一篇文章:“4年8个月零24天之后,在数次宣布结婚又数次食言之后,本世纪中最喧闹、见报频率最高的婚约以一次越洋电话而告结束:在13000公里长的电话线两端,奥地利影星罗丝玛丽·阿尔巴赫—瑞提,又名罗蜜·施耐德,25岁,与法国新浪潮骑士(《只有太阳可以作证》)阿兰·德隆,28岁,平静地达成一致,解除婚约。”
在好莱坞拍电影期间,由于饭店太贵,她在白威利山租了一套别墅,与女秘书桑德拉·约尔曼及几个佣人住在一起。一天,朋友兼代理人乔治·波姆来看她。一是来看看与杰克·莱蒙的合作,二是来谈下一部片子的计划,这是与哥伦比亚公司的合作。双方计划在7年中拍7部片子,并尽可能延长合作。
关于两人离婚的一个故事这样说:乔治·波姆接到阿兰·德隆的电话,让他在公文包里找出一封信交给罗蜜。罗蜜·施耐德得知阿兰·德隆打来电话而不与她讲话,斥责波姆不为他们接通电话,波姆支支吾吾。在去摄影棚的路上,她逼他说出实情,他终于拿出那封15页长的信。晚上,拍摄结束后,她看了那封信。罗蜜几近崩溃,泪水随之而来,靠着镇静剂和酒精的帮助。她才坚持拍完了整部电影。
关于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还不太离谱:据说,阿兰·德隆在电话上简短地告诉罗蜜·施耐德为什么要离开她。他说,她太好了,而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等等。结果和上面的故事一样——眼泪,崩溃,但一直坚持到拍摄结束。
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刺激的说法——拍摄过程中,罗蜜·施耐德与著名的好莱坞制片人罗伯特·伊文斯开始了一段充满激情的关系。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罗蜜·施耐德与亨利·麦恩分手后,她才认识罗伯特·伊文斯,这已是多年后的事了。
事实是(罗密·施耐德保留了许多字条),罗蜜回到巴黎的寓所时,发现一束玫瑰,下面有一张德隆写的字条:“我与娜塔利去墨西哥了,祝好!阿兰。”她也保存着维斯岗提的电报,他在报纸上得知两人关系结束时,向她表示“我爱你,罗蜜娜·卢卡。”
罗密轻视了他们的分离,也错误估计了阿兰拈花惹草的爱好。在她忙于工作的时候,一个叫娜塔丽的女人粘上了阿兰。她性感、放浪,不顾廉耻。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飞速结束自己默默无闻的命运。她跟阿兰说自己与罗密就像双胞胎,她为他拿衣服拿饮料拿剧本,总之像个影子一样与他寸步不离。终于她如愿以偿地怀了孕。罗密拿到了他们的照片,娜塔丽洋洋得意地坐在阿兰·德隆怀里,脸蛋漂亮俗气,身材矮胖,显出一种直率的农村女人所具有的挑衅般的自信。
对于阿兰·德隆来说,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头一回,这个法国电影界的花花公子,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本性,只要罗密转过头去,他就和别的女人调情。但是这一次不同:现在的这个女人,熟悉他的粗话和他那诞生于贫穷之中的顽强奋斗的愿望,而且她怀了孕。阿兰的说辞是“我最憎恨罗密出生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幸的是罗密被这个阶层打上了烙印。我不可能在五年之内抹去她被灌输了20年的东西。在她身上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爱其中一个罗密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恨另一个罗密也同样强烈。
最终,他给罗密留下一封长达15页的信件,并在家中留下作别的黄玫瑰以了结他们六年的情缘。几个月后,阿兰娶娜塔丽为妻。
罗蜜用剃须刀割开手腕的血管自杀,但被一个朋友发现并救了她。他认识一个正直的医生,照顾了罗蜜并对此保持沉默。
正如乔治·波姆对他所知道及经历的一切保持沉默一样。罗蜜·施耐德从没有忘记这一点。
几年后,在法国南部与亨利·麦恩的婚礼上,乔治·波姆是证婚人,她的手腕上还可见到一条淡淡的疤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