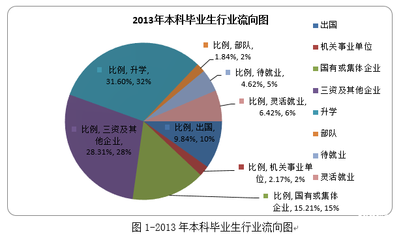杜彩是广院蛮有知名度的老师,这是我曾在大一时对他的一段采访,曾登在学校的《启明星》报上,现在放上来“充数”。呵呵,大二了,一直也没有再见过这位老师,很是怀念,说实话,在广院众多老师中,他真的很出众了,暂且不论别的,比很多人敬业!另外,也没有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出勤、点名、成绩上,着实难得。更重要的,不像马哲、邓论的老师一辈子研究那些垃圾~嘻嘻
另一只眼看播音主持
——访文学院杜彩老师
开门见山:我对播音系学生很担忧
安:您教过不少播音系学生,感觉如何?
杜:说实话,我对播音系学生挺担忧的,今后从业怎么办?自己的生存状态会怎样?是不是处在一个心里十分稳定的层面,这些都是你们要面对的问题。或许播音系的学生应该多分流些,可以选择作演员之类,不要完全定位于主持人。
安:在你们看来,播音系是不是比较浮躁?
杜:应该可以这么说。你们这个专业的“领袖”,都是大明星,所以应该警惕,不要看到了些许的“星”,就以为今后就是他们,那是好笑的。那样你会非常失落。另一方面,现在的学习能否给你们以后在社会上谋生的手段,这也称得上是一种生存发展的智慧。
传媒与知识分子
安:在中国目前的国情里,传媒人是否应该尽量保持知识分子的纯粹呢?
杜:中国知识分子都不纯粹,要了解纯粹的知识分子,去德国、俄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戕害下,屈从于政治;在商业环境下,屈从于商业。从国情看,许多大学的教授可以被认为不错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有些观点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有时甚至背离,在官方掌握的媒体中,他们是不可能允许出现的,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是不太可能保持纯粹的。
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信仰,但如果知识分子都没信仰的话,是很可怕的,国家就处在一个恶俗的境地里。
电视对人们的影响
西方人认识到了传媒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生产力发展了,传媒作为一种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该如何发展。西方许多学者都在思考科学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时代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倒退的,因为电视的快速导致了它的粗糙。
安:但你觉不觉的电视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文化的提高。
杜:是的,电视最具革命的一点就是击破了传统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老百姓在家一开电视,就可以看到门票高额的音乐会,这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地方:把文化民主化了,把精英文化世俗化了。
而我们主要避免的就是商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把人变得庸俗化了,变得容易遗忘历史。作为从事通俗文化的你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只是文化的一下部分,还有精英文化的存在,要培养自己的精英意识。
安:但我想,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具有精英意识的这一批人,进入电视这个大众传媒后,能接受他们的很少。记得一次主持人大赛,白岩松评价一个哲学系博士生:“我都不敢正视你的眼睛。”您不觉得这种高度太让民众难以企及吗?
杜:这是你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像我,就绝对不能当主持人,我的讲话中充斥着语言暴力
安:有吗?我们似乎不觉得啊。
杜:你们不觉得,这可能还可以理解,这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了解受众的原因,曲高和寡真的是你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也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其实在你们的圈内也应该可以看到,新闻人总是比娱乐主持人贫困,而我也总是很贫困的。
安: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段谈话似乎很矛盾,一面在反对商业文化,一面又在不得不参与其中……
杜:恩,这没办法,人的一生总是很矛盾的,人人见到美女都会感动,但由于教养、世俗又不能那么直接表露,这不是更矛盾吗?正因为这灵魂和肉身的矛盾,人才显得更真实。
一点建议:
安:给我们播音系的同学一点建议吧。
杜:不要只学播音,毕竟这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职业,要学会适应社会,同时要有危机感,要未雨绸缪,最好低调一点。我建议你们多学学政治经济学,自问:以后在社会如何发展,你的文化资本是什么?而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很对的,没有各种资源,你怎么在这个合作型那么强的圈子内搞播音?
我非常希望你们能赶快进入未来要面对的生存状态,要不到时候你会没有像今天跟我聊天的欲望。电视台是个非常垄断的行业,每年培养这么多主持人,如何解决僧多粥少的局面?
你们现在一定要有意识,自己专业要学好,但光有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是绝对不够的,要有能让自己立足社会的资本。不要让自己成为一旦面对显示就显现出萎缩的人。
后记:与杜彩老师的聊天,只持续了近20分钟,许多问题便只能点到为止,但管中窥豹,依然略见一般。
当我说起要采访时,他说:“采访我干嘛呢?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偶像崇拜的……”我赶紧说,只是谈谈你的思想,才欣然同意。杜老师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相对贫穷但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氛围里,在现代物质社会里,显得格外显眼。
也许他的许多观点,在时下传媒人眼里很不合时宜,但我相信,他所恪守的人格走向,也正是现代传媒人所需要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