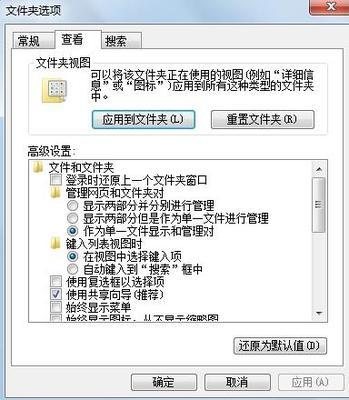南瓜头,就是南瓜藤的嫩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人吃南瓜头,富阳肯定有。近一两年很少去菜场,但是,我现在每天经过的陈家弄里,每天清早,总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最多的还是菜摊,暑假里早上去上班,经过那里,总看到有人一手提着鲜绿的一把南瓜头昂首走着,我总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他两眼,像别人所说的——英雄所见略同。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吃南瓜头。怎么吃也吃不厌。在我认为,蔬菜里,如果不加任何荤腥配料就能烧出鲜味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菌。第二种是笋。第三种是南瓜头。菌类早就被人们熟识了,只是我们这带的人很少有人会自己进山采摘。笋当然包括鞭笋和冬笋,它们似乎可以成为山珍,夏天的干菜鞭笋汤,有人把它叫人参汤。白腌菜蘑菇冬笋肉片,是冬日是下酒的一个小炒,在饭桌上被点的频率最高。但挖笋好像是技术活,一般人不容易挖到,所以,连带着鞭笋与冬笋的价格也就高了。最平易近人的是南瓜头。我喜欢它的平民化。
最开始以为南瓜头很少有人吃。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常炒给我吃。吃南瓜头的日子一般在五月或九月。五月,梅雨时节,下了很久的雨,南瓜藤疯一样地长。主藤上舒舒服服地长出八九片叶子了,没人管着它们,于是。主藤开小差了,这个胳肢窝里生一个嫩头,那个胳肢窝里又一个,就想着侵占地盘,扩张势力。祖母这时候就会毫不客气地扭下这些嫩头,只在几棵南瓜藤上清理一下,就够做一碗南瓜头了。
扭下来的南瓜头精神多好。它们一律食指粗细,手臂那么长。长了四五片巴掌大的叶子。毛茸茸的,越到头上,毛越细越白也越密。摘下叶子,从梗部沿边掐住一部分,翻下来,咝—咝,断续了几下,就有一层薄透的衣被撕下来,微微的绿色,有很好韧性。就这样把一片片叶子都撕好了,再撕须。有人说须是南瓜头的精华。我没有单独试过,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以为须有些可怕,它们卷曲,细长,而且不容易撕,但也总能耐着性子撕完。七八月一般不吃南瓜藤,因为能扭的南瓜藤大多扭完了,只指望着主藤多长些老南瓜,喂家里那头总也喂不饱的猪。九月的南瓜头是有些老,大多是摘了老南瓜以后,南瓜藤大约还有多余的力量,又生出一些支藤来,但毕竟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些支藤总有些缩手缩脚的样子。
撕完南瓜头,接下来的事就是揉。放在竹篮里,把南瓜头揉成一团,有些像揉马兰头,揉马兰头是为了去涩。可揉南瓜头是为了把藤上的细毛揉去,去糙。然后像一般的蔬菜一样炒,大火,放一点蒜末,或一点红辣椒,装盘后碧绿,洁白和通红的样子,真好。

我母亲最近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撕好的南瓜头直接放入沸水里一焯,然后捞起,往冷水里一放,色泽艳绿。炒好后感觉比揉搓的更好,少了那种糙的感觉。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种吃法。我有一天问我母亲,怎么会想到这种做法。就,懒得揉。原来,懒也有好处。
七月里吃南瓜藤的几乎只有一次。那是农历的六月廿三,是吃新米汤圆的日子。我问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回事。据说虹赤以里才有这样的风俗。我觉得很奇怪。更让人奇怪的是我家的新米汤圆会用南瓜头一起烧。这种味道,好吃得简直无法形容。没吃过的人肯定无法想像这种味道。一般人家的汤圆,里面包点芝麻馅,甜的吃。我家的新米汤圆实心,烧汤圆前先备好南瓜头。撕好,揉碎,准备好猪油。在锅里放水,放点盐,烧沸,将汤圆放入沸水里。几分钟光景,就看到那些浑圆的小球上下翻滚,有几个可能就在水面上不停地翻筋斗。把揉碎的南瓜头稍切几下,放进锅里,沿锅边铲几下,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一幅异样的画面,雪白的汤圆,碧绿的南瓜叶,宛若一个高手的杰作,像是翡翠盘里的珍珠。放少量猪油,马上起锅。不用味精,也不放鸡精。放了就太鲜,太腻。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退休了,我就住到山里去,自己种南瓜,那时候,就可以餐餐吃南瓜头了。
 爱华网
爱华网